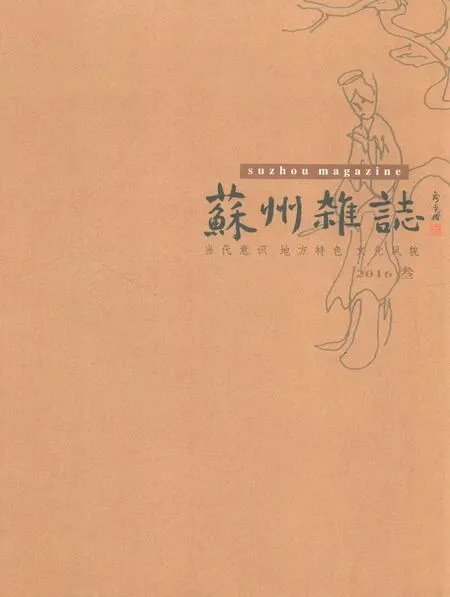重建穿山盛景
子川
重建穿山盛景
子川
在沙溪搞雅集有一定偶然性。江南古鎮多,叫響叫座的不在少數。第一次見到沙溪,有點驚詫,這么好的古鎮原先怎會不知道呢?毫無疑問,過去不知道沙溪也不全是我的錯。乍一相見,感受到一種簡靜中的清雅,與那些業已形成旅游氣候的古鎮大不同。后來,在樂琦委員那里得了一本《穿山小集》,又在她陪同之下去看了穿山遺址,終于發現與沙溪面緣后面的文化淵源。

子川書法
沙溪的穿山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小的山。沈周有詩:“遍觀天下山多少,惟有穿山山最小。”嘉靖本《太倉州志·山》:太倉山唯穿山為天作,在州東北五十里。高一十七丈,周三百五十步,中有石洞通南北往來,相傳海中島也。臨海記曰:“山昔在海中,下有洞穴,高廣各十余丈,舟帆從穴中過。”穿山是大海的饋贈,大自然的奇跡,“既有真山的嶙峋氣勢,又有假山的靈秀精巧”。宋元之時,即引來眾多文人墨客和方外名家。元代的德靜,明代的陸昶、沈周、文徵明、王育、陸鉞(仲威),清代的吳偉業(梅村)、趙樞生、邵廷烈等,都曾雅集穿山且留有詩文畫作。其中,文徵明詩句“春光過眼無多日,暮景榮身有幾人?綠竹蒼松同晚節,落花飛絮各風塵”(七律《穿山晚翠亭》),吳梅村詩句“勢削懸崖斷,根移怒雨來。洞深山轉伏,石盡海方開”(五律《穿山》),皆一時詠穿山的名篇名句。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峰不在峻,有詩則傳。
穿山毀于1952年,據說系大上海修建“共和新路”征采鋪路之石,就近將穿山作為石材開采致用。昔時的共和新路今日何在?通向哪里?知道的人不多,想知道的人也不會太多。而億萬斯年因海浪沖刷、因地貌變遷所造就的天然奇觀,竟因此不復存在,明清兩代穿山之繁華,蕩然無存。
作為天造之物,穿山是無法被恢復的。個體生命太短,即便用人類進化的全部時間進程,也不足以造就這樣的自然景觀。但我們的生命長度,足以讓我們明白自己的愚蠢以及種種敵視文化的罪過!過去用政治形態強調致用與今天用經濟意識強調致用,殊途同歸,其危害完全相同。也許我們該用詩、用詩象征的“無用之用”,來重建穿山盛景。事實上,從前人留給穿山的詩篇中,我們已經明白這樣的道理,山可以被炸,而詩的存在,卻令這個不復存在的山依舊存在,不因世事變遷而被遺忘。
自2012年始,發端于詩文化的沙溪雅集已持續五年。五年是一個不短的歲月,坐落于沙溪古鎮的文化江南會館,以每年一度的“詩夢江南,沙溪雅集”,在延續前人穿山雅集的風雅與文脈。
在文化意義上重建穿山盛景,我們還需要做更多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