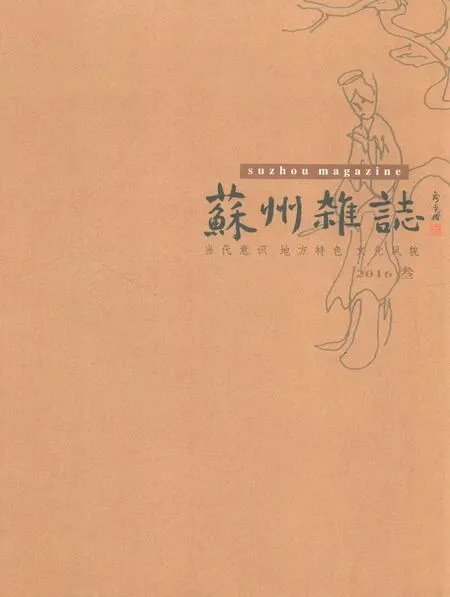培德里的鄰居
李名洲
培德里的鄰居
李名洲

很多往事隨著歲月飛逝過去了,但住在培德里的鄰居,有的雖整整過去了六十多個年頭,卻難以忘懷,刻骨銘心。
弄口旁側是一大典當,典當門邊設有書攤和牙攤;大餅店開在里弄口;緊挨大餅店是修鞋攤。碰上紅白喜事里弄交通被阻,警察也難以疏通。里弄很長,我們住在培德里6號樓上,靠南是6棟二層磚瓦房,靠北是6棟二層磚木房,中間有一條水泥通道,東面是兩棵高大挺拔的槐樹,夏天是納涼的好地方。那時我只有十幾歲,讀四五年級。我們住樓上,樓下住著以賣碗為生的德奎叔,還有德奎嬸和他的侄子阿信。我們兩家很融洽,遇事相互幫助,磕磕碰碰都謙讓。他們生活貧困,起早貪黑地干,卻難以糊口。“屋漏偏遭連夜雨”,1947年的夏天,阿信得了“霍亂”。上學之前我還去看望他,他躺在木板上嘔吐不止。我雖然不懂什么叫“霍亂”,但還是叫他們趕快送醫院,可是哪里來錢呢?只得硬挺著。等我中午放學回家,一進門就聽見悲痛的嚎哭聲。母親說阿信死了,我大吃一驚!身強力壯的阿信怎么這么快就離開了我們?半年下來,德奎叔變得形容枯槁,呆若木雞。添了一個小孩后,在兵荒馬亂、民生凋敝的年代,賣碗的行業無法維持生計。那年年三十,他把所有的本錢買了好菜,吃了一頓年夜飯。誰知半夜里全家人折騰起來,原來他下了毒藥走上絕路。鄰居得知后,湊足了錢,把他們送進醫院,經搶救轉危為安。培德里百余人,松了一口長氣。

住隔壁樓上老鄉鄰曹五與我同年,今年有70多歲了,小時常在一起捉蟋蟀、打彈子……他爺爺一口紹興調:“天氣冷颼颼,泡碗熱飯熱吼吼。”他爸是茶房,在一家店上班。80年代初,我從部隊探親回家,他在南貨店門旁擺了修理鍋盆的攤。不50歲的他一臉風霜,皺紋縱橫。他1955考取北京地質大學,后分配到大西北,嫌活艱苦回到家里,當過職員、教過書。后和一女人跑單幫發了一筆財,開過店,做老板。但他經營不當,嚴重虧損,最后盤還債。到了70年代后期,窮得一貧如洗。虧老夫老妻感情甚篤,相濡以沫,風雨飄的家庭未走上妻離子散的絕境。
隔壁樓下住著一個孤獨的老太太,50歲。她篤信耶穌,穿戴干凈利落,待人和,仗義疏財,常施舍窮人錢物。一天傍晚,偷潛入她家,用刀威脅她交出財物。而老太一點也不驚惶,對他講起做人的道理,了他兩塊大洋,還告訴他,若有困難可再找她。后來這個青年改邪歸正,在一家木工廠當工人,還常常帶著妻子、兒子來拜訪她。“文革”中,她遭到迫害,被抄了家。一幫紅衛兵揮舞著拳頭在她門口高喊:“耶穌給我吃饅頭,我給耶穌吃拳頭!”老太太含著眼淚連聲說道:“作孽啊!小朋友!”那個青年把她接到他家住,讓老太太安靜度過鬧心的“文革”。當時他已是這個廠的革委會主任。
她是一個有文化修養的女人,留著一頭整齊的黑發,梳妝樸素整潔,走起路來腰桿筆直,弄里的老少敬她三分,里弄發生大小糾紛,只要她出面,矛盾化解,無不心悅誠服。1946年,她正當不惑之年,在“教育救國”的影響下,創辦了一所私立小學。靠東一幢二層樓是學生的教室,約有百名學生,起名市西小學。一日多次鈴聲使寂靜的里弄增添幾分春天的氣息。女校長姓嚴,她年輕時出國留洋。不幸早年喪夫,留有10歲光景的男孩,日日跟在身邊,寸步不離。有一年春節,其兒子突然失蹤,她終日惶惶不安,魂不守舍。不知為什么我很同情她。“校長,我們會幫你找回來的。”原來她的大兒子(前妻所生),有點精神失常,把他弟弟帶回鎮海老家度假,一場虛驚,弄得我難過了半個月。
解放后,市西小學合并到曹家灣小學,她賣掉房子把錢全部捐給了國家,自己從事教師工作。
1995年我退休,去培德里,已成一片廢墟,拆遷戶各奔他鄉,兩棵老槐樹仍挺拔高大。我打聽到:德奎的孫子在沈陽空軍部隊任職,他常回來為爺爺、奶奶掃墓。曹五老兩口身體很健,搬到大龍港頤養天年,獨生女是一名歌唱演員。女校長可謂桃李滿天下,遍地芳菲,已去世多年。兒子繼承了她的事業,是一所中學校長。
當我離開時,回頭看了看兩棵老槐樹,仿佛聽見小學的鈴聲再次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