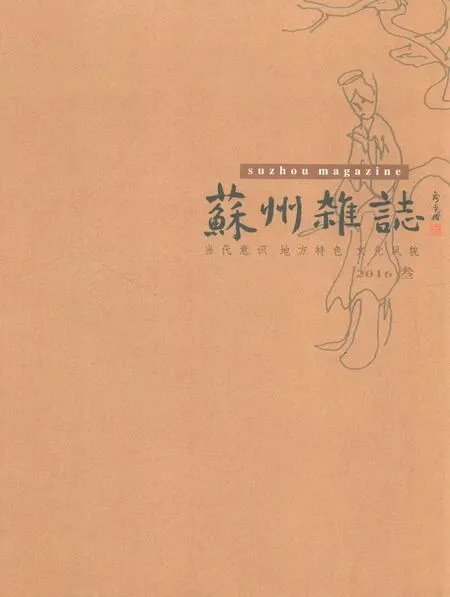回憶我的爺爺
陶金明
回憶我的爺爺
陶金明

黃異庵 書法
今年五月十八日,是我爺爺黃異庵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時光流逝,往事歷歷在目,音容笑貌猶在眼前。他雖一生磨難,但仍孜孜不倦不辭辛苦寫長篇,他雖室已雅無可雅,但仍開詩書印義賣展,所得全捐民政部門。他是一世無愁半世屈,但仍交代我們小輩要交友以誠。
父親講,爺爺從小出色,上海文化名人江錫舟來太倉旅游,發現爺爺人小字好有天賦,便介紹拜當時為滬上三大家之一的天臺山農劉介玉先生為師學習書法。十歲時和江錫舟兒子江寒汀一起在上海大世界門廳旁,一個揮毫寫字,一個潑墨畫畫,從此“十齡童”就名揚上海。多年后回憶此事時,爺爺還作詩一首,“共和廳里十齡童,對客揮毫小相公。一事至今忘不得,難為老父作書僮。”
1930年爺爺和江錫舟四女成親,1931年長女曙紅出生,1933年長子出生,取名云初,即我父親。十八歲那年爺爺即和舅兄一起學習蘇州彈詞,后因舅兄江寒汀常熟話太濃,一時難以改變,就放棄了學習。爺爺由于有較強的古典文學功底,加上特別喜愛一類文學性較強的書目,故一部有別于朱寄庵朱蘭庵的《西廂記》就此誕生了,貌不驚人的爺爺連同他的“黃西廂”走紅上海灘。
解放后,爺爺最先編唱李闖王新書,作為評彈界唯一代表,出席了五十年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戲曲工作者會議,被稱為“評彈才子”。1957年起走入坎坷,1959年被發配去青海。爺爺有詩為證:“姹紫嫣紅色太姣,妒花風雨自難饒。狂吹直去天西北,九月高原雪正飄。”1969年上山下鄉隨女到濱海,奇苦無比,半饑不溫。爺爺寫詩記錄道:“誰令幽境絕人煙,新屋初成五月天。曲水流墻觀不足,霉花開到枕頭邊。”爺爺常說自己是一生三海,三海先生,紅在上海,難在青海,苦在濱海。
應該說是坎坷經歷和深厚的文學功底造就了多才的爺爺。他的詩總是觸景生情,無論是全國戲曲大會歌頌志愿軍的詩,還是生活中有感而發自娛自樂的小詩,無不體現他的才藝和對生活的熱愛。爺爺酷愛彈詞,自編自演長篇有四部,《西廂記》傳給了楊振雄,《李闖王》傳給了饒一塵,《文徵明》傳給了趙開生。濱海歸來后,他迎來了又一個黃金創作期,《紅樓夢》《翁同龢和楊乃武》等相繼問世。談到紅樓夢,不能不說著名紅學家周汝昌老先生,在共同研究紅樓夢時,兩位老人結下了深厚的感情。諸多書信往來,惺惺相惜,一個說:“白頭人說紅樓夢,應被紅樓笑白頭。怪底掌聲雷動處,座中顧曲獨無周。”一個說:“多才多藝異常流,不獨知音顧曲周。論墨講詞兼篆印,一時聲動古蘇州。”周汝昌老先生評介爺爺柳敬亭后一人而已,不是一般的藝人,而是在文學藝術上博道的大方家。
1981年爺爺從西園新村搬入石幢弄,我和父親幫他搬家,講起我要去參軍,我父親有些想法,不大情愿讓我去。爺爺知曉后,做我父親的工作,說好男兒志在四方,小青年應該走出去參軍。要知道,當時他自己頭上的帽子還沒有完全摘掉。
爺爺歷經三海,為人樂觀,生性耿直,更加淡泊名利,雖在評彈、詩詞、金石、書法等方面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仍孜孜不倦。晚年生活盡管清苦,他從無怨言。1994年開詩書印義賣,凡來參觀者皆曰:此異庵之所以謂異也,不計自身之清貧若此,而竟養媳婦做起媒人來也,異哉!爺爺淡然一笑:“天自無言理可通,盈頭白發氣猶雄。但求安我心而已,只認無錢不認窮。”
1996年春,我到醫院看望爺爺,告知父親因病過世,他拉著我的手久久無語,然后說:我對事業投入太多,對子女關心太少,尤其對你父親。我有愧于他,我死后要和他葬在一起,多陪陪他。并談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長輩對隔代的殷殷期望,使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

黃異庵 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