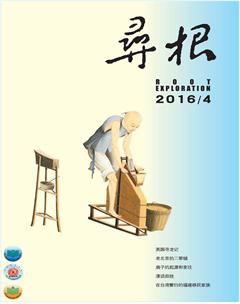老北京的二葷鋪
吳正格
“二葷鋪”這個詞目,《辭源》《辭海》里均未收錄。1992年出版的《中國烹飪辭典》里釋“二葷鋪”為“茶飯店”。近閱《小說詞語匯釋》,見有“二葷鋪”條,釋為“北方一種賣簡單飯菜的小飯鋪”。從筆者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較早載有“二葷鋪”的是清人陳森的長篇小說《品花寶鑒》,其第二十五回里寫道:“本在個二葷鋪打雜,因散了伙,情愿來幫同灌園。”陳森是江蘇常州人,道光中寓居北京,寫成此小說。茲見,“二葷鋪”之稱在道光以前已是京人習慣。
“二葷鋪”是怎么被京人應用的呢?我以為,遠與清時京都的清真飯館有關。早在明初,燕王朱棣掃北,隨軍的回人多有在京城落戶者。那時,牛街一帶是回人的集居地,其中不少人家就開起飯館或食鋪,并世代沿承。入清,清真飯館已遍及九城,基本是小本生意,一兩間鋪面。取用的食材呢,自然是以牛、羊肉為主。因而,牛、羊肉就被俗稱為“二葷”,也就連帶起“二葷鋪”之謂。這就如稱漢人飯館為“大教館子”、清真飯館為“隔教館子”,都是老京人的本地話。
后來,“二葷鋪”也不專指清真小飯館。凡是比大飯館子規模小、中等偏下,又比小吃鋪的檔次高,無論清真或大教,都被稱為“二葷鋪”。這類飯館,一般是四五張或六七張便桌,不承辦酒席,只供散座。您要去點個紅燒海參或熘蝦段、清蒸魚啥的,肯定沒有。人家是二葷鋪。若是清真館子,經營的不外是醬牛腱、燒羊肉、扒口條、熘胸脯、爆肚兩吃等。大教館子的“二葷”,通常指豬肉和豬內臟(又說為豬、雞),菜的花樣也不多,不過是干炸丸子配老虎醬、淡生熟肉片、滑熘里脊、壇子肉、爆腰花、熘肝尖、熘三樣之類的小熘小炒,趨顯于山東風味。要喝酒只有燒酒,一般不供應黃酒。燒酒就是老白干,老京人叫它“燒刀子”,也是北京方言。
當然也有素菜,如炸茄盒、炒合菜、醋熘白菜等,也都是山東菜的制路。但有三樣素菜,即麻豆腐、拔絲山藥、烙炸,則屬于京城的本地菜。麻豆腐,薛寶辰《素食說略》中有記:“乃粉房所撇之油粉,非豆腐也。以香油炸透,以切碎核桃仁、杏仁、醬瓜、筍丁及松子仁、瓜子仁,加鹽攪勻煨之,味頗鮮美。”薛為清末宮官,信佛,對京城食肆的素食頗為了解。他所記的麻豆腐,應該是原端做法。我想,此饌是因為用“粉房所撇之油粉”為原料,成本低,故加些講究的配料,這樣能賣上價錢。拔絲山藥,《素食說略》中記:“(山藥)云皮,切拐刀塊,以油灼之,加入調好冰糖起鍋,即有長絲。但以白糖炒之,則無絲也。京師庖人喜為之。”可見,清末做拔絲山藥時熬的糖漿,是用冰糖。也因“京師庖人喜為之”而使這一甜饌起譽,后來成為流行全國的名饌。但說“以白糖炒之,則無絲也”,就不對了。用白糖仍能拔絲,這道理廚師都懂。烙炸,是又烙又炸的菜,但收口是焦熘,為京都傳統名食。烙炸的原料是用綠豆面糊先烙成大片,再切成棱形小塊(或長方形小塊),遂以油炸至酥脆,然后用蔥姜蒜末、醬油、醋、水淀粉兌合的味汁熘之而成(后來這菜又加了些羊里脊絲當配料,也是為了賣上些價錢)。這三樣素菜,大飯館子賣的少。人家包辦酒席,慣做參蝦魚鴨,您專去吃這等素菜,那就不可能啦。所以常作小酌的人們,多習慣去二葷鋪。這三樣素菜,也就被二葷鋪的廚師炒成了氣候。
清末,京都最有名的二葷鋪是哪兒?崇彝《道成以來朝野雜記》中記:“東華門有一最小酒館而名震九城,名日和興號。其址正對已燒之東安門,小賣點心,佐酒小吃,無一不佳;酒為自造,尤有盛名。后以民初壬子正月兵變,火焚東安門,左右皆付之一炬,遂未復業。”這樣出名的二葷鋪,那時京城里還有不少,如西四牌樓南面路東的龍泉居,阜成門外路北的蝦米居,還有西長安街的龍海軒等。多掛金字招牌,常見的是黑漆牌匾上鑲著半凸的金字店號,講究些的,金字上貼的金箔,也就是很薄的一層,非純金。有的飯館,直接就把“二葷鋪”寫到牌匾上,像是文章題目下的副標題。
二葷鋪也在一些名家的筆下出現過,對我們了解這類小飯館有所幫助。1929年,張恨水應上海《新聞報》主筆嚴獨鶴之約,在該報連載了他的長篇小說《啼笑因緣》,其中寫到關秀姑拿出一塊錢,要她父親關秀峰請樊家樹吃一頓飯,并特別囑咐不要帶“樊先生到胡同口山東人開的二葷鋪”。僅這句話就能反映出兩種情況:一是清末民初有山東人在京城經營二葷鋪,關秀姑說的非為個例,而是表露出那時山東人闖京都都開餐館的一種跡象。二是這類飯館是面向普通大眾的,士大夫或公子哥兒是不肯光顧的,就連講究酬客的人也不愿涉足,嫌丟面子。可是,二葷鋪在清代京都的社會生活中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各地來京科考的寒窗試子們,及至民國時來京念書的學生,多到二葷鋪搭伙,解決吃飯問題。他們成業后,也會思念或回憶在二葷鋪就餐的難忘時光。更有小商小賈和市井庶民,在這里聚友小酌,聊聊山南海北、社會逸聞,內容不是主要的,而是吃得可口,喝得盡興。二葷鋪的蕓蕓眾廚們,也就把他們的手藝施展出來,積淀出一宗內涵非常豐贍的民間食俎型格。
又如夏枝巢所著《舊京瑣記》中說:“日二葷鋪者,卒為平民果腹之地,其食品不離豚雞,無烹鮮者,其中佼佼者,如煤市街之百景樓,價廉而物美,但客座嘈雜耳。”這段話,將清末京都二葷鋪的特征概括出來了。所說的百景樓,店址在前門外煤市街。該店的興隆應該在光緒末葉以前。因為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變”時,義和團焚燒前門外大柵欄老德記大藥房時引起大火,延燒至前門大街以西部分。在此范圍內,“略約延燒鋪戶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間七千余間”“今遭此奇災,一旦而盡”。百景樓亦難以幸免,災后未復業。按夏枝巢所說,那時的百景樓一是“價廉而物美”,二是“客座嘈雜耳”。從中試作析釋。
第一屬于經營有方。價廉是營興之道,物美是攬客之本。說起價廉,我不免要多說幾句貨幣。那時京都已流行新式銅幣,稱“銅圓”,與傳統的圓形方孔銅錢不同,無孔,中間有“光緒元寶”四字,背面有蟠龍紋,京人俗稱“銅板兒”。銅圓分為:當二十、當十、當五、當二(共四種)。當二十的俗稱“雙銅板兒”,當十的俗稱“單銅板兒”,此兩種流通最廣。從有關史料中分析:百景樓的豬、雞類菜,大致不超過三個當二十的銅圓,約合一毛五分錢;素菜不超過一個半當二十的銅圓,約合七八分錢。但大飯館,如飯莊、酒樓,因其房租、開辦稅、人員薪水等開銷大、費用高,這都要打進飯菜的成本里,故而上述菜的價格,要比百景樓高出三分之二。而僅就這些菜,大飯館未必比百景樓做得好。不然,該店何以被夏枝巢稱為二葷鋪中的佼佼者呢?這也正是其經營之盛的主要原因。
第二是“客座嘈雜耳”。百景樓的生意興隆,店小客多,客人聊天勸酒,或逗趣樂呵,那能不嘈雜嗎?且不說這等嘈雜,單說堂倌迎來送往或喚菜報賬的叫堂聲,也會不絕于耳。老京人都知道,像百景樓這樣火爆的二葷鋪,招募的堂倌,一定得是精明能干、頭腦靈活、身手麻利、記性又好的。甭管多忙,得不上錯菜、記錯賬;碰上挑剔的客人或突發的閃失,也能化難為順。那就全憑靈嘴巧舌、隨機應變。這也是使客人贊賞和能拉主顧的本事。我就給您摘錄一段二葷鋪堂倌的叫堂聲:
“燒刀兒一壺哦!一碟兒炒里脊絲兒、拉皮兩張燒紫蓋、炸焦熘碟兒丸子、炒肉片兒呀!切碟兒肉五花兒噠!中碗兒炸醬呀面伴(音‘把)兒倆呀!逛兒湯哦分碗兒盛,烙上兩張清油餅呀!”
至此,二葷鋪也就說出個大概。若給二葷鋪立個詞條,應該是:“二葷鋪,舊時北京方言,為民間語言的一種變體。約俗成于清中葉,道光間又有文載。泛指舊時北京小飯館或小酒館。視清真小飯館主營牛、羊肉菜為‘二葷;視漢式小飯館(或小酒館)主營豬肉、豬臟類菜為‘二葷(一說豬、雞);多為山東移民開設。店鋪通常設在民宅胡同口或鬧市街,遍及舊京九城。顧客主要是庶人百姓、進京科考的寒窗學子,后及民間的大學或學堂學生等。二葷鋪是北京民間菜和家常菜的成立基地之一,在清朝京都餐飲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現今,‘二葷鋪之謂隨著共同語影響的擴大而逐漸消失,但其餐所的載體仍在全國各地龐大地存在,對老百姓的飲食生活起著不能割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