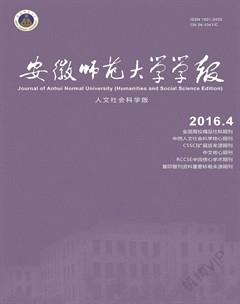知識演進與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遷
關鍵詞: 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知識轉型;變遷邏輯
摘要: 在知識演進的作用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遷經歷了古代知識型、現代知識型和后現代知識轉型等三個發展階段,新舊知識型轉換之間的張力推動著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變革。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遷是一種包容式的發展,新舊組織形態之間不是替代關系而是包容關系,這是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發展變遷的基本邏輯。遵循上述邏輯,有效激活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知識活力,對于推動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有著積極的借鑒與啟示意義。
中圖分類號: G451.7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0012435(2016)04052306
Key words: academic unit,knowledge transformation,transition logic
Abstract: With 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transition,academic unit transformation goes through three stages:classic college knowledge,contemporary college knowledge and postmodern college knowledge.The tension between different stages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unit.When new knowledge standard isnt compatible with college,academic unit need institutional reformation to dispel the tension between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s and help the college keeping the vigor to produce new knowledge.Academic unit transition is a kind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as the 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form is inclusiveness other than substitution.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academic unit can both overcome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unit,and also keep original unit structure,which is the basic logic of academic unit development.Following the logic,that activating the knowledge vigor of academic unit,has positiv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ing meaning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大學基層學術組織是大學從事知識生產傳播應用等學術活動的基本單位,知識發展演進對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變革提出了要求和挑戰。一般而言,人類知識演進經歷了三次重大轉型:一是由原始知識型向古代知識型轉型,二是由古代知識型向現代知識型轉型,三是現在正在經歷著后現代知識轉型[1]46。對應至大學組織的發展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12-18世紀為古代知識型時期;19-20世紀中期為現代知識型時期;20世紀中期至今為后現代知識轉型時期。本文按照知識演進的歷史來梳理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遷的邏輯,探究知識轉型與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遷的歷史聯系,進一步深化對大學基層學術組織演進內在機理的認識。
一、古代知識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
大學濫觴于12世紀的歐洲,大學組織的產生正是古代知識型作用的結果。12世紀,流落到東方的歐洲古典知識重新輸入歐洲,古典知識中蘊藏的理性精神與宗教神學相融合,造就了經院哲學的繁榮,為大學的產生與發展提供知識準備,“中世紀大學的繁榮也是經院哲學的繁榮”[2]109。
就組織形態而言,大學初為師生行會,“很多求知似渴的青年匯集到巴黎和博洛尼亞,他們組成眾多行會組織,構成了最初的大學”[3]45。最初的師生行會僅為保護師生權益的組織,并不承擔學術職能,例如,“同鄉會”(Nation)是相同出生地的學生行會,“教授團”(Faculty)是某一專門知識領域的教師團體,“學舍”(College)則是為學生提供免費的住宿和膳食的場所。因此有學者認為,13世紀“universitas”(university一詞的前身)只是表示大學師生組織,并沒有學術組織的含義。[4]144-145到了中世紀后期(15世紀),同鄉會逐漸消亡;Faculty從“教授團”演變為“學部”此處將faculty譯為“學部”,沒有采用“學院”等譯法,主要是想避免與“college”一詞譯法的沖突。將faculty稱為學部是日本學術界的譯法,有關內容可參見:黃福濤:《外國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頁;張磊:《歐洲中世紀大學》,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29、145頁。,成員包括教師和學生,成為大學實施專業教育的單位;College超出了單純的住宿功能,演變成承擔大學主要教學授課場所的“學院”。師生行會的學術職能逐步凸顯,學院和學部也成為大學基層學術組織制度的肇源。
由于古代知識型堅持形而上學的知識標準,重理論、思辨,輕實踐、操作,世俗知識被排斥在大學之外,大學遠離世俗世界,成為運用理性證明信仰的“象牙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大學知識結構單一,“文、法、神、醫”四科基本囊括了大學知識的全部,而且都被打上了宗教神學的烙印;知識活動單一,知識的目的就是為了傳播上帝存在的合法性,教學成為大學唯一制度化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大學的知識活動大多是圍繞單個學者而進行的,大學處于單層次的結構中,單個的學部或學院散布在大學之中,有時甚至就是大學組織本身。學部和學院雖然已經成為學術組織,但卻很難被稱為大學基層學術組織。
學部與學院成為制度化的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發生在16世紀。在文藝復興的影響下,知識發展逐漸擺脫了宗教神學的禁錮,古代知識型的知識標準遭到強烈地動搖,大學知識開始突破經院哲學的藩籬,轉而關注知識理性對培養理想人格的價值。大學的知識活動開始以提升人的修養、促進人的美德為目的,而不再僅僅是為了證明“神”的偉大,研讀古典文獻和學習語言文法成為大學流行的學術方式。這種變化的結果是語言文法修辭等與經院哲學相對立的古典人文學科知識逐漸在大學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
隨著古典文科知識與經院神學在大學的此消彼長,大學知識逐步呈現出世俗化、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從16世紀開始,大學知識逐漸改變了“混沌不分”的面貌,例如,16世紀的哥廷根大學已在文科學部中新設政治學、自然歷史、地理、外交學、數學、科學、藝術、古代和近代語言等課程[5]。大學知識體系的豐富對大學組織沿著專門化的方向進行分化和發展提出了要求。大學開始分化為雙層結構,典型的例子有,建于1538年的斯特拉斯堡大學,這所大學具有雙層結構,底層是傳授人文學科的學院,在學院之上有一層準大學性質的上層結構。[6]68由此大學基層學術正式形成了,“在歐洲大陸,以法國和德意志地區大學為代表,教師按學科組織成學部,實行集中教學,大學建立在學部(Faculty)的基礎上;在英格蘭,以牛津和劍橋大學為代表,大學內有按照日常生活組建的教師和學生組織——學院(College),大學教學分散在學院中進行”[6]68。學部和學院成為近代早期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兩大基本形態。
二、現代知識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
正如恩格斯所言,“文藝復興以后,自然科學第一次得到系統的、全面的發展”[7]446。17-18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為現代知識型的確立提供了條件。以16世紀人文主義復興為起點,至19世紀現代知識型確立,大學處于古代知識型向現代知識型轉型的階段。
自然科學發展不可避免地消解著建立在舊知識基礎上的價值觀念,大學面臨著人文主義、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等多重知識標準的影響。理性主義將數理邏輯作為理性的奠基,經驗主義把觀察與實驗作為獲取知識的主要方法。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從根本上否定了形而上學知識標準的合法性,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提供了認識論的指導,但在向大學進軍的征途中卻遇到了人文主義的強烈阻礙,在知識的標準以及獲取知識的方法上產生了分歧。知識本源是什么?是感覺經驗還是先天的觀念;知識活動的價值在何處?是培育美德,還是追求實用,或是知識本身就是目的;獲取知識的方法是什么?是回到古典著作,還是通過經驗的歸納或是進行理性的演繹。面對知識轉型的沖突,大學在17、18世紀毫無作為,依舊沉浸在經院哲學與古典文科的泥沼之中。科學革命與思想啟蒙在大學之外轟轟烈烈地進行,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大學日趨保守而失去了知識生產的中心地位,以至于有學者認為“17、18世紀是歐洲大學史上的黑暗時代” [8]2728。這種局面在19世紀得以改觀。以洪堡創立柏林大學為起點,大學主動適應現代知識型的發展需要,對自身的知識標準和認知方法進行調適,大學內部孕育出知識生產與傳播的新制度。
首先,“習明納”的制度化。習明納是一種強調師生對話互動,共同研討的新的教學方法,“從教授和學生非正式的集會演進而來,以師生對話取代教師的獨白”[9]28。在1820年之前,習明納并沒有在大學廣泛采用,“直到1820年,習明納僅少量存在于哲學、語言學等人文學科,且其預備功能多于研究功能。”[10]58在德國政府的資助下,1820年以后習明納從哲學和神學領域向自然科學領域擴張,形式日益正規,并有了固定的場所、獨立的圖書館和有保障的活動經費,成為德國大學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基本單位。習明納不再以訓練學生掌握經典,熟悉文獻為首要目標,而是以培養學生思考能力,培養學生從事創造性研究的能力為價值導向。習明納因此而被成為“科學研究的苗圃”[10]60。
其次,“實驗室”的制度化。實驗室是科學家開展科學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新型的科學家訓練方式”[11]66,不過由于不符合古代知識型的知識標準,實驗室長期徘徊在大學之外。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是,1826年化學家李比希在吉森大學創建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中,李比希徹底打破自然哲學式的傳統教學方式,把理論教學與實驗教學相結合,在完成理論教學的同時組織學生開展系統的實驗研究訓練,使得學生有可能很快掌握并且利用實驗儀器開展科學研究。實驗室不僅是為了教學而存在,而且同時能夠不斷貢獻新的知識。為此,李比希實驗室被稱為“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的近代教學-科研實驗室”[9]25。李比希實驗室在吉森大學的成功意味著觀察和實驗等實證性的知識生產方式已經被大學接受,這對科學知識在大學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有學者所言,“大學的實驗室對科學的價值如同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畫室”[9]27。
另外,“專科教授”的制度化。自然科學迅速發展帶動了知識領域分化加速,大學知識的專門化程度不斷提高。這使得中世紀百科全書式的教授已不可能存在,教授放棄了傳授普遍知識的努力,一個領域的專家可能對另一個領域的專家一無所知,“學者們的最小共同之處是那種對他們來說都是共同的知識,因為他們所研究的領域都是專門化的,互相獨立的。”[12]107傳統英式學院中的全科講師已經不能勝任專科教授的要求,從16世紀下半葉起,蘇格蘭的格拉斯哥大學就采用設立單科教授職位以取代傳統的教師負責全部學科教學的做法,這被伯頓·克拉克譽為“對知識發展具有極大的影響”[12]37。大約在同一時期,一些德國大學也出現了少數教授固定負責單門學科的現象,為講座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克拉克教授這樣評價道,“從1558年萊比錫大學的發展可以看出講座制已基本成型。”[13]44
習明納、實驗室、專科教授,這些都是促使大學接納現代知識型的制度性要素,講座(Chair System)與學系(Academic Department)成為制度化的大學基層學術組織也因此而順理成章。講座組織真正成熟是在19世紀的德國大學中實現的。“1809年,柏林大學在學部下設立由講座教授主持的研究所,并通過制度化的途徑使得講座成為德國大學最基本的教學科研單位。”[14]柏林大學講座制的特點在于:一是專科教授的聘任得以制度化,教授聘任的標準更加看重知識創新的水平,“致力于專門科學研究作為主要要求,把授課效能僅作為次要的問題來考慮。”[15]125二是在講座中通過習明納、研究所、實驗室等制度化的形式,要求教師和學生開展發現式的教學,把學習知識與探索真理結合起來。
學系產生于英格蘭的城市大學。這些19世紀才出現的“新大學借鑒了蘇格蘭大學設立單科教授取代全科導師做法,將系設為大學結構中的最低層級”。 [9]65與德國大學一樣,新大學的系是建立在分化的學科的基礎上,一個系就是一個學科,從而改變了傳統學院囊括全部知識的局面。不過,英格蘭大學學系建立地并不徹底,直到19世紀后期,牛津劍橋仍然強有力地堅持寄宿學院的傳統。學系被美國大學最早普遍采用。“到1890年,美國規模較大的大學都設立系。到20世紀初,所有的大學均設立了系或學院的建制。”[10]194
正是由于講座和學系等基層學術組織的制度化,科學知識在大學活動獲得了建制,取得了穩定的組織形態,贏得了持續發展的動力。不僅如此,大學知識的包容性也得以拓展,大學知識不僅來源于理性思辨,還可以來源于感覺經驗;大學知識的認知方法不僅需要注重文本和思辨,還可以接納觀察、實驗等實證的方法。這極大地改變了大學知識的圖景,大學不僅可以生產和傳播古典文科知識,還包括了物理、化學、生物等現代意義的學科知識,知識分類愈加精細,大學因此而重返知識生產的中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講座和學系組織的興起后學部和學院從事知識生產傳播的學術職能逐步弱化,更多地承擔起大學行政管理的職能,學部和學院逐漸蛻變為大學的中層組織。
三、后現代知識轉型中的大學基層學術組織
吊詭的是,現代知識型在20世紀的發展反而成為大學知識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從20世紀后半葉起,大學再次陷入知識轉型的持續張力與沖突之中。首先,現代知識型所遵循的知識分化和專門化的發展邏輯導致了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不斷分化與膨脹,增加了大學的離散性和管理難度,大學組織甚至面臨著分裂的危險。如何提高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結構的整合性和協同性成為大學組織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其次,現代知識型所堅持的“學院科學”的規范阻礙了大學對社會需求的回應,在社會問責呼聲高漲的20世紀后半葉,大學已經不能夠再以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為名而回避自身的社會責任。
后現代知識型在20世紀后半葉的發展為大學解決這一發展難題提供了基礎。后現代知識型的突出貢獻在于強調知識的多元標準,尤其對現代知識型所推崇的知識的客觀性、普遍性和價值無涉提出質疑,認為知識只能是文化情境下的產物,不存在純粹客觀和價值中立的知識。由于后現代知識型強調知識生產的情境性,這為大學知識活動走出學院科學的局限,承擔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奠定了理論基礎。在后現代知識轉型的影響下,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發展呈現出更多的模式選擇,呈現出新的特點。
其一,跨學科組織興起。由于更多的知識生產發生在以應用為目的的情境之中,“基礎”與“應用”之間、理論與實踐之間不斷交互,大學基層學術組織需要克服規模小、學科單一的不足,提升解決復雜科學問題和重大現實問題的能力。于是在二戰之后,跨學科組織在大學普遍興起。大學通過建立形式多樣的跨學科課題組、跨學科計劃、跨學科實驗室、跨學科研究中心等,在不同學科的講座、學系組織之間建構出矩陣式的組織結構,避免了大學知識因過度分化而潛在分裂的危險,從一定程度緩解了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知識生產專門化與知識應用綜合化的張力,為學系、講座、研究所等傳統學科組織在大學的繼續存在提供了制度空間。正如蓋格(Geiger,R.L.)所言,“美國大學當初在院系組織內部成立跨學科研究組織,或者單獨成立校屬的跨學科研究組織,為的是開展傳統院系組織不能開展的問題導向的項目研究,是大學基層學術組織張力的‘緩沖器,起到緩沖的作用”[16]。
其二,異質性增強。由于意識到知識與社會發展緊密相聯,科學發展對公共利益影響攸關,更多的團體和組織希望參與到大學知識生產活動中來,知識不再局限于學者個體的認知行為,也不單純是知識共同體內部互動的實踐行為,日益演變為“包括科學家、政治家、企業家,以及其他多種社會角色磋商互動的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17]16。發展科學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建立緊密的聯系。正如斯坦福大學亨利·埃茲科維茨教授的“創新三螺旋(Triple Helix)”理論所述,大學與政府、企業在知識創新中建立起交互作用、協同演進的關系,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教學科研活動也與產業創新活動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與交流關系,無論是在成員構成、績效目標或是知識生產方式上,基層學術組織的異質性顯著增強。
其三,組織結構也更加彈性靈活。由于學術研究的前沿問題往往是動態變化的,研究不同的課題往往需要積聚不同的研究人員和不同學術資源,因而高水平大學里始終動態維持一批以項目為基礎的基層學術組織。與傳統基層學術組織不同的是,這些新型基層學術組織圍繞某一問題或研究任務設立,組織形態多樣且結構化程度低,沒有學科、時間、規模的約束,對建制的穩定性也沒有特別的要求,能夠根據工作的需要,隨時集中不同學科人員和資源,在完成項目和任務后自行決定是否繼續還是取消。組織結構的彈性和靈活性大大增強了大學知識生產的適應性,使得大學底部充滿了知識創新的活力。
四、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遷的邏輯反思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在新舊知識型轉換之間的張力推動著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變革。當新的知識標準不能夠在大學里被兼容時,基層學術組織就需要在制度上進行變革,用以消解新舊知識型轉換之間的張力,確保大學進行新知識生產的活力。現代知識型功能目標確立后,大學需要更新基層學術組織以適應科學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活動,為此,大學衍生出了講座和學系組織,創造出習明納、實驗室和專科教授等新的知識制度,用以包容知識分化和專門化不斷提高的趨勢,為觀察、實驗等實證式的知識生產方式提供制度支持;在后現代知識轉型的過程中,為了保證大學能夠承擔起生產傳播社會性、境遇性知識的責任,避免大學因知識過度分化而導致組織分裂的潛在危險,基層學術組織又通過組建跨學科組織、增強組織的異質性以及創造出彈性靈活的組織結構,使得大學能夠繼續保持知識活力。更加值得關注的是,雖然新舊知識型之間充滿著持續的張力與沖突,大學基層學術組織演變并不是沿襲線性的邏輯,也即新的組織形態并沒有替代傳統組織形態,而是將舊的組織形態通過新的組織形態得以擴展,并且重新鞏固自身在大學的合法性。例如,講座和學系組織的制度化并沒有替代傳統的學部與學院組織,學部與學院繼續在大學中存在至今,只是淡化了知識生產的學術職能,轉換角色成為大學的中層管理組織;跨學科組織的出現也沒有替代傳統的學系和研究所,而是在跨學科組織與學系、研究所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彈性靈活的矩陣結構,用以承擔學系和研究所不能承擔的知識職能,為學系和研究所在大學的繼續存在拓展了空間。
因此,我們認為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演進是一種包容式的發展,新舊組織形態之間不是替代關系而是包容關系,建立新的學術組織,既克服傳統組織結構的不足,又不打破原有的學術組織結構,這是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發展變遷的歷史經驗。正像伯頓·克拉克所言,“歷史上高教系統的變化通常采用這樣一種折衷方式,即新的單位繞過舊的單位,而舊的單位依然存在”[18]。可以預見提高基層學術組織形態和結構的多樣性和適切性應作為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革與發展的主要任務。
推動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革對于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也具有重要而緊迫的現實意義。當前,我國正處于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推進期,“大學在創新驅動發展中與國家同行”[19]242已取得共識。從大學組織的發展邏輯來看,基層學術組織在大學中居于基礎性地位,基層學術組織的知識活力直接決定著大學的學術水平,也從整體上決定著區域或國家高等教育系統的創新能力。因此,大學創新能力提升必將最終落腳于基層學術組織知識活力的提升與釋放。注重激活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的知識創新活力,不僅是近千年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邏輯,也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現實選擇。從我國大學發展現狀來看,創新驅動發展需要建立知識生產的協同機制,大學基層學術組織不僅要成為大學知識活動的基本單元,更加要成為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中聯結多學科、多主體之間的組織界面,為推動知識跨組織邊界流動,合作實現創新目標提供機制保證。目前,大學基層學術組織“分散、封閉、割裂”的狀態還未能得以根本改變,基層學術組織知識創新活力不足仍是制約我國高等教育水平提升的關鍵因素。在此背景下,推動大學基層學術組織變革,提高基層學術組織協同知識創新的能力應當成為當前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重點和突破口。推動大學基層學術組織改革必須理性,必須重視汲取歷史經驗。當前,國內一些大學在探索基層學術組織改革中呈現出片面追求“大平臺、大團隊、大項目”為主要特征的發展思路,忽視了傳統學科組織的歷史貢獻和存在價值,任其發展勢必破壞基層學術組織多樣化的生態結構,也違背了大學基層學術組織發展的基本邏輯。應該以提高基層學術組織形態與結構的多樣性和適切性為目標,既要建立面向學科、比較穩定的基層學術組織,也要建立面向問題、動態的基層學術組織;既要建立單一學科的基層學術組織,也要建立跨學科的基層學術組織;既要建立實體性的基層學術組織,也要建立虛擬形式的基層學術組織。只有進一步提高組織結構的彈性和靈活性,提高基層學術組織知識生產的包容性,才能真正適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要求。建立更加開放、多樣和包容的基層學術組織結構形態應成為大學改革與發展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石中英.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
[2]涂爾干.教育思想的演進[M].李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Haskins,C.H.The Rise of Universities[M].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1.
[4]Pedersen,O.The First University:studium Generale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5]黃福濤.歐洲高等教育近代化的類型與道路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1999(1):9498.
[6]希爾德·德·里德-西蒙斯.歐洲大學史:第2卷[M].賀國慶,等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
[7]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菲利普·阿特巴赫.比較高等教育[M].符娟明,等譯.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5.
[9]伯頓·克拉克.探究的場所——現代大學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緒,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0]賀國慶.德國和美國大學發達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1]華勒斯坦.學科·知識·權力[M].劉健芝,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
[12]伯頓·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M].王承緒,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3]Clark,W.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14]伍醒.從講座制起源看19世紀大學學科制度化的變革意義[J].中國高教研究.2013(8):3742.
[15]弗·鮑爾森.德國教育史[M].滕大春,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6]Geiger,R.L.Organized Research Uints:Thei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Research[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90(1):119.
[17]李正風:科學知識生產方式及其演變組織[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18]萬玉鳳.高校在創新驅動發展中與國家同向前行[N].中國教育報,20150727(01).
[19]伯頓·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M].王承緒,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
責任編輯:馬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