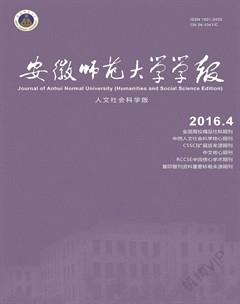費赫爾對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哲學批判
溫權
關鍵詞: 雅各賓主義;德性共和國;政治道德;意識形態;絕對自由
摘要: 費赫爾認為法國大革命從民主走向專制源于由“指券體系”所催生的國家干預政策,與之后有關“德性共和國”的虛假預設。它們將抽象的道德理想投射于具體的政治領域,并借助暴力手段使之泛化到社會各層面,從而強制營造出德性-國家-民主的統一,政治民主被道德專制取代,該過程本質上是哲學層面的絕對自由應用于現實社會的結果。
中圖分類號: D0-02;K561.41 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0012435(2016)04047506
Key words: Jacobinism; moral republic; moral politics; ideology; absolute freedom
Abstract: Fehér believes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democratic French Revolution toward despotism is caused by state intervention policy created by the "assignat system", and the following false presupposition of "moral Republic". They will abstract moral ideal projection in specific areas of politics, and with the help of violent means generalize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thus forced to create a unity of virtuenationdemocracy. Democracy is replaced by moral dictatorship, and the process essentially is an application of philosophically absolute freedom to the social reality.
以雅各賓派的獨裁專政收場的法國大革命,在政治與哲學層面留下了難解的謎團:由啟蒙主義主導的激進民主制度,為何在政治上日趨保守集權?對此,費倫茨·費赫爾(Ferenc Fehér)認為,革命初衷的變質與恐怖專制的興起,是一個從經濟舉措到政治運行,再到哲學預設,三者逐級異化的過程。首先,以“指券體系”為代表的經濟政策,作為“一個革命的措施,它將永久革命張力的不可避免的要素注入進連續的革命進程中。”[1]43從而,在經濟規律為政治指令所取代的同時,推行該政策的共和國也日趨成為剝削人民大眾的權力機器。其次,由激進政治制度塑造的“德性共和國”,在模糊政治與道德界限的同時,凌駕于律法之上,使不斷革命的意識形態蛻變為訴諸暴力以鞏固政權的世俗神祗。再次,大革命是一次倉促的哲學冒險。哲學中“德性共和國”的出現以及“救贖政治”的達成,“既不能產生任何肯定的事業,也不能作出任何肯定性的行動;它所能做的只是否定性的行動;它只是制造毀滅的狂暴。”[2]118因此,革命后期雅各賓主義的恐怖專政,是抽象的哲學理念付諸實踐而產生的惡果。
費赫爾通過分析哲學的抽象自由與“德性共和國”之間的內在關聯,從道德與政治的內在張力中,找到了困擾大革命民主進程的致命頑疾。在他看來,對二者關系的曲解,既是大革命走向失敗的直接誘因,又是啟蒙理性固有偏執情緒的必然結果。
一、“指券體系”與行政指令常態化:經濟邏輯還是政治邏輯
由大革命所締造的共和國,建立伊始就處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中,在客觀上促使其領導階層采取一系列臨時但頗具效力的行政舉措。反映在經濟層面,就是為平抑物價而強制施行的指券金融體系。“1789年8月初,法國國庫空虛,舉債又連遭失敗。社會動蕩所導致的消費的畸形增長,使硬通貨越來越短缺。以這種或那種形式發行一種新貨幣的迫切性已被提上日程”。[3]161鑒于此,由君主立憲派組成的事務委員會,借助臨時成立的特別銀行,發行了價值4億利弗爾的指券,“一方面設想發行一種真正具有貨幣效能的指券,遏制商業蕭條,恢復市場經濟活力;另一方面剝奪教會對其財產的經營管理權”。[3]163顯然,指券發行的初衷,原本是想在緩解國內通貨膨脹的基礎上,促成財政制度的良性改革。
但以自由貿易為前提的指券體系,不久就轉化為彌補財政赤字和償還國債的手段。指券的不斷貶值造成新一輪的物價飛漲,人民群眾入不敷出。然而,政府卻“不提‘資本家投機集團,更不提限價,強調的仍然是貿易自由和經濟自由。”[3]308于是,大規模的暴動和社會動蕩頻發。經濟上不健全的指券體系,隱含著國家與民眾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費赫爾指出,“國家要么從流通領域的大量貨幣中征用足夠數量的貨幣單位以滿足國家的需求,要么向所供應的貨幣中強制注入一定量新的貶值單位,以滿足家庭的需求”,但無論如何,它“在理論抽象方面仍然與法國革命的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1]53換言之,發行指券作為大革命的應急方案之一,片面強調了國家政權之于公民生計的絕對優先性。而臨時貨幣的貶值也“并不代表一個國家的破產,而是代表一條經濟道路上,在這其中,數以萬計的工薪族被迫遭受一個稱為大革命的抽象物的剝削。”[1]51費赫爾認為,后者無疑會產生以下兩方面后果:
第一,以應急政策為先導的指券體系,幾乎完全遮蔽了貨幣自身的運轉功能,并以籠統的革命性質取而代之。如此一來,“貨幣體系的‘革命性質意味著其內在規律不會表現出商品生產的水平和貨幣發行量之間的一致。”進而,“猛烈的通貨膨脹擾亂了本已經脆弱的窮人的家庭預算,……其政治后果……只能通過赤裸裸的暴力、刺刀來解決。”[1]55該現象反映出革命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普羅大眾真實的角色轉換。費赫爾認為,一旦君主制被推翻后,“群眾被看做市民,那他們似乎就完全沉浸在諸如面包價格這樣的庸俗問題之中,尤其在城市場景之中更為如此。”[4]8況且,為大革命所建立的“自由國家事實上是與自由市場相連的,公民也是自私自利的人。”[4]215因此,人民群眾的生計問題與革命能否營造出良性的經濟環境息息相關。隨著經濟政策向國家政權的傾斜,指券“持續不斷的貶值承認了預算需要政治和時間的優先性,甚至不惜犧牲以工資為生計的人的利益。”[1]50激化了人民與共和國之間固有的矛盾,導致革命政權的不穩定。
第二,指券體系的推行及其后續賦稅改革的失敗,促使政府加大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漸顯政治專制主義的端倪。一方面,“經濟學被一種武斷的方式政治化,同時,由于其自身不可避免的規律被宣稱是‘自然的。公民,他們所有關于這些問題的決定都應該作為重要指導,卻仍被邊緣化,從未被咨詢過。”[1]53經濟規律被政治的一廂情愿取代后,公民基本的利益訴求被忽視。面對群眾情緒的反彈與殘酷的斗爭環境,極端的政治手段在所難免。于是,“部隊,甚至暴力,作為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被納入到系統中來。……革命者只能采取兩種方式,一種是對民眾強加新的賦稅,另一種是強行臨時實施各種‘革命的經濟政策。……它們通過不同的方式把革命引向自殺(破壞自由)的漩渦。”[1]54經濟體制的泛政治化,把公民納入不斷革命的怪圈。隨著暴力手段的介入,自由靈活的市場貿易被簡化為國家的物質需求,原本獨立的經濟個體在服從行政命令的同時,在政治上也被視為彼此平等的集合體,并與抽象的國家相等同。在這種情況下,革命者就“產生了對‘革命團結的盲目依戀,失去了在客觀政治形勢發生劇烈變化時的應變能力。”[5]289他們作為具體政策的制定人,以革命的名義,為維護教條的行政指令成為新的獨裁者。
由指券體系所引發的行政指令常態化及其對經濟的粗暴干預,突顯了締造共和國時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之間的內在矛盾。“‘政治邏輯,旨在創造一種‘自由社會的動力,是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因素。……即使當社會經濟藍圖開始出現分歧,或是彼此之間互不相容的時候,這種常見的自定義在政治層面經常是同一的。”[1]20大革命的領導者旨在顛覆與舊制度相關的一切社會特征包括行將就木的經濟體系,但其強有力的政令不能掩蓋他們自身特有的階級屬性。指券體系的推行,從根本上來說,是掃除封建障礙,刺激工業資本持續發展的政治行為。這與貧苦民眾的根本需要大相徑庭。因此,為應對“一種群眾的情感:對工業資本主義潛在上升的一種懷疑的憎恨,工業資本主義發現了唯一的出路:一種教化的專政高于需要的遠景。”[1]106這表明,革命的自由只能是資本積累的自由,被這一目標所策動的大部分民眾,始終被排除在外。為彌補這種缺陷,革命者在宣揚理性的同時,一方面冠之以抽象的政治平等,另一方面又對其反對意見殘酷鎮壓。盡管他們“通常都炫耀自己的理念具有‘最高的合理性。但事實上,他們都是理性最差的學派。他們的內心充滿了國家干預論的主導精神。”[4]204脫離群眾的行政指令逐漸成為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權威,在啟蒙理性的包裝下又引申為絕對平等的幻想。而盲目的“均權主義……既摧毀傳統的等級制度,同時又使這種制度固定化,因為它在掏空等級制度內容的同時,又以法律的形式使之無限延續下去。”[6]116
指券體系的失敗是抽象的平等在經濟層面掉入專制陷阱的開端。大革命中的所有派別都以實現廣大群眾的自由與民主為己任,但狹隘的經濟訴求無法承載如此長遠的政治理想,它勢必演變成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的角力,并以少數人的獨裁專制宣告終結。革命者們不得不確信,“無論是自然條件還是‘經濟規律都不能抵制人類需要的動力,更進一步而言,他們是武斷的、無拘無束的夢想家,對他們來說,絕對的平等高于自由。”[1]57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對抗造成了國家對廣大民眾經濟平等與政治自由的雙重否定。所以,“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共和國憲法從來沒有確實變做一個‘民主政體;在‘自由與‘平等的假面具之下,暴虐和專制橫行無阻。”[7]239
這無疑釋放出一個危險的信號:共和國賴以為系的平等與自由理念,將蛻變為粗暴的政治教化;領導者擁有這項權力的合法性也不取決于廣大群眾的認可。為保證其政令的權威性,一種更為抽象的衡量標準勢在必行。于是,愈加極端的政權形式呼之欲出。這無疑為雅各賓派“德性共和國”的執政理念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二、“政治道德”與人民主權邊緣化:道德預設還是政治預設
雅各賓主義的興起,按費赫爾的理解,是“意想不到的、不可預知的歷史時刻三種趨勢空前匯聚的結果,……這三種潮流分別是:山岳派左翼激進派的政治運動,憤激派對社會與經濟的煽動,指券內部動力體制的呈現”。[1]20雅各賓派的執政理念充斥著激進的革命訴求,試圖通過劇烈的社會變革,在平復所有困擾共和國問題的基礎上,構筑完全正義的政治體制。用羅伯斯庇爾的話來說,該派別追求的目的就是使廣大群眾“和平地享受自由與平等”,并建立“永恒正義的王國。”[8]170
然而,為羅伯斯庇爾所奉行的政治原則,在強調全民參與的同時,還隱含著一條先驗的道德預設,即共和制度的良性運行與廣大民眾的善良意志并行不悖。因此,“這種共和政治可以用現實的完整形式達到公意,前提是所有參與者在道德上都是善的。同時,在一個腐朽文明當中道德的善只能通過一個正確的共和政治來獲得。雅各賓派堅信,他們通過宣稱道德政治和政治道德來達到目標。”[1]71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看待政治與道德之間的關系?該設想被納入民主實踐后,能否真正兌現它的諾言?歷史證明,他們早已誤入歧途。
從宏觀上來看,為政治道德所建構的“德性共和國”不啻為狹隘的復古主義幻想,從來不具備穩固的現代政治基礎。因為其合法性不以剛性的律法為必要條件,而是以柔性的道德意志為基本前提。所以,“在雅各賓派的解釋中,‘共和國包含兩個實質性要素。首先,與個人野心、貪婪和利己主義相比,它被看作是‘社會時空擴展和集體意志。其次,與所有革命者中的政治敵人相比,它被看作美德的體現和協商,而這些政治敵人在教化的政治和政治化的道德中顯現出‘腐敗和‘邪惡。”[1]74抽象的衡量標準,使國家在區分敵友時變得武斷且隨意。作為行政指導的公民德性,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解釋,只能流于主觀的膚淺直覺。反映在群眾層面,就是民粹主義的輿論或意識形態;而它一旦為領導者所采納,必然產生排它性的權威崇拜。上述兩種情形無一例外的出現在雅各賓派統治的共和國之中。因此,雖然“革命召喚了一個新的階級(人民群眾——筆者注)參與政治生活,……但輿論變成了一種力量,必須和它商量,并倚重它的協助,借以支持政府。”[9]45它既是群眾的公意,也構成領導者甄別善惡的直接來源。于是,在道德至高無上的口號下,“德性和恐怖盛極了一時;因為‘主觀的德行的勢力既然只能建筑在意見之上,它就帶來了最可怖的暴虐,它不經過任何法律的形式,隨便行使權力。”[7]421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種由意見形成的道德暴力,最終的受害者卻是產生它們的普通民眾。
從中觀上來講,由政治道德所引導的民主體制,實則是一元獨裁專政對多元黨派政治的壓制。它既體現為雅各賓派對人民主權的踐踏,也意味著政黨之間的平等協商化為泡影。這是革命者對代議制民主片面理解造成的惡果。盡管雅各賓派承認“政府的實際權力應該由選出的有能力處理國家事務的少數個體來執行。”但“他們也是盧梭的追隨者,追隨他對代議制的批判及其公意觀念。……他們堅定地相信‘人民總體上不能管理自身”。[1]99如此一來,雅各賓派就切斷了民主選舉與行政權力之間的有機聯系。并將對“德性共和國”的期許,轉變成對人民與其它政黨的雙重敵視。在不確定公民是否具有他們所要求的高尚品德之前,為后者所選出的政治代言人顯然不具有相應的合法性。況且,“在政治異常興奮和‘狂熱的時候,……新的最高統治者通常都會膨脹得與所有部分都不相稱,甚至在新的政治形而上學中得以神化”。[4]210被神化的正是雅各賓派尤其是羅伯斯庇爾對自身執政理念的盲目自信。他們自認為是政治道德的代言人,且天然是衡量民眾善惡與否的唯一權威。故而,“在政治上,雅各賓派不容忍任何競爭對手。……對他們來說,只有一個中心、一個觀念、一個主權是多么自然。……即在‘德性共和國中只能有一種意志,導向中心的意志。”[1]116在這點上,雅各賓派雖然是絕對平等主義的支持者,但他們自身卻游離于這種平等之外,并成為高于乃至主導平等的世俗神祗。
從微觀上來說,被政治道德所裹挾的普通公民與政策的執行者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藩籬。其中的原因在于,當雅各賓派“很少任用全權代理人和地方活動分子時,他們是雇傭官僚主義者而不是代表,這些官僚主義者既不是被選出來的也沒有地方根源,他們直接依靠中央權威。”[1]95這就使政府與公民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脫節。作為領導者對群眾的組織形式,它直接反映出雅各賓派對待人民群眾的兩面態度。革命者既期望他們的政治構想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得以實現,又擔心后者在激烈的社會動蕩中失控,危及自身的政權。“革命精英對群眾實行組織化的做法,突出地反映了他們對于群眾的一種既愛又恨、既容又怕的復雜情感。”[5]40這與政治道德所要求的一元政治不無關系。為羅伯斯庇爾所強調的公民道德優先性,實則是雅各賓派對民眾實施教化的政治權威性。而該團體內的領導成員,自然就是高于普通民眾的道德監護人。執政者與群眾的差異化意在營造群眾自身的同質化。經過教化的“‘人民成為……善良意志的不加區別的總和:經此,代表制被排除了,革命意識于是以個人意志為名義,并以此為出發點重構了一個想象的社會。”[6]37革命者與民眾之間的隔閡,毋寧是抽象的道德理念應用于具體的政治實踐時,必然遭遇的社會后果。
雅各賓派的“德性共和國”之所以淪為獨裁專制的庇護所,導源于它奉行的政治道德理念曲解了平等與自由之間的關系。羅伯斯庇爾曾一再強調美德與平等之間的同一性。他指出,“我所說的是公共美德……而不是什么別的東西。但是因為共和政體或民主政體的實質是平等,所以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熱愛祖國必須包括熱愛平等在內。”[8]171與共和政體相結合的平等,在革命者看來,還是人民群眾擺脫王權達成普遍幸福的必要前提。在羅伯斯庇爾看來,較之于個體的自由,平等往往具有絕對的優先性。這就使以平等為內核的政治道德成為實現公民幸福的手段。于是,道德自身下降為一般的幸福原則,并根據領導者的主觀意愿,被強行投放于公民的日常生活領域。如此一來,必然在國家權力方面引起巨大的惡果。“正像它在道德方面所造成的一樣,……主權者想根據自己的概念使人民幸福,于是就成了專制主義;人民想放棄自己追求自身幸福這一普遍的人類要求,于是就成了反叛者。”[10]209不難看出,平等對自由的壓制,意味著政治與道德之間的關系發生了顛倒。雅各賓派在突顯公民幸福的同時,“把國家和社會、政治義務和道德義務混為一談”,這是其“形而上學的國家論的主要錯誤。”[11]70正確的政治準則“絕不能從每一個國家只要加以遵守就可以期待到的那種福利或幸福出發……而是應該從權利義務的純粹概念出發”[10]145。這就要求自由的個體對道德原則的自律性接納。換言之,指引共和國前行的不是以絕對平等為標志的政治道德,而只能是彰顯個體自由的道德政治。雅各賓派正是由于歪曲了道德之于政治的絕對優先性,才逐步否定了人民自由在政治實踐當中的積極作用,進而以抽象的道德專制取而代之。
問題的關鍵在于,民主自由的消失與道德專制的出現,卻是大革命向往自由的結果。這就涉及絕對自由的悖論,及其對大革命進程造成的深遠且負面的影響。
三、“絕對自由”與革命正義虛無化:哲學實驗還是政治實驗
將大革命只看作純粹的政治事件,并不足以涵蓋其所蘊含的歷史意義。在更為寬泛的層面上,它是抽象的哲學自由遭遇現實的世俗權力時帶來的全新體驗。“大革命闖進了一個真空地帶,或者不如說,它在直到昨天還屬于禁絕地、但突然間被僭入的權力領域里迅速蔓延開了。……意思就是說,公民社會……正在擺脫象征性的國家權力,同時擺脫國家的法度。”[6]69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意在同之前傳統的權力機制徹底決裂。這表明,象征王權的政治體系及其運用的封建法度,必然成為大革命所要清算的對象。反映在哲學領域,它包括形下與形上兩個層次的內容:
一方面,大革命對封建專制的批判,要求徹底祛除王權之于自由的荼毒。因此,對后者的象征性代表——國王的審判與處決,在革命者尤其是雅各賓派看來,就顯得尤為重要。費赫爾認為,該舉動“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目標。作為哲學的革命者,他們想監督君主政體原則象征性的葬禮,作為一種實現哲學承諾的行為……他們想在將要形成的新共和國德性和革命矛盾的過去之間劃一條明確的區分界線,……國王的死刑看起來完美地為這兩個目的服務”[1]129。審判并處決國王的正義性何在?妥善地回應該質疑,直接關系到革命運動的合法性。然而,在費赫爾看來,革命者的行為無法自圓其說,后者甚至只能被視為政治上消極的逃避。 “當我們為了反動地懲罰哲學的罪行而成為勝利者時,同意特赦是集體怯懦的行為,也是極其專制的基礎,而不是一個自由共和國的建構行為。最后,在政治上,哲學實踐的血腥應用是通過斬除一個人而排除一個系統的象征,這是一次整體的失敗。”[1]126接受懲罰的國王只是抽象的封建專制象征性的犧牲品,而革命者對他的判決卻將非理性的暴力因素引入法律當中。因此,專制的毒瘤并沒有被根除,而是以審判的形式完成了由君主到革命者的讓渡。之后雅各賓派的獨裁政治證明了這一點。由此可見,這一行為根本不具有它所宣揚的正義性,而革命的合法性也只能從法律之外的領域獲得佐證。
另一方面,庶民對王權的戰勝,最初表現為公民自由對之前法律制度的否定。故而,革命是超然于原先正義體系之外的全新體驗。它意味著一種編年體上的斷裂。鑒于此,“國家再生需要新人和新習慣,人民要在共和主義的模子里被重新鍛造。因此,日常生活的所有犄角旮旯都要被檢查,找出舊制度的腐化痕跡后徹底掃除,以做好迎接新制度的準備。”[12]73但行之有效的重塑方案卻沒有被及時提出,反而以籠統的自由觀念敷衍了事。其惡果是公民對自由的擯棄。這集中體現為,“在新的、由獲勝的人民從君主那里借用的主權概念中,……它可能會陷入自相殘殺的斗爭之中,從而使國家難以控制。它可能蘊涵著各種各樣的政治風暴,從而使其成為自己的最壞敵人,并把民眾帶入到一種呼喚著‘我們不想要自由的集體政治歇斯底里癥之中。”[4]211在費赫爾看來,這是關于自由的空洞說辭向歷史開出的空頭支票,它必然伴隨著理性的真空以及蹩腳的民主與專制思想的媾和。
自由的得而復失及其與正義之間的張力,實則是大革命在哲學層面遭遇危機的直接表現。自由與正義各自的悖論,是大革命自身無法克服的痼疾。“法國大革命從‘哲學得到第一次推動。但是這種哲學起初只是抽象的‘思想,不是絕對‘真理的具體理解——兩者之間有著一種不可測度的區別。所以,‘意志自由的原則反抗著現行的‘權利。”[7]417催生大革命的自由理念,是與現實相分離的抽象哲學設想,本身并不具備健全的政治實踐方案。內容的貧乏導致它在棄絕現行制度后,變為純粹的否定力量,不具備絲毫的建設性。由于自身的無規定性和破壞性,它只能表現為革命的狂熱。后者“所希求的是抽象的東西,而不是任何有組織的東西,所以一看到差別出現,就感到這些差別違反了自己的無規定性而加以毀滅。因此之故,法國的革命人士把他們自己所建成的制度重新摧毀了”。[13]15在這樣的情形下,以穩定的律法為前提的正義觀,顯然與大革命對正義的定位格格不入。在以絕對平等和道德政治為目標的絕對自由中,“一切社會階層,都消除了。……它的目的就是普遍的目的,它的語言就是普遍的法律,它的事業就是普遍的事業。”[14]116于是,革命的正義只能表現為不斷地清除與自由相背離的人與物,喪失了它對自由的規約作用。與此同時,“哲學的革命者……這種巨大的,對所有類型苦難的敏感,……使他成為絕對善的化身,……因此,在自由辯證法的旋轉軸上,他自由地做任何事情。”[1]82一旦絕對的自由使普遍的律法轉化為個體的情感,革命的正義也就因此拋棄了它的理性支撐。當原先的革命者成為善良意志的代言人,并再度走上神壇時,所謂的正義就只能充當他們在任意殺戮后為其辯護的丑角了。所以,絕對的自由及其所彰顯的革命正義,“所能作的唯一事業和行動就是死亡,而且沒有任何內容、沒有任何實質的死亡,因為被否定的東西乃是絕對自由的自我的無內容的點;它因而是最冷酷最平淡的死亡,比劈開一個菜頭和吞下一口涼水沒有更多的意義。”[2]120絕對自由毀滅了正義的可能性,也從哲學層面說明了大革命走向專制的必然性。不被理性法則所制約的抽象觀念,在現實層面的盲動,毋寧說是一次哲學的冒險。而其代價,則是大革命失敗后繼任者連續的專制統治。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革命是以啟蒙主義為先聲的政治實驗。在它的背后,隱含了政治道德以及絕對平等的觀念同現實之間的巨大張力。表現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它不可避免地誘發了人民主權的缺失,并促使道德專制的形成。從這點上來看,大革命的失敗無疑是以強權手段為先導的“救贖政治”的失敗。然而,它還是以人類自由解放為目的的哲學實驗。其中充滿了對永恒正義和絕對自由的期許。抽象理念與具體現實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最終醞釀出極端的血腥殺戮,造成了大革命對啟蒙主義深刻的逆向回應。當大革命遭遇政治和哲學的雙重困境時,它所倡導的民主理想就伴隨著行政指令的常態化而被革命自身所凍結。
不可否認,大革命開啟了人類之于自由民主的積極探索。但以抽象的哲學觀念為指導,并將其納入社會實踐當中,勢必引發哲學理念同政治規劃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政治運動只能被視為推進社會進步的手段,它無法涵蓋社會民主自由的全部內容;另一方面,在哲學層面得以自洽的抽象自由也僅僅具有導向性功能,它不能被當作改造社會的模板而妄加推行。從這點上來看,大革命對后世的啟示,不啻為以道德的視角全面審視一度被合理化的啟蒙精神,從而為后者設定必要的限度。只有這樣,真正的民主自由才能得以實現,哲學的預設才能與政治實踐在現實層面獲得統一。
參考文獻:
[1]費倫茨·費赫爾.被凍結的革命——論雅各賓主義[M].劉振怡,曹麗新,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4.
[2]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3]王養沖,王令愉.法國大革命史[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
[4]費倫茨·費赫爾.法國大革命與現代性的誕生[M].羅躍軍,等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0.
[5]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6]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M].孟明,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7]黑格爾.歷史哲學[M].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8]羅伯斯比爾.革命法制與審判[M].趙涵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9]保爾·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國語言[M].羅大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10]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11]L.T.霍布斯.形而上學的國家論[M].汪淑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2]林·亨特.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M].汪珍珠,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13]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14]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責任編輯:陸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