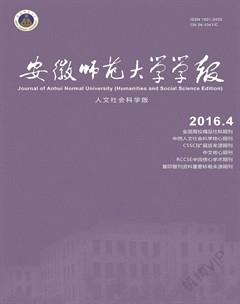老人自死習俗:“鯀復生禹”神話與歷史背后的真相
徐永安 杜高琴
關鍵詞: 老人自死;鯀復生禹;天問;巫術思維
摘要: 依據愛德華·泰勒的“萬物有靈觀”、弗雷澤的原始巫術思維原理、范熱內普的“過渡禮儀”等人類學經典理論,剖析“鯀復生禹”神話,鯀-禹部落(家族)具有雨師職能。去掉神話歷史化、歷史道德化的迷霧,鯀的被殺背后真相是自死。“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老人自死之后的“三年之喪”的儀式。儀式中鯀向禹轉移的“神靈”形象、儀式的空間特性都體現了源自祖先顓頊的部落傳統。“鯀復生禹”神話具有老人自死習俗與成人禮儀雙重意象。以禹為核心,顓頊-鯀-禹部落在三代史的開端具有特殊地位與重要性,老人自死是那個時代的敬老、孝道的重大儀式。
中圖分類號: G112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 10012435(2016)04049710
Key words: the elders' lone death custom; Gun died and was reborn as Yu; Tian Wen; magical thoughts
Abstract: Based on Edward Taylor' s animalism,Frazer's theory regarding the primitive magical thoughts and Gennep's classic theories on anthropology in his book Les Rites De Passage,analyze the famous mystery—“Gun died and was reborn as Yu.” It turns out the Gun-Yu family plays a role as the rainmaker in the tribe.The real reason behind Gun's death is that he chose the way of lone death.The poem “why not release Gun after imprisoning him for 3 years in Yu Mountain” suggests the custom that after the parents' death,the offspring has to be in mourn for 3 years.Both the “God image” Gun transfers to Yu and the spatial features of the ritual indicate the custom has been passed from the tribe whose ancestor is Zhuan Xu.There are traces of coming-of-age ceremony and the elders' lone death custom in the “Gun died and was reborn as Yu” mystery.With Yu as the core,the Zhuan Xu-Gun-Yu tribe plays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par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hree Dynasties.The elders' lone death custom is regarded as a way that people shows their respect to the elders.
關于老人自死傳說的研究,我提出解釋理論是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中的“萬物有靈觀”與詹·喬·弗雷澤《金枝》中的原始巫術思維原理(即老人自死習俗的本質是民俗信仰),并結合范熱內普的“過渡禮儀”理論,解析了典籍中“堯舜禹禪讓”的真相是老人自死習俗,周期三年,并在商末周初,演化成“大夫七十而致事”的官禮、“三年之喪”的喪禮。①本文在此基礎上,繼續依據上述經典人類學理論,旨在論證,“鯀復生禹”(《天問》中“伯禹愎鯀”)的神話背后,包含著老人自死習俗的內涵,同時進一步對堯舜禹禪讓真相進行解析,并賦予這段歷史以新的解讀。
“鯀復生禹”出自《山海經·海內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1]536對該神話最早著迷的古人就是屈原。他在《楚辭·天問》中問道:“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伴隨疑惑與探究,幾千年無定論,究其原因,還是人們的思想跳不出神話歷史化、歷史道德化的藩籬。
弗雷澤指出,在未開化的野蠻社會中,巫師“最首要的是控制氣候,特別是保證有適當的降雨量。水是生命之源……因而在原始人社會中,祈雨法師是位極其重要的人物。”[2]95“因為人們既篤信巫師擁有使甘露降臨、陽光普照、萬物生長的力量,因而也就很自然地會把干旱和死亡歸咎于他的罪惡的玩忽職守和存心固執己見,并相應地給他以懲罰。因此,在非洲,國王如果求雨失敗便常被流放或被殺死。”[2]132白尼羅河流域的丁卡人,“正由于他享有崇高榮譽,丁卡的雨師們一個都不允許自然地老病死去……所以,一個雨師感到老了,體力不濟了,就告訴他的孩子們說他想要死了。在阿加的丁卡人中,做法是挖一個大墓穴,雨師躺在里面,他的朋友和親戚圍在穴邊。他斷斷續續地向人們說話,回憶本部落過去的歷史,提醒他們他過去是如何統治、如何教導他們的,并告訴他們將來如何行動。教誨完畢之后,他就吩咐他們把他蓋起來。他躺在墓穴里,土就拋到他身上,他立即就悶死了。”而“他的可貴的神靈就立即傳給了適當的繼承者——他的兒子,或其他近親。”[2]398我們將從這里入手,通過多角度分析,證明“鯀復生禹”具有類似的歷史真相與文化內涵。
一、 關于鯀-禹部落(家族)的性質
第一,他們屬于黃帝的世系。《山海經·海內經》:“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1]503《山海經·海內經》郭璞注引《世本》:“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1]528《史記·夏本紀》也選擇了“黃帝-昌意-顓頊-鯀-禹”這一世系說法。
第二,顓頊-鯀-禹部落具有“酋長與雨師兼具一身”的特殊身份。《大荒北經》曰:“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附禺引郝懿行解云:“《海外北經》作務隅,《海內東經》作鮒魚,此經文又作附禺,皆一山也,古字通用。”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丘方員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竹南有赤澤水,名曰封淵。有三桑無枝。丘西有沉淵,顓頊所浴。”[1]478《海外北經》曰:“務隅之山,帝顓頊葬於陽,九嬪葬于隂。”[1]291《大荒西經》中記載:“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及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1]476顓頊所居之地多水,多淵,有山,這最雨師所心儀的風水寶地;“顓頊死即復蘇”,說明顓頊有巫術變化能力;巫術變化形象為蛇與魚,都與水有關。所葬之地亦以神名命之(“附禺之山”即“鮒魚之山”。“鮒魚”與“魚婦”音同而字顛倒,或是傳承記憶出錯所致,實為一名)。這一段文字,以詩歌節奏讀來,可能就是祈雨儀式中的咒語,此段文字稍作調整,即是兩段語義清晰的歌詞:“風道北來,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天及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表達了祈求枯魚—魚婦—蛇—顓頊四位一體(包含巫師與圖騰動物之間的靈魂轉移)的“復活”儀式的內涵。
顓頊作為部落聯盟首領時期,已經存在禪讓不傳子的傳統,他的部落后代就在其后的部落聯盟首領之下專門職掌水旱之事,這就是為什么堯舜時代治水的大任會由顓頊的后代鯀、禹承擔的原因。《列子·楊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3]213《莊子·盜跖》:“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4]197即傳說禹治水時,身體“偏枯”,俗稱“半身不遂”,走路也跛了,稱為“禹步”。其實背后是禹實施繼承于祖先顓頊的巫術通神儀式。
確認以上兩點,在后面論證“鯀復生禹”背后的老人自死內涵時,就可以明了這的確就是在傳說中的炎黃時代的原始社會普遍存在的習俗。
二、鯀的事跡爭論背后的神話歷史化、道德化的邏輯剖析
鯀的事跡以《山海經·海內經》中記載的神話為最早。神話中的英雄被殺,是可以殺而不死,或死而變形,死而復生的,鯀作為巫師身份尤其如此。由此“殺鯀于羽郊”之后,又有“鯀復生禹”就是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然而隨著后人以理性思維取代神話思維,而將神話歷史化、現實化,在這二者之間就必然存在邏輯上的矛盾了。于是人們按照各自理解的需要,出現了重新“解構”神話材料的兩種邏輯。第一種是,認同神話中鯀被殺是歷史事實,那么其后的“鯀復生禹”就是無稽之談。《尚書》中記載:“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勿成。”[5]26-28“(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5]56-57“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5]293-294《史記》進一步綜合表述:“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賢于鯀者,愿帝試之。于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于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6]11二者都采取了繞過“鯀復生禹”內容的思路,建構了一段影響深遠的“信史”!這種處理也無意中包含了神話中的合理成分,即禹繼承鯀的治水事業時已經是成人。
然而,神話中鯀是正面的英雄形象,鯀的被殺,是“不待帝命”。與其舍命為天下相比,“帝”因此殺他,顯然過分。鯀的事跡中的確包含有功于民的一面,從民的立場看,鯀的死充滿悲劇性的崇高感,而“帝”的形象反處于其下,甚至對立。《天問纂義》毛奇齡注曰:“大抵鯀治水隨地筑堤,今河北清河、廣宗、臨河、黎陽等界,所在皆有鯀堤可見。”[7]11說明鯀雖未能根治水患,但畢竟減緩了洪水的危害,百姓是將鯀和禹一樣紀念的。《國語·魯語》曰:“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8]166鯀能夠與黃帝、顓頊、帝嚳等相提并論,作為郊祀王城外百里之內為郊。祭天地在郊,皆得稱郊。《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鯀至少是以雨師的身份配祀天地。對象延續下來,說明他不僅有功,也不可能存在與堯舜爭天下的大罪。
這樣的對比顯然與堯舜二帝一貫占據道德制高點的歷史觀相沖突。于是,在《堯典》中,鯀與“帝”的位置完成了轉換,且從堯帝的口中否定他“方命圮族”。雖然不知四字具體所指,但已經定性,只是罪不足誅。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按說罪加一等,堯既然沒有因其治水無功而殺之,舜又何必“殛鯀于羽山”?
從維護部落聯盟首領或帝王道德正統出發,《堯典》與《史記》都將鯀的事跡予以反道德化改造,是別無選擇的選擇。此后的典籍中,鯀的罪更是被提升到與帝王爭奪天下的高度,“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為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9]267“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于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于羽山之郊。”[10]243
如此,帝王殺鯀不僅順理成章,也造就了自己政治與道德上的正統形象,“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就被包裝成了合乎后人道德觀的正版歷史。但是,這種處理方式,不僅對“鯀復生禹”避而不談的本身就是留下了一個對神話結構解釋上的缺陷和疑問,同時帶來了另一個難以解釋的人性問題,如后文的“若以為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還有,作為父子,為何鯀的道德這么低下,而禹的道德那么高尚?從文獻來看,人們也只能用禹就是天生的道德高尚的原因來解釋了。
第二種重新“解構”神話的邏輯是,傾向于“殺鯀于羽郊”與“鯀復生禹”都是存在的,這就必然導致對鯀先被“殺”的真實性的疑問上,集中在對“殛”字的理解上。將鯀反道德化者持“誅殺說”的居多,但也有持“流放說”的。《尚書今古文注疏》引疏云:“云‘殛,誅者,《釋言》文……‘誅,責遣之,非殺也。《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是殛即放也。《祭法》疏引《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圣功,故堯興之。若以為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案:舜之殛鯀,方將使之變和東夷,必非置之死地。箕子云‘殛死,亦謂殛之遠方而至死不反,故《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久遏絕之,不施舍也。”[5]57屈原《天問》中的記載為流放說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就“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四句, 陳遠新曰:“乃帝遏之不殺而用其子,且知其子不以父故避嫌,而不蹈父故轍,亦可深思鯀之為鯀矣。為鯀出脫,即是為堯舜出脫;不然,棄父用子,終是千古疑團。”[7]97可見,解“殛”為流放,很大程度上也繞開了前面提到的人性的障礙。“流放說”的另一個證據,是《天問》中解釋“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兩句的文獻支持。
(唐)杜佑解《舜典》“鯀殛于羽山”曰:“按司馬遷曰:‘舜流四兇于四裔,以御魑魅。此一明四兇不死也。又,《舜典》云‘流宥五刑者,五刑中有死,既以流放代死,此二明四兇不死也。又《舜典》言,舜美皋陶作士曰:‘五流有宅。孔安國注云:‘五流有宅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兇。此三明四兇不死也……所以辨鯀至羽山而自死者也。”[11]2219首次明確提出了“自死說”,看似即將破題。
第二種邏輯畢竟仍然是以神話歷史化為目的,而不是對神話思維的恢復,更沒有可依據的解釋神話思維的理論(那是19世紀以后的產物)。因而即使杜佑提出的“自死說”,其認知的本質與老人自死習俗真相之間仍然隔著一堵厚厚的墻壁,并且他們必然陷入一個新的邏輯矛盾之中,那就是如何解釋“鯀復生禹”的內涵!
三、 后人對“鯀復生禹”的世俗化解釋
由于對老人自死習俗的遺忘,不理解這里的“復”乃是“重”的意思,“復生”乃是神靈“重生”,包含繼承者是直系血緣親子關系的特定內涵,這與“顓頊死即復蘇”是一脈相承的。當然,“復生”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是鯀的神靈重生,也是禹的重生(接受了鯀的神靈,其生命結構改變了,具有神性)屈原最先發出這樣的疑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引出了歷史上延續兩千多年的“猜謎”活動。
《天問》有“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死而分竟地?”王逸解為禹母生禹之事。[7]201-212《吳越春秋》曰:“鯀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肋而產高密(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12]239《帝王世紀》亦謂:“顓頊生鯀, 堯封為崇伯,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已。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于石紐。”[13]21這樣的感生神話,由于《天問》的記載,說明在屈原之前已經存在。女嬉生禹與伯鯀愎禹在《天問》里同時存在,正好說明,后者應該是“復生”,換言之,此時的禹不是嬰兒,而是成年人。
屈原疑問的原意是:鯀是男人,如果禹是在鯀的腹中孕育,那是怎樣在他的身體里變化的呢?這已經是“看呆神話”,即用生活經驗向神話發問(這是《天問》的一個基本邏輯出發點)。后人還是圍繞男人生育的矛盾繞圈子,一些解釋反而跑的更遠。
解“愎”為狠者,如王逸:“言鯀愚狠,愎而生禹,禹小見其所為,何以能變化而有圣德?”王夫之曰:“鯀之愎,禹之圣。”解“愎”為懷抱者,如洪興祖曰:“愎一作腹……《詩》云,出入腹我。腹,懷抱也。”林云銘曰:“禹固出于鯀之懷抱也,乃變障隄而為疏導。”指出語法結構問題者,如夏大霖曰:“禹腹鯀是倒裝句法,謂禹乃鯀所懷抱。”而他們對“夫何以變化”大多作禹為何德行比鯀高的解釋。[7]9697本來《山海經》神話中就是“復”生,為何還爭相在《天問》這里解作“腹”生呢?就是因為都不明白“鯀復生禹”是鯀-禹之間神靈轉移,是鯀在禹身上的“重生”。
聞一多解釋曰:“腹原作愎,鯀禹二字互倒……《廣雅·釋詁》一曰:‘腹,生也。……《海內經》曰:‘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復生無義,復當讀為腹,亦謂鯀化生禹耳。”[14]23他雖然也解作“腹”,但是解釋“鯀化生禹”更合理了,也接近了神話內涵(聞一多時代,西方神話學理論著作原著、譯作他是能夠看到的)。但是聞一多認為鯀既被殺,“復生”就沒有意義,卻又是在拿生活的邏輯看神話。“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兩句相連,正是包含了鯀的死亡所體現的悲劇性內涵,即有辱使命,殺而不死,非生禹不能寄托未竟事業。其神話情節就是“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1]537然后才有“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因此,“復生”不是沒有意義,而是有重要意義。從被“殺”到“復生”,完全符合神話的文學特征,夸張,浪漫,詭譎,凸顯了鯀在這個神話結構中所處的悲劇性地位與內在精神的沖突。前人解釋的“伯禹愎鯀”都應該回到“鯀復生禹”神話語源上,“愎”“腹”都應該回到“復”字上。這與從母親腹中出生是完全不同的。
依據《天問》文獻存在的時間順序,后人對“鯀復生禹”的理解原本應該不會和禹母生禹混淆。而袁珂認為:“神話中‘鯀腹生禹的情節,帶著父權制氏族社會男人喬裝生子風習的痕跡。”[15]29他解釋以“產翁制”,是和禹母生禹混為一談了。神話學專家尚有如此解釋,對古人的模糊理解也就不必苛求了——古人對“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的解釋(以王逸注為代表)包含了以下的理解和暗示,即鯀生出一個小孩的禹(不妨就將他們的理解視為“產翁制”的轉述),再長大成人;或者雖然鯀生不出禹,但鯀被殺之時,禹還是一個小孩的禹(這樣,“鯀復生禹”被賦予生離死別以及父命子承的悲壯也無不可),經過十幾年,而為成人的禹。中間可能經過高尚的母親或托孤者的教育,品德智慧遠超其父,并被舜授命治水。這樣神話中后三句“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不就完全符合時間邏輯而成為一體,前面提到的人性障礙不也迎刃而解了嗎?
假如我們如此理解,作為部落首領,鯀應在30歲之前就要成婚,為何卻很晚得子?如果這點說不清,那么在禹的成長過程中,至少在其童年和少年時期,一定要有一個過渡性的部落首領來領導全族,但是神話和史書都沒有任何的相關材料。而禹至少要長到20歲(也就是舜至少要等20年),才能受命繼承鯀治水的事業,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我們來看《尚書》,假定堯帝啟用鯀治水與求賢于舜同時,舜經歷3年考驗(實際為“殯”之“三年之喪”),至鯀治水9年時,舜即位6年。又假定舜次年“殛鯀于羽山”,其時禹由母而生,至《大禹謨》中舜與禹言:“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時,禹治水13年已經成功。即便對話就在成功之時,則舜用禹治水在繼位20年時,推知禹應為13歲。如“殛鯀于羽山”與舜禹對話時間都更晚,推算出禹的歲數更小,治水是不可能的。因此“鯀復生禹”時禹應該是成人。
由此,“鯀復生禹”包含兩種儀式,一方面,“鯀復生禹”是發生在父子之間的老人向年輕人的神靈轉移儀式,是鯀的重生,“復生”。另一方面,則是禹完成成人禮時的重生——成人禮儀中包含死亡與再生儀式,他們家族有“顓頊死即復蘇”的傳統。在這個意義上,說“鯀腹生禹”是合理的。馬林諾夫斯基論述原始民族成人禮儀,“所歷試驗,常使被試者裝作當場死亡旋又復活的樣子。”同時,還要“將神圣的神話與傳統有系統地教與青年,漸漸使他知道族中奧秘,使他見到神圣的事物。”有一種形式是:“主宰將青年吞下,使他死亡,然后使他復活,以成戒行圓滿的成人。”[16]22這其實是一個“感生神話”在成人禮儀中的表現形式。與之相似,“鯀腹生禹”很可能先有一個“鯀吞禹”的前奏,與禹第一次孕育時,女嬉“得薏苡而吞之……因而妊孕”相對應;而“剖之以吳刀”“大副之吳刀,是用出禹”,又與禹第一次出生時“剖肋而產高密(禹)”相一致。亦即禹的成人禮中的再生部分重復了他過去第一次孕育出生時的感生神話形式,只不過是載體變成父親鯀。通過儀式,禹才能夠有資格接受鯀的神靈,承擔部落首領與雨師的職能。可以說,舜在等待合適的時間,即禹的長大成人,先舉行禹的成人禮,接著舉行鯀的老人自死儀式。(禹的合理年歲,鯀復生禹時應在進入20歲后的青年期,《儀禮·士冠禮》中“年二十而冠”或源于此。)
綜上分析,筆者認為,鯀在堯帝用舜之前即治水已久,其歲數當在堯之下,但至少比舜大不少。堯帝所言“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此前必有洪水由起到盛的過程,其間鯀帶領所部以筑堤堵水的方法,終不能有效根治,有辱使命,此乃“方命圮族”的內涵。堯帝第二次啟用鯀治水,鯀不變其法,九年無成效。至舜帝時代,仍未成功。鯀背著“方命圮族”的壓力,殫精竭慮,心力交瘁,身體衰老明顯超出實際年齡,治水已經有心無力。為天下大計,舜或命令鯀提前實施老人自死儀式,盡快將神靈轉移到繼承者禹的身上,以免神靈的衰老將部落帶入頹敗的危機之中,而不能完成治水大業。
如此解釋“鯀復生禹”,即可理解“帝令祝融(筆者按:或舜)殺鯀于羽郊”與“鯀復生禹”并列出現,也能解釋屈原“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的疑問。
四、“三年不施”中的“神靈”轉移儀式、形象及空間特征
(一)對“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的儀式性解釋
王逸注曰:“言堯長放鯀于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后人多解為堯、舜囚而不殺、不赦。如周拱辰曰:“曰三年何也?《公羊注》: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施矣,惟有永遏之已耳。”[7]92-95人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堯舜與鯀的關系上了。他們不解“鯀復生禹”的真相(包括錯誤理解鯀生出一個小孩的禹,再長大為成人的禹)。自然也就不能理解“三年不施”的背后,是指鯀的一點神靈完全轉移到禹的身上需要經過三年的“過渡禮儀”,即經歷“分隔——邊緣——聚合”三個階段,在以成人兼巫師的新身份完成聚合到成人群體的儀式之前,禹還不能開始進行治水大業。以天下當時的水患之嚴重、舜帝與百姓對禹的期待,三年的等待太漫長了!因而“三年”在此是一個被強調的數字,而“三年不施”的疑問則表明在神話的流傳過程中其內容與對象都被誤讀了。
在很大程度上,“三年不施”與“三年不腐”(從神話角度也可理解為“三年不死”)存在著對立關系。前者包含了天下治水需要的緊迫性,而后者包含著鯀-禹之間的神靈轉移儀式特殊的重要性。第一,它不是一般70歲,而是提前了許多歲數(但至少在禹成年禮之后)舉行的。對鯀而言,是迫不得已的;第二,比之堯禪讓于舜,鯀是以失敗者的身份,帶著巨大的遺憾、羞恥,背負命運的不公和對命運的抗爭而進行禪位的。為了完成未竟事業、重振部落榮譽,必須保證自己的生命在禹身上“復生”!不可因為治水的急迫而有任何懈怠。他內心世界的一切禹必定清楚。大禹治水,正是因為肩負雙重的使命,他的奉獻才超常徹底,他的事跡才如此感人,《莊子·天下篇》引墨子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圣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治水才能“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二)“神靈”轉移儀式中的圖騰形象分析
形象之一,龍。聞一多引古籍“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與“大副之吳刀,是用出禹”兩句曰:“或曰化龍,或曰出禹,是禹乃龍也。剖父而子出為龍,則父本亦龍,從可知矣。”[14]23(以刀“剖父而子出”顯然是嫁接了女嬉“剖肋而產高密”、 修已“胸坼而生禹”的情節,并與后來的啟自母腹“破石而出”相類。)依此,轉移的神靈形象首先是龍。它賦予鯀-禹家族掌控水旱的智慧與靈驗。大禹治水有龍相助。傳說夏后氏之王多乘龍。《海外西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儛《九代》;乘兩龍,云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1]253《大荒西經》曰:“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珂案:開即啟也,漢人避景帝劉啟諱)[1]473活脫脫一副大巫師的形象。張光直說:“夏后開無疑是將天上的樂章與詩歌帶到人間的英雄,此時他便是一個巫師,得到兩蛇和兩龍的幫助。龍與蛇可能與他們為上帝溝通人間的使命有關。”[17]46-47龍蛇能助巫師升天。龍成為中華民族之象征,鯀-禹部落的龍圖騰影響深遠。
形象之二,熊。《史記》對“黃帝”的注釋:“[集解]徐廣曰:‘(黃帝)號有熊。[索引]案:注‘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正文有黃帝“教熊羆貔貅赤貙虎,以與炎帝戰于版泉之野。”[6]6從排序看,熊圖騰的部落是最具戰斗力的,而他們很可能就是顓頊-鯀-禹部落的源頭。《山海經》中多處記載了多位帝王(包括顓頊)陵冢前的神獸,熊列于其首,顯然與其力量和勇猛的特性有關。
《左傳·昭公七年》記晉平公夢熊問韓宣子,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18]429(《國語·晉語》略同)《漢書》顏師古注曰:“禹治鴻水,通軒轅山,化為熊。謂涂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涂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19]385聯系二者,可見轉移的神靈也有熊。它賦予了禹領導治水、筑城等工程所需要的力量和勇氣,也是重大工程開工儀式上所請之神。
形象之三,鱉。《史記》曰:“舜……乃殛鯀于羽山以死。[正義]:鯀之羽山,化為黃熊,入于羽淵。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為三足也。束皙《發蒙記》云:‘鱉三足曰熊。”(筆者注:原文能之下為三點)[6]11《經典釋文》解釋《左傳》化熊之說釋“黃能”云:“如字,一音奴來反;亦作熊,音雄,獸名。能,三足鱉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鱉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鱉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鱉為膳,斯豈鯀化為二物乎?”[20]1089 美國新墨西哥的祖尼印第安人認為“人死之后靈魂轉生為烏龜……死者的魂魄就是以烏龜的形體聚居在另一個世界里。”(見弗雷澤著,徐育新等譯,《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481頁),二者或有某種內在聯系。鱉或“黃能”,常居于水底,穩健有力,代表雨師部落在水下疏浚、治理河道的工程能力。而熊也可以入水,文獻中關于鱉、“能”、熊的混雜性解釋,恰好反證了那不過是雨師部落在水下和陸上治水、開路、筑城等多種能力相互統一的圖騰化表現。
形象之四,玄魚。《拾遺記》卷二謂:“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于羽淵,化為玄魚。時揚須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之‘河精。”[21]33“鯀”字為魚類,與“顓頊死而復蘇”的形象“魚婦”(實際上是“鮒魚”)有傳承關系。蛇、龍、魚、鱉,形象雖有變化,但皆不出水族之物(古人或魚蛇混同,《海外南經》曰:“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可見模擬或相似巫術思維的痕跡,自顓頊而傳之。
儀式中轉移的圖騰“神靈”包括上述四種(熊兼有鱉、“能”的屬性)。其中,“熊和龍的母型蛇、蜥、鱷,都要冬眠——驚蟄,這在初民看來,也是一種死與不死、生與再生的辯證運動。鯀禹的化熊、化龍,就昭示著他們的生命只能轉化不能毀亡,他們的業績只會斷續而不會中止。”[22]5-6魚和鱉、“能”(龜類)則代表著雨師所擁有的最元初的生命創造力和生不息的生命延續力。在“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的祈雨儀式里,魚甚至是最重要的神靈。
(三)“神靈”轉移儀式中的空間特征分析
《山海經·南山經》曰:“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草木,多蝮蟲。”(羽山之下注:“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即鯀所殛處。”)這里倒是很合乎雨師的環境特征。《尚書今古文注疏》中對“羽山”的注疏:“《史記》[集解]馬融云:‘羽山,東裔也。[正義]《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云‘羽山,東裔者,《地理志》:‘東海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山在今山東郯城縣東北七十里,江南贛榆縣界。”[5]57《天問纂義》中,“蔣驥:‘羽山在今淮安府贛榆縣。又登州蓬萊縣亦有羽山。游國恩按:‘羽山見《離騷》,當以在今蓬萊縣者為鯀殛處,他所傳同名者非也。”[7]95
聞一多將神靈形象與空間地點統一起來:“《中山經》曰:‘從山多三足鱉。從山即崇山。樂府古辭《董逃行》‘吾欲上謁從高山,謂從高山,可證。《周語》上:‘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注曰:‘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案當即傳說中鯀所封崇國之山(《周語》下又云‘有崇伯鯀)崇山為鯀所居地,而云多三足鱉,是亦主鯀化為能鱉之說者也。”[14]21
丁山在《古代神話與民族》中進一步論證:“《山海經·中山經》云:‘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是多駕鳥。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畢沅《校正》云:‘渚,在今河南嵩縣。”丁山考證:“今嵩縣……因崇山為名。崇山,《詩》言嵩岳,卜辭曰岳,為殷、周禱雨勝地……則鯀化羽淵,宜在崇山附近之禪渚;所謂羽山者,羽之為言雨也,雩也,即謂禱雨之山矣。”鯀稱崇伯,羽山即為崇山。[23]231
聞一多、丁山所言似更為合理。《大荒北經》所載顓頊所浴沉淵,所葬附禺(鮒魚)之山,《海內東經》言“漢水出鮒魚之山,帝顓頊葬於陽,九嬪葬于隂,四蛇衞之。”[1]385“鮒魚之山”是顓頊-鯀-禹部落在漢水的發源之地。比照羽山與附禺(鮒魚)之山、羽淵與沉淵,顯示出具有傳承性的對應關系。換句話說,鯀進行的老人自死儀式,是在類似于祖先顓頊所居住的有山,有水,有淵的自然環境中,這種巧合顯然包含了精心安排的目的性。亦證明舜“殛鯀”,實質是舜命令鯀提前完成“鯀復生禹”的儀式,而不是直接被誅殺。
《天問》曰:“阻窮西征,巖何越焉?”王逸注曰:“言堯放鯀羽山,西行度越嶺巖之險,因墮死也。”[7]227其包含的儀式是:鯀身處于羽山(崇山),或天然洞穴中,完成神靈與肉體分離(自死)后,神靈以圖騰形象回歸祖先故地,以獲得祖先的認同與庇佑,并通過接觸巫術得到祖先賦予的強大力量(這是一個精神的而非身體的歷程);然后再返回羽淵,完成神靈向禹的轉移,開始“顓頊死既復蘇”的儀式。對照《大荒北經》顓頊葬附禺之山,浴沉淵的描寫,鯀完成神靈與肉體分離后,進入喪禮階段,葬于羽山。禹則進入三年守喪即神靈轉移的過渡禮儀階段。羽山、羽淵二者距離相近,其間,禹或有在羽淵沐浴,通過水的媒介,與神靈——龍、熊相互融合的儀式。這大概就是“焉有虬龍,負熊以游”的真實涵義。“化為黃熊,巫何活焉?”則從反面說明在神靈轉化的三年儀式中,一切都有專門的巫師主持,即《論語·憲問》中孔子所言“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
水,是雨師進行通神或實施神靈轉移儀式的必需要素,故《山海經》《天問》中的顓頊-鯀-禹神話都與水密不可分,由此也揭示了現存的自死窯遺址大量分布于河流兩岸或朝向溝谷這一空間特征的秘密所在。
《后漢書·張衡傳》注引楊雄《蜀王本紀》故事曰:“荊人鱉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24]972聞一多《天問疏證》所引本故事曰:“荊有一人名鱉靈,其尸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尸隨江水上至郫,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令)決玉山,民得安處。”且以為“此亦主鯀化為能鱉之說者”。[14]22有當今學者以為乃是有附會“阻窮西征”與大禹治水之功的色彩。[25]47-53若是如此,則證明鯀完成神靈與肉體分離后,肉體死亡(尸),而神靈開始回歸故地(是漢水而非長江)楚民族與顓頊有族源關系,《天問》說明楚人保存了對鯀做為治水英雄的神話情感。隨著楚民族從漢水流域進入到江漢平原,鯀治水神話演變出新的鱉靈文本,背景被置換為長江流域。鱉靈的故事結尾:“(望帝)乃委國授之(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帝。”鯀終于在另一個空間獲得了英雄應有的尊嚴與王者的地位,這也體現了道統與民間對鯀的評價的不同。之說可成立。這里言“尸隨江水上”,是為滿足后面鱉靈“遂活”的需要,作“借尸還魂”的載體。
至于后人從維護堯舜道德正統的需要出發,把殺鯀的羽山描繪成十分荒涼、恐怖的面貌,是最自然不過的了。如聞一多所引證:“《地形篇》又曰:‘北方曰積冰,曰委羽,注曰:‘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為名。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委羽山一曰羽山,即帝所刑鯀處。而《墨子·尚賢中篇》曰:‘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14]36
五、結論
堯舜禹禪讓和鯀復生禹兩個神話中都包含老人自死習俗。禹在其中具有特殊地位與重要性。在禪讓的神話背后,禹與前任有不同之處,是經歷了兩次老人自死儀式,一是“鯀復生禹”,一是“舜-禹禪讓”。在他的身上,既延續了本部落禪位于子的傳統,又承載了部落聯盟禪讓于外的傳統;他的體內,既有祖上顓頊-鯀的神靈,也有帝王堯-舜的神靈;他治水,既是要解天下之災,也要重振家族榮耀。他要與天斗,與地斗,與命運斗,與自己斗,“生于憂患”的大禹真是壓力山大!所以他治水的神話事事動人,又處處沉重,特別是他變熊開山,妻子見而化石,兒子啟破石而出的神話,折射出禹的內心深藏的孤獨、無助、悲涼,以及些許的迷惘,甚至他的下一代的出生也打上了家族悲劇的烙印,與他那化身為熊的孔武有力的形象形成強烈的對比與反差。然而他以超出常人的意志堅持著,以熊的力量繼續著,終以成功而告慰祖先與天下。
相比《尚書》中堯、舜作為帝王的道德化形象,典籍中禹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更加豐滿生動,由于受到道德史觀的強大影響,后人更看重堯舜禹禪讓神話,而忽略甚至貶低了鯀復生禹神話所隱含的歷史信息,以及鯀-禹部落對中國歷史的重大影響。因為他們的部落不僅是宗教知識(雨師·巫師)的掌握者,也是當時科學知識的掌握者(如以《禹貢》、夏小正為代表的系統的地理知識,天文歷法知識);具有能征善戰的軍事能力,還掌握著最先進的工程技術和工程建設能力——除了水利工程,他們還是城市的建造者。《呂氏春秋·君守》曰:“夏鯀作城。”《淮南子·原道訓》曰:“昔者伯鯀作三仞之城。”《吳越春秋》:“鯀作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漢書》臣瓚引《世本》曰:“禹都陽城。”還有可以與堯舜比肩的各種美德:忠誠,奉獻,天下為公,勤勞(《大禹謨》中舜贊其“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自我犧牲(三過家門而不入),隱忍,謙遜(《大禹謨》中舜、禹的對話)等;他們也吸收融合了其他部落與部落聯盟中的優秀文化與先進技術,逐漸成為當時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代表。舜禪讓天下于禹,這是鯀、禹都不曾奢想的事情,卻是天命和歷史給予他的最公正的回報,也是歷史的必然選擇。鯀-禹部落成為天下正統,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也開創了中華文明的嶄新時代!而這一歷史開端追溯到“鯀復生禹”的神話,就必然和老人自死習俗聯系到一起。
1960年,英國學者李約瑟在《現代中國的古代傳統》一文說:“關于中國官僚封建主義的起源,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論點,認為那和中國古代水利工程超越一切的重要性是有關系的。我認為這種說法很有道理。”[26]35今天,他引述并贊同的這一觀點也在解剖老人自死習俗與堯舜禹禪讓、鯀復生禹神話關系的論述中找到了源頭。
分析堯舜禹禪讓與鯀復生禹同時,關于老人自死習俗與孝道的關系也水到渠成。兩個神話不僅包含了老人自死習俗的內核,而且老人自死在彼時彼地都是事關部落興盛的神圣的神靈再生儀式,根本不存在野蠻、不孝的問題。孝道的觀念不是憑空存在的,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是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產生的,存在于每個時代的現實生活中,其內涵與形式是會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有所改變的。從彼時彼地的觀念(巫術思維·民俗信仰)本質看,老人自死反倒可以說是彼時彼地的對老人的最大的孝,最隆重的孝,是孝道的重大儀式。老人自死習俗與后來的某些禮制(“七十致事”“三年之喪”)的形成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從原始社會的巫術思維,經過夏商時期的過渡,進入周代的禮制,這一漫長的演進必然伴隨著觀念的轉變,也必然伴隨記憶的喪失,解釋的訛誤,并長期影響后人的認識。所以,我們運用辯證唯物史觀去看待二者之間的關系,并結合人類學、民俗學(包括神話學)的理論深入解剖,才能更加接近歷史的真實。而僅僅站在后來以家族血親關系為核心的孝道觀念的角度,包括從某些口傳文本的敘述導向上,看待老人自死形式上與后來孝道的沖突,判定前者是野蠻、不孝,甚至將老人自死習俗的消失看作是從棄老到敬老,社會從野蠻進入文明的標志,所持的是靜止的、割裂的、片面的歷史觀;是歷史道德化的思維慣性的表現,所得出的結論當然也是值得商榷的。
日本學者伊藤清司說:“我們可以推定,舜經受考驗的傳說,在流傳過程中有了很多變異,所以給內容帶來了一些混亂。其中最大的混亂也許來自古代執筆的的那些文人學者。他們也許把舜經受考驗的傳說看做‘不雅馴,于是根據儒教的思想意識,對其內容巧妙地作了一番脫胎換骨的改造。然后,根據封建孝悌道德觀念,加以粉飾,致使傳說的原來面貌有了明顯變化。就這樣,故事中出現了理想的圣天子像(這是捏造的),還出現了名為禪讓,實則架空的所謂理想的王位繼承的范例(這是創作)……可能不管他們怎樣喬裝怎樣粉飾,傳說的真面目卻不可能全部被掩蓋。我們很幸運,在人民的創作中還有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民間故事,這些民間故事就是我們據以摸清傳說之本來輪廓的線索。”[27]433-434他的觀點對我的思考是有力的支持,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會否定融合了儒家思想的老人自死傳說對傳播孝道觀念具有的積極意義。
總之,以禹的事跡為核心,老人自死習俗為紐帶,與正統信史、上古神話、民間傳說、漢水流域區域歷史與文化遺存等,建立起了跨越時空的文化聯系。認同堯舜禹禪讓與鯀復生禹神話的背后隱藏著老人自死、成人禮儀習俗,以及伊藤清司解析的婚姻難題考驗的風俗,那么我們確信并傳承至今的這一段歷史中,有關人物、事件內容、結構關系與語言表述等,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要重新改寫。
參考文獻:
[1]袁珂.山海經校注[M].成都:巴蜀書社,1993.
[2]詹·喬·弗雷澤.金枝:上[M].徐育新,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
[3]王強模.列子全譯[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
[4]王先謙.莊子集解[M].上海:上海書店,1991.
[5]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04.
[6]司馬遷.史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94.
[7]游國恩.天問纂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2.
[8]左丘明.國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呂不韋.呂氏春秋[M].高誘,注.上海:上海書店,1991.
[10]王先慎.韓非子集解[M].上海:上海書店,1991.
[11]杜佑.通典[M].顏品忠,等校點.長沙:岳麓書社,1995.
[12]趙曄.吳越春秋[M].張覺譯,注.長沙: 岳麓書社,1994 .
[13]皇甫謐.帝王世紀[M].濟南: 齊魯書社,1998 .
[14]聞一多.天問疏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袁珂.中國神話史[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16]馬林諾夫斯基.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M].李安宅,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
[17]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18]宋元人.春秋三傳 [M].北京:中國書店,1990.
[19]班固.漢書:武帝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94.
[20]陸德明.經典釋文:中冊卷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1]王嘉.拾遺記[M].蕭綺,錄.齊治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
[22]蕭兵.《天問》難題一則[J].云夢學刊,2004(6): 56.
[23]丁山.古代神話與民族[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4]范曄.后漢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94.
[25]李修松.“鱉靈”傳說真相考[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5).4754.
[26]李約瑟.四海之內:東方和西方的對話[M].勞隴,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
[27]伊藤清司.難題求婚型故事、成人儀式與堯舜禪讓傳說[C]∥葉舒憲.神話—原型批評.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
責任編輯:汪效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