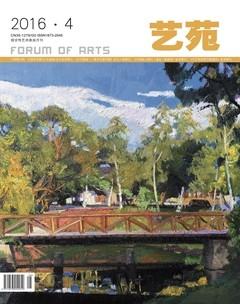試論《宣和書譜》中的“逸格”品評
范功
【摘要】 作為北宋著名的書學(xué)論著,“逸格”品評是《宣和書譜》書法評論的重要特色。它反映了宋代的書學(xué)理論和書法創(chuàng)作的傾向,從“逸”的區(qū)分也有助于考察《宣和書譜》的編撰、審定等問題,從中發(fā)現(xiàn)書家傳記編撰者的佐證。
【關(guān)鍵詞】 《宣和書譜》;逸格;品評
[中圖分類號]J29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對北宋書論著作《宣和書譜》的研究,以前多集中在對作者的考證以及它在修撰中涉及的問題。本文擬從書法品評的角度,對前輩時(shí)賢的研究成果做一點(diǎn)粗淺的補(bǔ)充。《宣和書譜》各卷有分目,人各一傳,共立傳197名書家。在每傳中其知人論書的特點(diǎn)十分明顯,論及書法也頗為精細(xì),夾敘夾議,體例亦佳。我在研讀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作者在論書時(shí)常使用“逸”字,而且?guī)缀鯇Α耙荨弊指F盡了一切限定詞。當(dāng)然,也有個(gè)別不是用于書評的。這一現(xiàn)象引發(fā)我的一些思考,今做一整理。為下文敘述的方便,我先把這些“逸”字在著錄中的出處摘錄如下:
以上所錄《宣和書譜》的全部含有“逸”字的內(nèi)容中,第22條是用于人名,但相關(guān)的文章卻可以作為判斷米芾是否參與全部內(nèi)容審定的依據(jù)之一。第29條是帖名。其他的則是對書法、書者和詩文的評價(jià)。其中第3、23條是用于評論事理、人物的;第5、14條是評論詩文的;第24條表面是形容事物,實(shí)際也是在品評書法。
這些含有“逸”字品評書法的文章在全書中出現(xiàn)的次數(shù)較多,這足以引發(fā)我們做出如下的思考。
一、“逸”的品評角度和宋代的書學(xué)傾向問題
《宣和書譜》對書法中“逸氣”的崇尚可以從兩方面表現(xiàn)出來。其一,書評中反映出的重“逸氣”的思想。卷二對衛(wèi)包的篆書之“飄逸絕塵則未也”的不滿,對唐元度的篆書之“責(zé)其疏放縱逸”,充分說明編撰者對“逸”的刻意追求。尤其對篆書風(fēng)格也作出“逸”的要求,在宋以前是絕無僅有的。其二,對“逸”的良苦區(qū)分。如:大量使用含有“逸”字的詞匯進(jìn)行品評,先后有“飄逸、縱逸、散逸、俊逸、絕逸、清逸、流逸、閑逸、雄逸、怪逸、放逸、超逸”等。這一點(diǎn)在下文中詳述。
應(yīng)該說,“逸”是中國本土文化中既成的審美范疇。
“逸”字的本意指逃失。《說文解字》云:“逸,失也。從走兔。兔漫池善逃也。”[1]203又引申為超群的意思,用來指人。《論語·微子》章記載:“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情,廢中權(quán)。”[2]82人有高潔的品行方可稱為逸。到了漢末、魏晉時(shí)代,玄學(xué)盛行,追求“逸”成為一種時(shí)尚,在這種情況下,對“逸”的崇尚自然地滲透到了繪畫領(lǐng)域,特別是當(dāng)繪畫由人物向山水轉(zhuǎn)變時(shí),“逸”更被用來品評繪畫,黃休復(fù)在《益州名畫錄》中,將逸格列于神、妙、能三格之上,指出“畫之逸格,最難其儔”[3]6,確立了逸格在畫評中的崇高地位。至此以后,逸格被作為一種繪畫標(biāo)準(zhǔn),大家將用筆簡約,靈動(dòng)多變,新意頻生且神形兼具的畫風(fēng)稱之為逸格,而忽視了對作畫者的關(guān)注。倪瓚清晰地道出,他的畫被評為逸的原因,就在于畫家本身狀態(tài)的“逸”,在于畫家胸中的“逸氣”,“逸”開始向個(gè)人品格方面回歸。畫家只有將關(guān)注的目光從繪畫的技巧中解放出來,著眼于傳遞自身的精神氣質(zhì),將自己的性情通過筆端流于紙上,才能達(dá)到“逸”,“逸”不是一種繪畫技巧和規(guī)范,而是作者性情的表露,胸中有“逸氣”,加上一定的繪畫技巧,才能達(dá)到“逸”。這種回歸不是簡單地重復(fù),它上升到了另一個(gè)高度,那就是藝術(shù)表現(xiàn)自我的觀念。
從唐代開始,“逸”的確立就預(yù)示著一種審美反叛。在書論中“逸”最早出現(xiàn)在《八訣》中。在此書里,歐陽詢說:“澄懷凈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后來,體現(xiàn)禪宗美學(xué)的“逸”格由李嗣真提出。李嗣真在《書后品》中,始列“逸”品,并將其置于九品之上。他說:
昔倉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蓋德成而上,謂仁、義、禮、智、信也;藝成而下,謂禮、射、御、書、數(shù)也。吾作《詩品》猶希聞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能也,及其作《書評》,而登逸品之才者,亦當(dāng)絕終古,無復(fù)繼作也,故裴然有感而作《書評》,雖不足以對揚(yáng)王休,弘闡神化,亦名流之美事耳。
在他的眼里,可見“逸”的格調(diào)之高。“逸”格,具有不拘常法,縱任無方的藝術(shù)特征,它是一種非人工的超脫塵俗的韻外之致。并且從“能”格進(jìn)到“逸”格,是一種客觀迫向主觀,由物形迫向精神的升進(jìn)。升進(jìn)到最后,是主客合一,物形與精神的合一,具有“逸”格的書法是人的心靈自由灑脫的表現(xiàn)。這也是中國書家的終極追求。從中唐開始,“法”已趨向衰落,而到晚唐則已成為昨日黃花,幾無地位可言。釋亞棲便公開宣稱:“若執(zhí)法不變,縱能入木三分,亦被號為書奴。”晚唐五代書法領(lǐng)域,“逸”格對法的蕩滌,不僅確立了“逸”的審美主體地位,也為宋代的“逸”格品評奠定了基礎(chǔ)。
“逸”作為一種獨(dú)特的生活態(tài)度、精神境界在藝術(shù)中的反映,各種表現(xiàn)之間其實(shí)界限比較模糊,所以《宣和書譜》中作者對“逸”作出區(qū)分的良苦用心,除了反映了時(shí)代的書學(xué)傾向外,也能反映出作者審美上主觀的好惡。不過總的來說,足見作者對“逸”的審美因素的重視,其中“飄逸”出現(xiàn)得最多(蔡京、蔡卞均以“飄逸”稱之,特別引人注意),尤見作者對“飄逸”的激賞。
若粗淺給以解釋,那么“放逸”,表現(xiàn)作品中體現(xiàn)的人的充分的自由感,它縱橫恣肆,沉著痛快,悠然于法度之外,從心所欲而不逾矩。“超逸”,指一種迥脫根塵,心靈臻于真實(shí)無妄之佳境。“清逸”,指一種真實(shí)的藝術(shù)境界,體現(xiàn)出藝術(shù)家深摯的宇宙情感,在其獨(dú)特的體驗(yàn)中出現(xiàn),這就是主客觀合一的渾然的境界。這些對“逸”的解釋,其抽象性不言而喻。《宣和書譜》中岑宗旦認(rèn)為“懷素草書閑逸”,而作者也認(rèn)為“其吐論不愧古人”。元代趙孟頫認(rèn)為懷素“顛逸”(1)。“閑”與“顛”應(yīng)有大區(qū)別,然而都沒有脫離了“逸”字。可見,自宋以來,評者均視“逸”為書法高境界的表現(xiàn)。
隨著宋代“逸”的思想環(huán)境的充分生成,就導(dǎo)致了對書法品評視角的轉(zhuǎn)換。甚至在一向以端莊謹(jǐn)嚴(yán)取勝的楷書領(lǐng)域也打出了要追求“逸”的旗號。宋代倪思《經(jīng)堂雜志》云:“大抵楷法貴于端重,又要飄逸,故難兩全。”雖難以做到,但畢竟是作為一種目標(biāo)去引領(lǐng)書家的書寫。
由《宣和書譜》的這一現(xiàn)象可以表明:以“逸”的標(biāo)準(zhǔn)來評判人、事、書已是宋時(shí)的一種“風(fēng)氣”,這反映了宋代以晉韻為宗,追求“逸”氣,疾庸惡俗的書學(xué)傾向。
二、從“逸”的區(qū)分看米芾與《宣和書譜》的編撰、審定問題
(一)米芾與部分文章的編撰、審定
《四庫全書提要》認(rèn)為此書是由米芾、蔡京、蔡卞三人“所定”,今世學(xué)者也多有否定,但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不可簡單否定。通過對“逸”字的考察,我更贊成后者。《宣和書譜》中除了品評時(shí)對“逸”的重視之外,其作者還對“逸氣”作出了比較細(xì)致的區(qū)分,所以就有了,謝奕、李白、釋應(yīng)之、蔡京、蔡卞的行書以及陸繕草書的“飄逸”,孔琳之行書的“絕逸”,毛喜草書的“奔逸”(2),皇象草書的“雄逸”,賀知章草書的“怪逸”,張旭草書的“放逸”,懷素草書的“閑逸”(3),還有歐陽詢行書、許渾詩歌和薛濤思致的“俊逸”。同時(shí)也就有了唐元度篆書的不夠“縱逸”,衛(wèi)包篆書和李建中行書的不夠“飄逸”,趙模的正書不及王氏書法的“奔逸”,李宵遠(yuǎn)草書的太過“縱逸”。除了對“逸”作出各種細(xì)心的體察并試圖區(qū)分外,作者還很注意“度”的把握。如可以做到“飄逸”“清逸”“俊逸”,甚至“奔逸”“放逸”等,但決不可過于“縱逸”。這些界定使我們感覺到編撰審定者對所著錄書家的品評標(biāo)準(zhǔn)是經(jīng)過一定斟酌的,絕非草率而為,籠而統(tǒng)之。當(dāng)然并不是說以這樣的標(biāo)準(zhǔn)對全部的內(nèi)容進(jìn)行了審定。
由此,不能不使我們聯(lián)想到米芾的書法。米芾書法的主要特點(diǎn)即雄健飄逸。同時(shí)代及后來的書論家又多用“逸”字來盛贊米芾書法。如蘇軾說他“超逸入神”(4),趙構(gòu)說他“自然超逸”(5),魏了翁說他“雅逸”(6),王柏說他“逸邁奇崛”(7),蔡絳說他“飄逸”等等(8)。頗為自負(fù)而且善于精鑒的米芾當(dāng)然對這一點(diǎn)有充分的認(rèn)識,并把他作為評判佳書的重要指標(biāo),這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米芾不僅是著名畫家,在書法方面還是“宋四家”之一,“蘇黃”因是“元祐黨人”,被排除在著錄之外,更不可能參與編撰,而蔡京、蔡卞雖然有書法上的功夫,卻談不上有什么書學(xué)思想。所以編撰評定的擔(dān)子自然更多的落實(shí)在米氏的肩上。而米又極重書作中的“逸氣”,這使我們聯(lián)想到《宣和書譜》中以“逸”評賞書作的小傳可能多由米氏審定。
(二)作為考察書家傳記編撰者的佐證
《宣和書譜》卷十五《王羲之傳》說:“梁武帝評之(指王羲之)曰:‘勢如龍躍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xùn)。其亦善于擬倫也。”可見,作者對這種評論方式是給以肯定的。然而,這確非米芾的立場,因?yàn)樵谒磥磉@樣的品評語言是:“征引迂遠(yuǎn),比況奇巧——是何等語?” (9)
而京、卞在《宣和書譜》之小傳中皆被作者冠之以“飄逸”,這很可能是編撰者中趨時(shí)風(fēng)而又阿諛蔡京者所為。因?yàn)槊总勒J(rèn)為“蔡京不得筆”,而蔡卞雖得筆然缺乏的正是“逸韻”(10)。米芾能在召對時(shí),敢于面對皇上直陳上述的觀點(diǎn),也絕不會(huì)在文中違背自己意愿為他們寫上“飄逸”二字了。
這些文章雖不能明確找出其具體作者,但通過這些考察至少有助于對判斷米芾的審定工作給予一點(diǎn)參考。
三、關(guān)于“‘逸字”問題
卷十二劉正夫一傳中,說他“晚年間作‘逸字,獨(dú)藏于家”。有學(xué)者將“逸字”解作“草書字”(11)。若解作“草書”,則《宣和書譜》中唯此一處用這種說法。其他各處則直接寫作“草書”。并且書史上從沒有把草書稱作“逸字”的記載。另一種解釋則是寫“逸”這個(gè)字,晚年偏愛寫某字的現(xiàn)象不是沒有,如時(shí)下有些人專愛用毛筆表演“龍、虎、劍”一般,但這種說法不甚合情理。所以,我雖對前一種說法表示懷疑,但相對來說后者卻更可信。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今提出來以引起注意。
本文從“逸”字這一著眼點(diǎn),整理了對《宣和書譜》的一點(diǎn)想法。在論證過程中盡可能地對前賢研究的現(xiàn)狀進(jìn)行理解和思考,倘能起到一點(diǎn)補(bǔ)充作用,則是這次學(xué)習(xí)的最大收獲。
注釋:
(1)趙孟頫《跋唐懷素論書帖》云:“懷素所以妙者,雖率意顛逸,千變?nèi)f化,終不離魏晉法度也。”
(2)《宣和書譜》卷十七·毛喜一傳:“其(指毛喜的草書)奔放超絕處,論者以比平郊逸驥,晚景飛隼。其亦善取況者也。”說明作者是贊成這一說法的。“逸”在此解作“奔逸”,是筆者所加,非原文。
(3)《宣和書譜》卷十二·岑宗旦一傳:岑氏評懷素書為“閑逸”,作者認(rèn)為:“其自得于心,積學(xué)于外,而其吐論所以不愧古人”。表明這也是作者的看法。
(4)《珊瑚網(wǎng)·書錄》卷二十四下:蘇軾云:“米書超逸入神。”
(5)宋高宗趙構(gòu)《翰墨志》:“然喜效其(指米芾)法者,不過得其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fēng)骨,自然超逸也。”
(6)《書林藻鑒》卷九:魏了翁云:“南宮大字雅逸,細(xì)書結(jié)密,皆有可法。”
(7)《書林藻鑒》卷九:王柏題南宮小字詩稿云:“寶晉之字,幾滿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邁奇崛之勢,是其長也。”
(8)宋蔡絳《鐵圍山叢談》中云:“米芾元章有書名,其投筆能盡管城子五指撮之勢,翩翩若飛,結(jié)字殊飄逸,而少法度。其得意處大似李北海,間能合者,時(shí)竊小王風(fēng)味也。”
(9)米芾《海岳名言》:“歷觀前賢論書,征引迂遠(yuǎn),比況奇巧,如‘龍?zhí)扉T,虎臥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yuǎn),無益學(xué)者。故我所論要在入人,不為溢辭。”
(10)米芾《海岳名言》:“海岳以書學(xué)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shù)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jiān)描字,蘇軾畫字。上復(fù)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11)這一解釋見潘運(yùn)告主編、潘運(yùn)告譯注的《宣和書譜》,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1999年12月,第1版,第233頁。
參考文獻(xiàn):
[1]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
[2]楊伯峻.論語釋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3]黃休復(fù).益州名畫錄[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