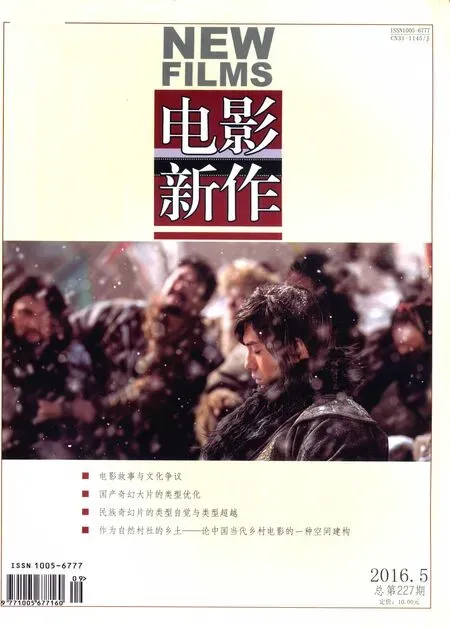亂序時空、鏡中幻影與族群記憶
杜 梁
亂序時空、鏡中幻影與族群記憶
杜 梁
近年來,隨著《鬼吹燈》《盜墓筆記》引領盜墓文學興起,盜墓題材電影再度攪動了“池中春水”。從墓穴景觀所承載的社會歷史功能來看,國產盜墓題材作品與好萊塢電影傳遞出白人中心主義與反殖民意識兩種文化傾向。《盜墓筆記》中錯亂的時空與虛幻的人設,共同支撐起這部模糊了現實與臆想界限的個人口述史,然而透過重重迷影,似乎又可以窺探到內蘊在本民族文化中的神秘主義傾向與社會歷史、族群記憶的對沖與碰撞。
盜墓 時空 幻影 族群記憶
所謂“盜墓”,原本指的是淵源古遠的私闖他人陵墓并盜竊其中陪葬物品的非法行為。然而,在文學與電影作品的書寫過程中,盜墓之事逐漸被遮蒙上文化神秘主義的面紗。這種轉義不僅僅源于逝去墓主借由各種異物巧具、奇門遁甲之術與陵墓“闖入者”斗智斗勇的傳奇軼事,同樣也是由于部分盜墓賊為了掩飾自身丑行而編織出各色怪力亂神的故事以蠱惑他人。久而久之,不單《搜神記》《醒世恒言》等古代小說、筆記中收錄過因盜墓致使死者復生的故事,連《漢書》《晉書》等正史中也有所記載。①可以說,盡管厚葬風俗興起后,深埋地下的奇珍異寶成為吸引不法者“發丘”“倒斗”的首要因素,但是對于無意以身犯險的旁觀者而言,盜墓者們所憂慮、畏懼的未知之境的險惡乃至交通生死的可能性,恰恰構成了前者滿足獵奇心理的絕佳戲劇張力。
以盜墓為主題的影片僅僅是探險題材電影的龐大陣列中一個細小分支。從域外視角進行審視,其中最為“耀眼”的自然是1981年上映的《奪寶奇兵》,基本上確立了此后好萊塢同類文本的基礎敘事程式,也常常被看做這一亞類型的“鼻祖”。此后《木乃伊》系列(1999、2001、2008)、《古墓麗影》系列(2001、2003)、《國家寶藏》系列(2004、2007)等盜墓題材影片大多并未超脫出探險故事的慣用套路,基本上是“美國西進運動或隱或顯的殖民化書寫,白人探索者強力征服古老神秘的“異域”部落力量,強調了現代社會對古老文明的全盤統治,甚至以白人的洞見終結外界對于神秘歷史、神話、傳說的紛紜雜談。”②
相較之下,國內的盜墓文本要更加復雜,較早涉及此類情節的作品至少可以追溯到李翰祥的《大軍閥》(1972)和《銷魂玉》(1979)。20世紀80年代,香港也曾出品過《魔翡翠》(1986)等全盤復制《奪寶奇兵》模式的影片,得其形未得其神;內地攝制的《東陵大盜》系列(1986、1987、1988)、《夜盜珍妃墓》(1989)等影片則囊括了民國時期軍閥武裝洗劫、守陵人監守自盜、民間高手施計取物等種種亂象,同時不乏針砭時弊的現實拷問與護寶退敵的民族情懷。90年代《天朝國庫之謎》(1990)、《夢斷樓蘭》(1991)等作品延續了寶藏顯影——遺跡探秘——多方亂斗——衛戍陵墓的基本敘事脈絡,而此間內地與香港聯合制作的《古今大戰秦俑情》(1990)則借由時空穿越的方式勾連歷史長河中的幾個時間節點,從而面向歲月縱深處挖掘地下墓葬空間所承載的文化內涵。進入新世紀,《神話》(2005)、《刺陵》(2009)、《決戰剎馬鎮》(2010)等作品雖然時空背景有所不同,但基本沒能實現敘事與文化層面的突破。近年來,在《鬼吹燈》《盜墓筆記》引領下,盜墓文學的興起,加之以IP改編為核心的泛娛樂策略逐漸成為大眾傳播媒介的普遍選擇,盜墓題材電影再度攪動了“池中春水”。
拋開存在版權紛爭且內容無關盜墓的《九層妖塔》不談,《尋龍訣》與《盜墓筆記》均傳遞出對于歷史和記憶的偏向。前者通過最后一代摸金校尉胡八一與王凱旋遠赴美國后的落魄經歷,書寫了傳統文化行將消弭于現代性浪潮中的彷徨與無奈;后者則經由吳邪虛實難分的講述,試圖在現實人生與盜墓經歷這兩種記憶之間辨明真假。在這兩個文本中,又可以剖解出面向歷史記憶來求證自我存在的嘗試,對于胡八一追索的舊日時光而言,群體生活中的完美女性丁思甜竟然與揮散不去的夢魘女尸魅影合一,帶有象征意味的變幻女體恰巧顯露出主人公在苦難過往與疏離現實之間的反復掙扎。作為盜墓家族中唯一一個并不了解地下秘密的“他者”,吳邪迫切地想要尋回原應延續下來的家族記憶,甚至以此為基點來回望本民族文化神秘主義的歷史原點。
進一步看,吳邪正是借助地下陵墓這一精神分析學意義中的“子宮”,才完成了返歸文化神秘主義后的脫胎重生。值得注意的是,除非受到外力作用,否則墓中景象的變化僅僅呈現為灰塵的層層覆蓋。而看似恒定與靜態的陵寢內部,實則暗藏著各式各樣的機關陷阱、禁制術法來保衛逝去靈魂的萬載無危,更嚴重的人身威脅則來自于作為歷史象喻符號的墓穴主人死而復生,二者共同支撐起生人免進的千古死局。幾千年來薪火暗傳的摸金校尉與土夫子們穿越狹窄的“盜洞”后,無形之間完成了古今場景乃至生死兩界的巧妙轉換,凝結千年的地下景觀被建構為勾連歷史端點與當下時間的象征性空間,同時也是聯結陰間與陽世的界交之處。基于墓穴的多重空間意義,作為家族中唯一“局外人”的吳邪才能夠重新體味本族群的盜墓秘辛,輕易跨越兩千年的歲月變幻,與古象王和蛇母等留存于家族筆記中的人物正面相對。在克服重重險阻之后,吳邪事實上完成了從無知“小白”到個中熟手的身份轉換。
從墓穴景觀所承載的社會歷史功能來看,國產盜墓題材作品與《奪寶奇兵》等好萊塢電影傳遞出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化意識。由盜墓轉向護寶,是此類文本出于規避道德風險的需要而采取的共同選擇。然而,看似無甚分別的守衛者形象背后,卻存在著歷史遺留寶藏歸屬權的爭奪,甚至可以從中讀取出白人中心主義與反殖民意識的對立與沖突。《奪寶奇兵》《木乃伊》《古墓麗影》等文本中,來自西方的裝備精良的歷史探索者天然攜帶著一種行為悖論,他們先從異域墓穴中偷盜神圣之物,隨后又不計報酬地將之捐獻于國家博物館,看似大公無私的處事風格卻剛好是對其“世界警察”的身份自詡的絕佳諷刺。印第安納·瓊斯們不斷推動著現代意識的齒輪來“碾壓”古老文明,他們在凝固時空中與遠古時代對話并且充分炫耀自己的優越性,深蘊其中的仍舊是帝國主義式的殖民幻想。
相較之下,國產盜墓題材影片所塑造的守衛姿態顯得更為自然。其中大部分文本巧妙地選擇以動蕩不安的民國時期作為盜墓傳奇的背景,因此衛護既有流通價值又作為本民族歷史象征符號存在的地下寶藏免受外敵侵擾,自然也屬于反殖民侵略行動的組成部分。顯而易見,陪葬器物的所有權決定了守護者立場的合法性。《盜墓筆記》則試圖越過對吳邪、裘德考兩伙賊人的道德審判,轉而構建兩個更為可怖的指代歷史陰影的野心家形象。對外部世界的滄海桑田一無所知的古象王與蛇母,卻仍舊“天真”地嘗試完成統一或者說報復天下的癡夢,吳、裘雙方在卷土重來的古代妖魔面前暫時性地握手言和,攜手完成守護塵世的目的。可惜的是,苦心孤詣追求長生奧秘的裘德考為何突然良知發現,影片中沒有給出足夠可信的證據。不過,標靶的轉換至少表明了國產盜墓影片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也即相比于外在的“假想敵”而言,自我背負的記憶包袱更需直面。
地下場景的“錯亂”是源于空間所承載意義的轉換,經由吳邪的腦中幻想而肆意延展的時間則演化出凝結、流動與跳躍等多種形態。少年、青年、中年時期的吳邪分別承擔著觀看者、行動者和講述者的不同身份,凝視與訴說的主體都是盜墓活動。敘事視角在主人公人生中三個節點之間往復躍動,削弱了這趟蛇母陵之行的可信度,或許盜墓行動僅僅是少年“小三爺”的腦中幻想,也可能是中年吳山居老板信口編纂的無稽之談。③相比之下,“悶油瓶”張起靈的人生軌跡更為“詭異”,他是每間隔一段時間個體記憶就自動“格式化”的“天授頌詩人”的傳承者,而每逢關鍵時刻他又能保持著在場的狀態,故而其生命歷程恰如時斷時續的虛線一般模樣。此外,蛇母陵中蘊藏的乃是關于永生的終極奧秘,盡管古象王與蛇母沉睡兩千年換來的只是死亡前的片刻清醒,但是他們的確通過自我的“樹化”實現了時間端點的跳躍。可惜的是,此二人對于永恒的生命形態的貪求,在吳邪一行攪亂了原本幾近凝固的地下時空后被打散。
從少年吳邪的角度看,他對于家族秘密的好奇以及對于葬禮儀式的陌生感構成了一對撕扯靈魂的反作用力,唯有通過一場臆想中的“遠征”才能夠予以緩解。當少年吳邪在家族葬禮上隨著眾人目光凝視講述“浮生若夢”的評彈女人,也即開啟了他探尋心中隱秘欲望的歷程。畢竟“老九門”中的場景能夠與蛇母陵墓進行一一對位,評彈女人與蛇母佩戴著相似的護甲、吳邪意外闖入的滿是鏡子的房間與蛇母陵中場景如出一轍、蒙面人搶走的轉經筒又與開啟墓門的鑰匙形狀相近,這些類比恰恰提供了佐證,當少年吳邪所能夠接觸到的日常生活場景蒙上文化神秘主義面紗后,便在他的腦海中生發出一場勘尋家族記憶的冒險游戲。
照此邏輯來看,盡管影片頗有些“賣腐”意味地組織起“瓶邪CP”,但“悶油瓶”張起靈不過是少年吳邪意外闖入藏有家族秘密的閣樓后發現的鏡中幻影。換句話說,屬于“老九門”的群體記憶在吳家唯一的“干凈人”身上發生斷裂,吳邪被共享地下秘密的父輩們排擠在外,而張起靈正是他將自我植入家族歷史后找到的合法身份,同時也是精通墓中各類機關的理想化的自我,由此導致中年吳邪口述的版本中,難以區分“我”和“他”(張起靈)誰才是敘事主體。有趣之處在于,張起靈擁有漫長壽命但無法保持個體記憶的延續性,吳邪走過的生命歷程雖然短暫卻能夠借用手中鏡頭記錄歷史,當前者頻頻對鏡自觀來留取自我存在的證據時,后者主動走上了“證人”的位置。恰如影片中多次出現的那幅名為《創造亞當》的油畫,賦予張起靈記憶/靈魂的吳邪正是這場幻夢中唯一的“造物主”,故而地表塌陷處兩人沒能成功“牽手”,與蛇母決戰時“小三爺”卻能夠踏著飛輪來拯救“悶油瓶”。
在吳、張二人主體意識的糾葛外,長達兩千年的時間隧道的原點處,恰巧站立著一位能夠定義、解釋這種身份謎團的造墓者。正是經由“小哥”張起靈在錯亂時空中的穿插與勾連,才真正將歷史線段的兩端聯結起來,作為盜墓歷史終結者的吳邪與修建陵宮的無面目的“鐵面生”得以遙遙相望。也正是在這層意義上,張起靈化身為溝通過往與未來的守護神靈雅努斯④。影片結尾處復現了吳邪與張起靈在吳三省家門口錯身而過的場景,然而隨著鏡頭的切換,兩人卻分別身披鐵面生與無名蒙面者的外衣回首對望,及至于此,吳邪與其他三個形象之間的對應關系變得更為復雜。即使不考慮將原著小說繁雜的情節、網絡作為電影版本的敘事背景,單從吳邪多次佩戴鐵面生的狐貍面具來看,兩人之間也必定存在著一種宿命般的聯系,甚至可以說,吳邪正是鐵面生所選定的解謎者。⑤從少年吳邪手中奪走轉經筒的蒙面人則是他始終難以忘懷的恐懼之源,張起靈與蒙面人的巧妙對位似乎也在不斷提示吳邪,他永遠無法成長為一名合格的盜墓人。考慮到面具所攜帶的象征意義可能會因佩戴者不同而強化或轉義,同一張假面下主人的身份也存在不確定性,故此,少年吳邪出于自我英雄化的原由而臆想出的張起靈形象不過是鏡中幻影。
暫且將目光從鬼神蠻妖的世界中抽離出來,對經由歲月“腐蝕”的墓穴之主進行審視,不難發現他們幾乎都以非本來面目的“幻影”身份視人。據說《盜墓筆記》出于規避審查的需要,才將原著中掌握長生秘術的西王母與其情人周穆王更替為不見史書記載的西域蛇母與古象王。⑥這兩位以沉睡千年的代價換來片刻清醒的“替身”,遵循了同題材作品中古代惡魔的形象定式,野心勃勃地試圖完成昔日未竟的霸業。更有甚者,這位蛇母或許僅僅是少年吳邪的“厭女癖”心理的折射,當他凝視薄施粉黛的評彈女藝人時,卻不自覺地將之認作象征“陰界”且仇視世間的“妖女”。
在同類形象序列中,出場頻率最高的非秦始皇莫屬,《古今大戰秦俑情》《神話》《木乃伊3:龍帝之墓》(以下簡稱《龍帝之墓》)等作品中,均將其視為來自古代的殘忍無情的君主。不同之處在于,前兩部作品均將尋求長生藥物以維系其專制統治的秦始皇視為造成陵中人千年孤守的罪惡源頭,這種反感源于先民凄慘經歷形成的共同記憶,專制君主的身影至今仍是揮之不去的民族夢魘。《龍帝之墓》則緊抓這段“黑歷史”,不遺余力地全盤妖魔化,將龍圖騰、秦始皇、兵馬俑視為一體化的試圖馴服全世界的邪惡力量,但卻非東游西蕩的美國“浪人”的一合之敵。秦始皇的本來面目如何已經不再重要,經過符號意義的再建構,他已經變化為暴君與惡魔集合而成的幻影君王。
錯亂的時空與虛幻的人設,共同支撐起這部模糊了現實與空幻界限的個人口述史,然而透過重重迷影,似乎又可以窺探到內蘊在本民族文化中的神秘主義傾向與社會歷史、家族記憶的對沖與碰撞。正如影片中的評彈曲詞所言:“浮生似夢夢浮生,真作假時假亦真。人生如鏡鏡映人,但愿是影避凡塵。”當吳邪們吹散蒙在古老墓門上的塵沙,隨即顯現出的是通向民族歷史源頭與遠古菲勒斯崇拜的危險路途。也許是為了避免陷入道德窘境,對于銀幕上的摸金校尉與土夫子們而言,其以身犯險的誘因遠不止于物利和怨仇,探尋自我身份的主體性、追索族群記憶才是真正目的所在,而闖過宿命遺音、尸蹩大潮等層層關卡的幸存者,能夠刷新自我認知,甚至可以隨意鄙夷古老陵寢所象征的權力體系。或許唯有如此,游走于地宮、陵寢間的探險者們才能夠重返“本是無邪帶點真”的人生狀態。
【注釋】
①王子今:《中國盜墓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289頁。
②聶偉、杜梁:《“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海外大片——分賬片引進二十年》,《當代電影》2014年第11期,第157頁。
③《盜墓筆記》片方曾發布過一則名為《<盜墓筆記>“驚喜升級版”彩蛋》的視頻,中年吳邪親口向前來采訪的作家坦誠,他講述的故事并非是對盜墓經歷的真實還原。視頻觀看地址:http://video.sina.com.cn/ view/250709825.html
④雅努斯(Janus):羅馬最古老的神靈之一,掌管著一切門戶、通道乃至事物的起始與終結。傳說中他擁有兩副面孔,能夠分別看向過去和未來。
⑤網絡上流傳的一則名為《盜墓筆記到底講了什么故事——其實就是西王母引發的千年血案》的帖子,提供了另一種解讀原著的方式:吳邪一族本就是鐵面生的后人,而他自己更是背負著后者記憶的“實驗品”。同樣身負多人記憶的“悶油瓶”則是鐵面生一族的死敵,由于他難以承受記憶沖突造成的壓力,故而逐漸養成了刪除記憶的能力。“悶油瓶”曾為了保護吳邪的本真狀態而多次助他封存記憶,但是后者最終還是選擇承襲家族追求長生的欲望,二人遂定下十年之約。原貼網址已經刪除,但轉載者普遍認為此文作者是暖和狐貍,參見《盜墓筆記到底講了什么故事——其實就是西王母引發的千年血案》,磨鐵中文網:http://www.motie.com/ topic/6184
⑥洋洋:《<盜墓筆記>導演&編劇專訪》,時光網:http://news.mtime.com/2016/08/03/1558187.html
杜梁,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電影學博士。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部級社科研究項目(GD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