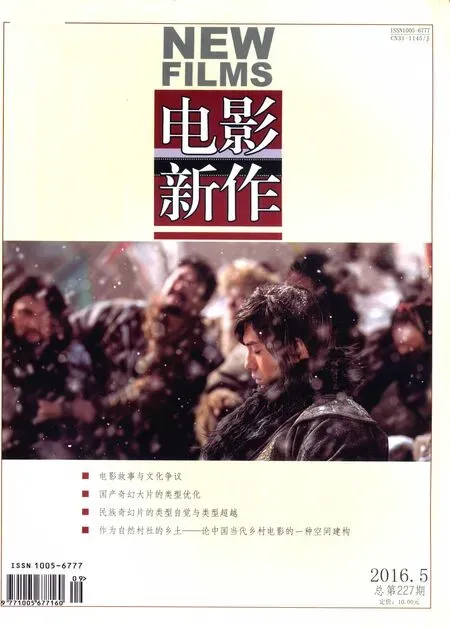行政力量的補充:抗戰前國民黨政權電影生產動員體系中的新生活運動
李九如
行政力量的補充:抗戰前國民黨政權電影生產動員體系中的新生活運動
李九如
抗戰爆發前,國民黨政權發動的新生活運動,對該政權的既有電影生產動員體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表現在獎勵、扶助、制定標準、共同/委托制作等幾種官方原有的電影動員方式之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新生活運動也在國民黨中宣會(部)的電影界談話會中產生了影響力。
新生活運動 電影生產動員體系 電影界談話會
1934年,國民黨政權發動了一場旨在控制社會的新生活運動,這場試圖以“禮義廉恥”改造國民的“衣食住行”的運動波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電影自然也不例外。①從某種意義上說,新生活運動是對國民黨政權控制社會的行政能力的補充和加強,它的“由公務人員作起,再推之民眾”的運動程序說明了這一點。②這就意味著,既有的國民黨官方體系,必然要首先受到該運動的推動和刺激。這不僅表現在運動的思想內容所試圖對當時已經陷入官僚主義的國民黨官方體系產生的影響,更表現在運動本身對這一效率低下、“腐敗無能”的政權的刺激上,盡管效果如何人們評價不一。在電影管理領域,國民黨政權的電影生產動員體系就受到了新生活運動一定的影響,控制能力得到了提升。
在抗戰爆發前,國民黨電影檢查部門(無論是教育內政部電檢會還是中央電檢會)所具備的某種“生產性”,通過所謂“剪刀”政策改造國產電影特別是左翼電影的意識形態語義,并不足以構成真正的電影生產動員機制。其實,甚至在整個國民黨政權大陸時期,該政權的電影統制都并沒有形成類似于蘇聯電影體制或1949年中國新政權建立之后的社會主義電影體制中存在的那種生產動員體系,也從沒有獲得過同等的動員能力。但這并不表明南京國民政府沒有嘗試過朝著相似的目標前進。在20世紀30年代初中期,通過不斷地強化,南京國民政府也形成了一個不是那么完備和統一的電影生產動員體系,這個體系主要由中央宣傳委員會(1935年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更名中央宣傳部)下屬的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1936年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成立后撤銷③)和電影股(后更名電影科、電影事業處④)兩個部門,以及軍委會政訓處電影股、教育部及其下屬機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等組成。⑤在這一時期,實際能夠面向社會產生動員能力的“主力”,是中宣會(部)和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尤其是前者,其在1937年抗戰爆發以前所發起的三次全國電影公司負責人談話會,成為戰前最主要的電影生產動員機制。與之相比,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就其職權而言雖然主要并不是一個生產動員部門,但它所宣傳推廣的那一套“電影教育化”的理念,⑥深刻影響了中國電影的生產,更重要的是,該協會在教育電影的生產動員方面,發揮過關鍵性的作用。當然,在前述電影統制體系本身的電影生產動員中,新生活運動也成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戰前的中國電影格局中,國有或者說官營的電影生產,只占據很小的比例,上海的那些民營電影機構,構成了電影生產的絕對主體。在這種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的電影統制,在電影生產方面,其實主要依賴于生產鏈條末端的審查機制,來消極性地防范逸出其意識形態控制的電影。至于積極主動地引導乃至動員電影生產,南京國民政府很早就意識到這是比較難做到的。除了前文提到的電影檢查部門的“生產性”之外,囿于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性質和經濟制度等原因,它不太可能短時間內做到消滅所有的民營電影機構,而完全以國有化的電影機構取而代之,因此其最初設想并付諸實踐的帶有生產動員性質的行動,就是與民營電影機構或社會人士“合作”。這一點也鮮明地體現在電影股或后來電影事業處的工作任務中:它的兩項重要任務就是“指導”和“聯絡”國內各電影生產機構和公司。⑦從廣義上來說,所謂合作,包括獎勵、扶助、制定標準、共同/委托制作等幾種方式。⑧新生活運動在這幾種具體的合作方式中,分別發揮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另外,作為對于電影生產動員能力匱乏的代償,國民黨政權還在1934年后發起了電影界的談話會,新生活運動于其中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一、獎勵與扶助機制中的新生活運動
就扶助電影業而言,可以說它是當時國民黨內官方人士的一種共識。早在1933年浙江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給國民黨中央的一份呈文中,為了“挽救電影藝術為中共宣傳”,就已經提出了“由政府撥款津貼各私人電影公司,獎勵其拍制宣傳黨義的影片,并給予種種援助,務使其不因營業關系致不得已而受共產黨的影響和利用”的挽救辦法;⑨同樣在1933年,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在給中國電影指明“出路”之時,也提出“政府應盡力協助”的問題,認為“政府與人民通力合作,雙方進行,凡有困難,可隨時向政府陳述,以求補救,然后中國影業,始有發展之望”。⑩但是,這基本上只是國民黨內一些人士的美好愿望,由于經濟困難,而同時大量的經費又被挪作戰爭等用,更由于由此導致的專業化行政系統的不健全,因此事實上南京國民政府并沒有“閑錢”和常規機構去扶助電影業。?當然,扶助電影業并非只有資金支持一途,政策上的優惠或者便利也是一種扶助,在這方面,南京國民政府的確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優化電影檢查程序等,但總的來說,這種“小恩小惠”意義不大,更算不上“通力合作”。扶助不成,尤其是經濟上難以對民營公司構成影響力,則所謂的生產動員,也就缺乏了根本的保障。退而求其次,獎勵也是一種能夠正面引導電影生產的方式,為此中央宣傳委員會于1934年特制定了《獎勵電影事業辦法》,宣布“內容合于中央規定之制造標準”的國產影片可申請專門組織的“國產影片評選委員會”審核從而獲得獎勵。?“辦法”出臺之后的1936年,中央宣傳部根據“辦法”出面組織了第三次國產電影評選,盡管在這次評選中獲得優勝的影片“大致已脫離年前風行一時而帶煽動意味之作風”,但頗為吊詭的一點是,直接宣揚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新生活運動、而且此前已經因此得到褒獎的《國風》也參加了評選,結果卻是一無所獲,該片實際的創作者朱石麟也未獲得作為“從業員”的獎勵。的確,其他獲獎影片諸如《凱歌》《船家女》等也已經不是純粹的左翼電影,?但它們那“左右搖擺”的狀態畢竟不如《國風》來得“純正”。這個耐人尋味的結果,表明獎勵也未必能真正促進國民黨想要的那種電影生產動員。進一步說,“新生活電影”《國風》的落選,反襯了國民黨一直致力于建構的電影統制體系本身作為一種專業化行政系統的嚴重缺陷。?關鍵是,旨在改善官方的社會控制能力的新生活運動,在獎勵和扶助機制中的作為,也乏善可陳。直接為新生活運動鼓與呼的《國風》最初受到的嘉獎,來自中央電檢會,隨后在給聯華公司的公函中,它又鼓勵后者“嗣后對于此項影片,仍需加倍努力”,并表示“本會實有厚望焉”,在此過程中,作為新生活運動的推動機關,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對《國風》的注意,卻需要中央電檢會專門致函提醒。?
二、制定標準與共同/委托制作:“新生活電影”劇本的征求等措施
更能呈現出南京國民政府電影生產動員能力在組織上的問題的,是制定標準及與之相連的共同/委托制作意義上的合作。為了引導電影的生產,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早于1932年就審議通過了一份由中宣會擬定的關于電影生產標準的倡導性文件《國產影片應鼓勵其制造者之標準》,這個標準基本上把國民黨政權的一切統治訴求都一股腦兒放了進來。?同時,中宣會還擬定了《中央宣傳委員會征求電影劇本辦法》,其中對于征求電影劇本的標準,其要求與上述影片的標準完全一致。?仔細查看這個標準可以發現,它所提倡的東西,其實差不多正是不久之后新生活運動所要倡導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些標準落實到具體的實踐當中,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再次暴露了作為一種專業化行政系統的國民黨電影統制體系的短板。如果說征求劇本還算是一種落實方式的話,那么國產影片的標準則看起來根本沒有落實到創作中的途徑。誠然,根據規定,電影股(科、事業處)承擔著指導各影片公司“并設法扶助其事業之進展”、并且聯絡這些電影公司和“電影作家及其他電影界份子”的職責,?但實際上所謂的“指導”和“聯絡”所建構的只可能是一種非常松散的權力關系,在缺乏制度尤其是組織保障的前提下,它們所能夠形成的影響力,甚至還遠不如處于秘密狀態的那些身為編劇的中共地下黨員們的“地下”活動。事實上,面對電影生產動員的任務,中宣會(部)不僅缺乏組織手段,無法將各電影公司納入自己的麾下,而且它甚至缺乏這種意識,或者說它其實是對于社會的組織化有某種疑慮心態。一個顯明的例子是,當1936年文化界的救國運動風起云涌的時候,國民黨中宣部卻針對各種救國會組織的出現發表了《中央宣傳部告國人書》,以“陰謀論”的語調,指認“共黨”和“社會民主黨余孽”,利用“民眾之熱情,乘機煽惑,藉文化團體知識分子為工具,以逞其危害民國破壞秩序之陰謀”。
?不管這種指認有多少事實依據作為支撐,國民黨的態度本身就表明了它對于組織化動員社會的猜疑和恐懼。這與熱心于組織和動員活動的共產黨形成了鮮明對比。?
對于通過組織化來控制社會的猜疑或者無能,正是導致中宣會(部)傾向于與電影界之間采取合作方式進行生產動員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正是因為行政組織能力上的薄弱,合作的效率變得十分低下。征求劇本是中宣會(部)等電影統制部門實施共同/委托制作意義上合作的重要方式和步驟,但就其實施效果來看,應當說并不理想,或者說根本就是名不符實。自中宣會于1933年制定了征求劇本的辦法之后,一時之間,面向社會公開征求電影劇本幾乎成為一種風潮。表面看起來,中宣會制定的在公開的大眾媒體上登載啟事,并通過主動聯絡文藝界、電影作家甚至“對于電影感有興趣者”以求獲得劇本的方法,?的確造成了官方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合作,但實際情況卻往往是,征求劇本成了國民黨官方內部的一種“圈內游戲”。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這種征求劇本的活動,其結果往往是國民黨內的官方人士成了征求活動的“大贏家”,比如江蘇教育廳舉行的兩次劇本征求,第一次選中了蔣星德的《小天使》,第二次選中了王平陵的《慈母心》。而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征求下,錄取的仍然是他們二人的作品《大地回春》和《生命線》?。這兩位作者可并非一般的文藝界人士,更不只是“對于電影感有興趣者”,他們都是國民黨政權系統內部的人。?這就意味著,所謂的面向社會征求劇本,并沒有真正將社會動員起來。當然,從《小天使》被送交聯華公司拍攝,并獲得一定成功的角度看,則在委托制作方面,以合作進行動員的模式,也并非一無是處。同樣,作為“新生活電影”的《飲水衛生》,也以委托制作的方式,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在征求劇本的過程中,新生活運動作為一項內容,也被列為官方希望得到社會響應以期進行合作的創作對象或題材。早在1934年3月,國民政府的全國教育電影推廣處,就認識到“蔣委員長創導之新生活運動,確為復興民族、挽救頹風之要圖”,因此決定“將新生活運動須知及其意義等,編為故事,攝制影片”,為此該處一方面“特專函蔣委員長鄧秘書文儀請求供給材料”,另一方面“委請小說家徐卓呆編撰劇本”,以供將來攝制。?這應當是最早響應新生活運動進行電影動員的舉動了。其后,國民政府教育部為向全國提供教育電影以實施電影教育,決定在選購影片之外自制影片。所謂自制影片實則主要還是與有制片能力的機構合作,由此,1936年該部“為求周密起見,決將關于(甲)發揚民族意識,(乙)培育模范公民,(丙)提倡新生活運動,(丁)復興農村四種影片劇本,公開征求,期臻完善”。?在此,提倡新生活運動影片劇本的征求,是作為教育部日常行政工作任務之一部分而提出的:提倡和實施電影教育或電化教育,是當時教育部門的一項常規工作,恰逢此時正在進行新生活運動,而該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社會教育的一種形式,因此它很自然地成為了征求的內容。對于教育部來說,新生活運動的發起,只不過是為它進行多種電影教育的工作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與此不同的是,在此前一年中宣會所進行的一次專門的新生活運動電影劇本征集活動,則將多種形式的教育都集納于新生活運動的名義之下,“不拘一格”地征求劇本:
中央宣傳委員會征集新生活運動電影劇本啟事
本會為推進新生活運動起見,擬于最短期間攝制新生活教育電影數種,用茲提倡,茲特擬定辦法廣為征集是項電影劇本,以便攝制,征求辦法錄后:(一)凡描寫具有新生活運動含義之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實施狀況之電影劇本均可應征。(二)應征之劇本須側重積極之指導,劇情內容尤須注意禮義廉恥之觀點與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之重要原則。(三)應征之劇本除寄送本事外,關于劇本之攝制辦法,凡分幕鏡頭、字幕對白、歌曲動作等均須詳細附列說明。(四)應征之劇本經本會審查認為合用者即專函洽商,否則寄還。(五)應征之劇本選用后每種酬金以現金二百元至四百元。(六)應征期限暫定本年四月底截止。(七)應征之劇本應另紙開列編著人之真實姓名、職業、通訊處等,加蓋圖章掛號郵寄南京本會電影科,并注明應征劇本字樣。(標點為筆者所加)?
應該說,這是一份很詳細的征集啟事,也抓住了新生活運動在這一時期的精髓,并以之要求應征的劇本。與教育部的征集相比,這個專為新生活運動而設立的活動,無疑看起來更有針對性,也將更能促進新生活運動的推廣和展開,有助于它想要實現的社會控制。不過,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樣,因為缺乏有效的組織化保障,這個劇本征集活動,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出它應有的作用,就很成問題了。實際上,在此次征集新生活運動電影劇本之前一年,中宣會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就已經“確定以‘新生活運動’為本年度國產影片之中心作風”,并且還“由中央宣傳委員會函各公司查照切實進行”。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制定標準”,但一年以后,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的方治卻不得不承認,這個號召“尚未有顯著之成就”,并再次呼吁“我電影界深體新生活運動意義之重大”。?
在性質上類似于征求劇本,這一時期一些電影統制機構借助大眾媒體面向社會的互動合作,也涉及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發動之后不久,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上海分會就在上海文化界的新生活運動中扮演了十分積極的角色。該分會不僅在上海發起成立了文化團體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而且很快又在其年會上通過了兩項有關新生活運動的提案:其一,函請總會轉呈中央從速成立全國電影統制委員會以利新生活運動推進案;其二,擬請大會通電全國各電影公司一致擁護及宣傳蔣委員長倡導之新生活運動案。?提案中說到的通電很快發出了,這份通電在簡單地以充滿頌揚的口吻復述了蔣介石關于新生活運動與民族國家之間關系的見解之后,提出了“新生活運動中電影事業之重要”的問題,進而針對電影在新生活運動中所可以發揮的作用,通電指出,“查各種制造品自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一日起均需制印新生活運動標幟……電影界自應從速加印此項標幟并加映新生活須知等全文字幕,俾時時引起觀眾于此項運動之注意,及贊助興趣”,而對于此后影片的內容,通電認為“凡片中種種舉動粗暴、污穢、不潔等表演,與奢麗之布景等,凡與新生活之原則有背、而予民眾不良印象者,倘非萬不得已,力宜避免,處處將禮義廉恥,從衣食住行表現之”,如此則電影對于新生活運動的作用,“自較任何宣傳為大”。?作為一份充滿了天真而簡單之想象與急切之表現心理的通電,可以想見,盡管它利用了當時最先進的通訊工具之一,這可以保證它的迅捷性,但卻不可能賦予它對“全國電影公司”以有效的訓誡力。
然而,我們卻不應該由此得出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是一個只會溜須拍馬而毫無實際價值和作用之統制機構的結論來。恰恰相反,在這一時期,正是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在與社會力量合作攝制教育電影方面,取得了曾被長時間忽略的重要成果,這就是它與金陵大學理學院合作生產的一系列教育影片。可以說,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是那時動員社會力量進行合作生產最成功的電影統制機構,在它的生產動員之下,僅就與金陵大學理學院的合作而言,其出品影片的成果,就遠非中宣會(部)的實際社會動員成就可比(不計該機構下屬中央電影攝影場出品的諸多影片,因為嚴格來說,這些創作不屬于“社會動員”范疇)。中國教育電影協會與金陵大學理學院的生產合作,始于1935年冬天。這年的十月份,雙方出于各自的需要,共同組織了合作委員會,并“聘孫如經(按:這里應為孫明經之筆誤)先生專司其事”。?雙方合作的模式為,“協會負經濟責任,金大負技術責任”,為此,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從其專項資金中提出了四千元作為合作經費。?作為一個有資金和組織保障的合作模式,中國教育電影協會與金陵大學理學院的合作,比之前文提及的那些合作動員,必然會更加可靠而有效率。不過,應當看到,在合作的過程中,金陵大學理學院所制作的教育影片,是以地理風景、國防常識、自然科學、工業常識等為主的,?盡管這些影片的創作,均出自民族國家的動機,但它們畢竟還是相對“客觀”的,意識形態色彩并不強烈。這意味著,像“新生活電影”這樣明顯為國民黨服務的影片,不會成為這個合作模式的主要生產目標。到1937年,由于金陵大學理學院在制作教育電影上的出色表現,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大規模推行電影教育”之際,也決定與該院合作,委托它“攝制關于科學知識,新舊工業,地理風景,民眾教育,農事改進”等類影片,但根據其規劃,此時的金陵大學教育電影部仍然準備優先攝制地理風景片。?盡管如此,在這一年,金陵大學教育電影部的孫明經,仍然創作了一部宣揚新生活運動的“稿本”《新生活》,準備攝制成影片,只是由于“瑣事及抗戰開始”,導致“未暇開攝”。?
三、電影界談話會的新生活動員
這一時期南京國民政府在生產控制方面缺乏組織化動員手段的問題,已如前述。對于這個問題,國民黨官方不是沒有意識到,只不過,不管是出于主觀還是客觀的原因,它這時的確沒有真正的以一套專業化行政系統去動員社會生產的能力。作為對組織手段匱乏的某種補充或補救,中宣會于1934年發起了第一次全國電影公司負責人談話會,企圖以面對面的直接商談,來彌補其行政體系的欠缺。此后直到抗戰爆發之前,該談話會共舉行了三次,顯現出常規化的傾向,但由于抗戰的爆發,這一傾向被強行中斷。作為一種對話機制,談話會試圖將代表國民黨中央意志的機構和人員與當時國內主要的電影生產創作力量聚集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之中,寄望于以此增強政府權力對社會力量的訓誡力和引導性。正如當時的媒體指出的,“中宣會以國片界與中央行動步驟不能一致,常引起種種意外糾紛,故乘這個機會,發起召集一個全國影片公司負責人談話會”。?按理來說,這應當可以奏效,根據吉登斯的觀點,作為“互動情境”的“場所”是一種“權力集裝器”,因為“它為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的集中提供了可能性”,現在,既然國民黨建立的國家所組織的行政體系并不能形成一個特別有效的“確定情境”,?那么通過將電影公司負責人們直接置入一個具體的、由權力發起的情境/場所之中,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事實上,當中宣會將電影公司負責人們召集在某個具體的空間之中“談話”的時候,它就已經形成了“居于權威位置的個人對另一些個人的活動實施直接的督管”意義上的監控,?在這種監控之下,電影公司負責人們,必然要受到權力的影響。不過,同樣存在的問題是,在談話會上,中宣會(部)固然可以對電影公司負責人們施加其影響,但是會后的“會議精神”落實的問題,在此仍然沒有獲得解決。
談話會自身的機制,也限制了中宣會(部)對電影公司的生產施加影響的可能性。就其機制而言,談話會是以“中央召集—公司提案—開會討論—形成決議”的方式展開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央召集固然在先,但它卻并不為會議設置明確的議題,由此公司提案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談話的議程和走向,而公司提案,則充分顯現了這些社會生產力量的“各懷鬼胎”。因此,與其說談話會是一個傳達國民黨意識形態要求的會議,不如說它是某種政府與社會進行討價還價式對話的公共空間,通俗地說,談話會甚至成了電影公司負責人們向政府進行“訴苦”或者索要利益的大會。綜觀第一次談話會上各電影公司的提案,其中充斥著要求政府在電影檢查上予以“通融”、在電影企業發展上予以“維助”“便利”“保護”等各式各樣的內容,即便是類似“中央顧念西北邊防,提倡扶助攝制有關邊地風土人情之殖邊影片,以促起國人衛國守土之觀念案”這樣的提案,貌似在積極響應政府,而只要一看其背后的提案者就可以發現,它之被提出實則仍是出于提案公司“西南愛國公司”的經濟利益;?第二次談話會三項總提案中的兩項,“國產影片應謀取得國際市場藉廣宣傳案”和“呈請中央積極培植電影人材,與設廠自制電影用品案”,明顯也是與各電影公司利益息息相關的;?到了第三次談話會時,會議干脆直接成了“訴苦”和抗辯大會,據說由于1935年一年中“上海電影公司各方面,好像都受了許多委屈”,導致在會上“各公司的代表,說話的時候,不但很激昂興奮,而且都是把一年來的舊賬,又清算了一次”,這其中明星公司周劍云更是“大發牢騷”,而歐陽予倩甚至直接表示反對政府提出的“作風的統一”的要求。?有意思的是,面對電影公司的“咄咄逼人”,在談話會的機制下,中宣會(部)的表現卻十分“謙遜”而克制,在第三次談話會上,時任中宣會副部長方治不僅再次表示了要“協助電影界發展電影事業”、與電影界“分工合作”的意愿,而且還對“過去兩度談話”之后“不能完全做到電影界同人之希望”而“引為抱歉”。?
就三次談話會所選擇的“地點”分別為首都華僑招待所、上海綢業銀行上海商社、上海市政府。它們作為一種空間,是頗為類似于吉登斯所說的“人們在一天中的一段時間或一生中的一段時期里”進行集中活動的“特別建構起來的場所”的,?在這樣的場所里,行政力量所實施的監控得以順利進行。但也正如吉登斯指出的那樣,在這些場所中,所謂的控制其實又是比較散漫的,其間存在著某種“由于控制辯證法的緣故”而訂立的“論爭協議”,?談話會所彌漫的“訴苦”和抗辯氛圍,正是“論爭協議”的某種體現。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論辯一方的電影公司,出于自身利益,以提案的方式大量表達了其訴求,?與之相比,中宣會(部)方面,卻往往處于匯報工作、應承電影公司要求的境地。當然,中宣會不是沒有利用談話會的機會向電影界發出它的動員要求,這正是談話會發起的根本目的和目標,但至少就第一次談話會而言,時任中宣會主任委員邵元沖對電影界所表達的“幸勿忽略自身所負使命之重大”的要求,?無疑還是淹沒在了電影公司代表們紛紛提出的提案之討論中。由此看來,除了其自身的機制制約之外,缺乏明確而具體的動員要求,也是導致談話會在動員性上差強人意的一個重要因素。不過應當看到,中宣會在此后的談話會上,也因為意識到這一點而對其動員要求有所具體化和明確化,而在這個過程中,新生活運動再次為之提供了某種契機與可能性。在第二次談話會上,官方就明確提到,新生活運動已被確定為國產影片的“中心作風”,因此希望“我電影界深體新生活運動意義之重大,改正過去盲從歐美化之錯誤,去淫靡頹唐肉感浪漫之描述,代以禮義廉恥之訓練,遵照中央規定之標準,分工合作,殊途同歸,以盡社會先導之責任”,并進一步要求電影的“編劇題材”,今后要“務以激勵民族意識發揚固有文化,灌輸科學知識,促進生產建設為經,而以提倡合群團結勇毅果敢之精神,培養重秩序守紀律之良好習慣為緯,庶幾一盤散沙之國民,為電影之教育而知所團結,知所奮發”,?這個關于“編劇題材”的“緯”度方面的要求,顯然直接來自于新生活運動對國民和社會所發出的號召。而到了第三次電影談話會時,中央電影事業處處長張北海更是在會上直接將新生活運動納入了他所提出的關于電影劇本的三條原則之中。這“電影劇本三條原則”分別是:
(一)發揚民族意識,以完成國防電影的使命;
(二)慎重採擇適合時代性之電影題材,以推廣國難時期電影教育的功效;
(三)電影劇情之現實描寫,應充分協助新生活運動之推進。?
第三次電影談話會召開于1936年4月底,此時關于國防電影的討論正在悄然醞釀興起之中。國民黨官方對于國防電影,有一種首鼠兩端的態度,一方面作為一個民族主義政權,國民黨當局自然希望電影被納入民族國家的話語體系之中,以發出電影救國的影像呼吁;而另一方面,它又深恐國防電影被共產黨乘機利用,成為后者借以大規模重返電影界的一個絕佳機會。因此,當電影劇本的三原則之一提出“電影劇情之現實描寫,應充分協助新生活運動之推進”這一條時,新生活運動在此所發揮的作用,就不只是提供某種電影動員契機的問題了。這條原則與第一條關于國防電影的原則同時提出,盡管后于國防電影原則,實際上就抑制或者說限定了國民黨所提倡的“國防電影”的內涵:以協助新生活運動的推進來框定“電影劇情之現實描寫”,這保證了設想中的國防電影,絕對不會出現左翼的、階級論色彩的現實描繪。這是因為,新生活運動的社會觀,恰正與共產黨的左翼意識形態社會觀,構成了直接的對立,最明顯的一點就在于,新生活運動要以民族國家的名義整合整個社會,而左翼意識形態則將社會視作階級對抗的存在(盡管它也倡導并支持民族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新生活運動又參與了與共產黨之間的電影動員爭奪戰。
【注釋】
①大體來說,在抗戰之前,新生活運動是一場追求“整齊、清潔”和所謂“三化”(生活生產化、軍事化、藝術化)的運動,它試圖通過官方的直接推動和教導,改變國民的生活方式。關于新生活運動的介紹和評論,可參見王曉華.“模范”南昌——新生活運動策源地.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7年;溫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②蔣中正.新生活運動綱要.前途,1934年第2卷第6號,第6頁。
③中央黨務月刊,1936年第90期,第318——319頁。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雖然撤銷,但電影的統制工作,還是主要由中宣會(部)負責。
④1935年電影股升格為電影科,至1936年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撤銷后,中央宣傳部下設電影事業處,原附屬于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的劇本審查委員會改隸電影事業處,除此之外,此時的電影事業處,主要是由原電影股(科)升級而成的。參見中央黨務月刊,1935年第81期,第349頁;中央宣傳部電影事業處電影劇本審查委員會組織大綱.中央周報,1936年第402期,第2頁;馬雨農.張沖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12年,第138頁;陳友蘭.電影教育論.商務印書館,1938年,第45頁。
⑤這其中,軍委會政訓處電影股主要是一個制作部門,并且在抗戰前發展很不完善,因此其所謂生產動員能力也就基本上僅限于部門內部,并且這里的所謂動員,也不屬于“社會動員”的范疇。
⑥楊燕等.民國時期官營電影發展史.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3頁。
⑦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鑒1934(影印本).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年,第557頁。
⑧在電影部門之外的一些其他政府部門與當時的民營電影公司的合作,往往屬于委托制作模式,比如1932年國民政府就和明星公司的張石川合作,“攝制津浦、膠濟、隴海三條鐵路沿線風景名勝的宣傳紀錄影片和新聞短片”,照杜云之的說法,這種合作“暗中就是中央在支持張石川的行動”。參見杜云之.中國電影七十年.臺北:“中華民國電影圖書館出版部”,1986年,第148頁。
⑨魯滌平關于挽救電影藝術為中共宣傳呈(附《電影藝術與共產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一).南京:鳳凰出版社,1994年,第386頁。
⑩中國教育電影協會.電影事業之出路.南京:中山印書館,1933年,第13頁。
?比如,當1933年末明星公司因經濟等問題陷入危機之中的時候——該公司于1933年末連續因債務等問題陷入兩場訴訟之中——南京國民政府也曾經“假惺惺地借款幫助它解決困難”,但最終明星公司還是靠《姊妹花》的營業成功而得以渡過難關的。參見明星影片公司迭被控訴.電聲,1934年第3卷第39期,第764頁;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年,第309頁。值得注意的是,倒是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在這一階段拿出了一定的資金對非營利性的社會制作機構進行了扶助,參見后文論述。
?中央宣傳委員會獎勵電影事業辦法.中央周報,1934年第316期,第3-4頁。
?中央宣傳部國產影片評選委員會二十四年度影片評選報告書.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1936年第7-12期,第83-88頁。
?從1933年開始的國產電影評獎,到1936年共舉行了三屆,其中頗有幾部左翼、或者有左翼傾向的電影獲獎。關于這個現象,有一種解釋是說前兩屆組織評獎的郭有守和第三次的主持者張沖,一個是中共秘密黨員,一個同情于中共。這種夸大個人在歷史事件中的作用的說法,固然有其不嚴謹之處,但也說明一個問題,即作為國民黨電影統制的實施者的官僚系統,像它此時其他部門的情況一樣,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現代意義上的專業化行政系統。參見孫健三.中國電影,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兒.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第434-435,33-36頁。
?參見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函第一一二號.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1935年第2卷第9期,第3頁。
?該標準具體如下:1表現中華民族之尊嚴者,2闡揚總理遺教及本黨主義政綱政策者,3表現本黨革命史績者,4激勵民族意識者,5發揚中國歷史的光榮者,6發揚中國固有的文化者,7表演中國國民刻苦耐勞和平中正之精神者,8鼓勵生產建設者,9灌輸科學智識者,10表演改良農工商業及其他實業者,11提倡善良道德者,12提倡合群及團結之精神者,13鼓勵勇毅果敢之精神者,14提倡善良風俗者,15提倡尊重公共秩序之精神者,16破除迷信邪說者,17其他足以補助社會教育者。參見國產影片應鼓勵其制造者之標準.中央周報,1932年第237期,第9頁。
?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鑒1934(影印本).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年,第570頁。
?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鑒1934(影印本).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年,第557頁。
?中央宣傳部告國人書.中央周報,1936年第402期,第1頁。
?一直到1937年電影制片業公會成立,國民黨好像才突然意識到對社會自我組織能力加以利用以延伸其統治鏈條的問題,因此在該會成立大會上,才會有許多國民黨重要官員的高調出場。參見電影制片業公會昨日舉行成立大會.申報,1937年5月24日,第9版。
?方治.中央電影事業概況.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鑒1934(影印本).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年,第571頁。
?參見教廳第二次征求教影劇本結果.民眾教育通訊,1935年第5卷第6期,第121頁;教部征求教育電影劇本揭曉.民眾教育通訊,1937年第7卷第2期,第110頁。
?王平陵當時是中央劇本審查委員會的委員。至于蔣星德則與陳果夫關系密切,抗戰興起后更服務于“航空委員會政治部”。參見陳果夫.移風易俗教育電影編著之緣起及經過.教育電影移風易俗內容述要.教育部中華教育電影制片廠指導委員會印行,出版年不詳,第4頁。
?本市教育界紛起提倡新生活運動.申報,1934年3月20日,第15版。
?教部征求教育電影劇本.民眾教育通訊,1936年第6卷第5期,第110頁。
?中央宣傳委員會征集新生活運動電影劇本啟事.申報,1935年4月8日,第6版。
?中宣會昨在滬召集電影界談話會.申報,1935年4月15日,第9版。
?本市教育界紛起提倡新生活運動.申報,1934年3月20日,第15版。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滬分會昨舉行年會.申報,1934年4月2日,第14版。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滬分會昨舉行年會.申報,1934年4月2日,第14版。
?潘澄候.金陵大學理學院與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合作推行及攝制教育影片之經過及今后之希望.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五屆年會特刊,1936年,第56頁。
?陳友蘭.電影教育論.商務印書館,1938年,第48頁。
?一直到1947年底,金陵大學所生產的全部教育影片,除上述類別之外,還有農事、公民及其他等種類。在所有影片中,地理風景、工業常識類占據了絕大多數。參見金陵大學理學院影音部攝制十六毫米動片目錄.影音,1947年第6卷第7-8期,第103-104頁。
?金陵大學攝制教育影片.民眾教育通訊,1937年第7卷第1期,第146頁。
?孫明經.《新生活》影片擬稿.電影與播音,1944年第3卷第3期,第6頁。
?史諾登.電影公司負責人談話會詳情.電聲,1934年第3卷第12期,第224頁。
?[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3-16頁。
?[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5頁。
?天.電影談話會各公司提案之內容.電聲,1934年第3卷第13期,第247頁。
?中宣會昨在滬召集電影界談話會.申報,1935年4月15日,第10版。
?第三次電影談話會記詳.電聲,1936年第5卷第17期,第406-407頁。
?電影談話會之主席致辭.電聲,1936年第5卷第17期,第406頁。
?[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25-226頁。
?[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27頁。
?第三次談話會上一個頗為戲劇性的小細節,說明了電影公司表達訴求的愿望之強烈,以及談話會本身作為一種控制和動員機制的“散漫”性:在會上,明星公司代表周劍云為發表意見,“前后站起來有七八次之多”。參見第三次電影談話會記詳.電聲,1936年第5卷第17期,第406頁。
?史諾登.電影公司負責人談話會詳情.電聲,1934年第3卷第12期,第224頁。
?中宣會昨在滬召集電影界談話會.申報,1935年4月15日,第9版。
?第三次電影談話會記詳.電聲,1936年第5卷第17期,第407頁。
?關于國防電影,《中國電影發展史》認為這一概念是1936年5月份被提出來的。參見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63年,第418頁。這一說法并不確切,早在1933年11月上海市立民眾教育館就曾“擬開映國防電影”,這表明,至晚在1933年11月之前,國民黨官方就已經在使用這一概念。參見市民教館籌備國防及市政展覽.申報,1933年11月25日,第14版。另外,第三次電影談話會召開于1936年4月,也早于5月份使用國防電影的概念。當然,這一概念真正得到闡釋,也許應當還是1936年5月份以后的事情。
李九如,北京電影學院中國電影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