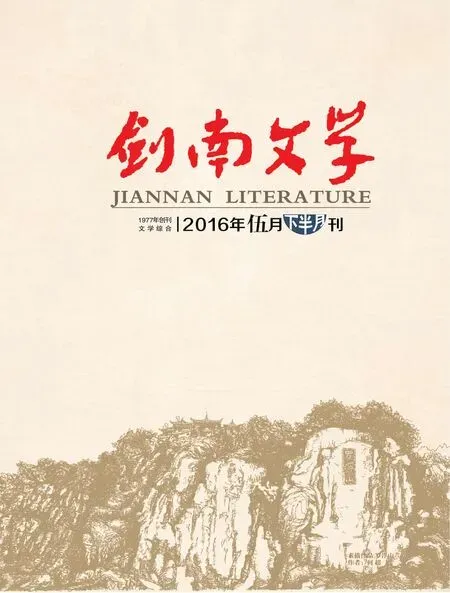新感覺派小說的新因素
□杜 陽
?
新感覺派小說的新因素
□杜陽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西方文藝思潮先后傳入中國。當然主要是現實主義,此外浪漫主義、現代主義也是具有較大影響的文藝思潮。在中國現代文學的三個十年中,中國的現代派作家,都表現出對西方現代派的極大熱情。現代主義在二十年代留下了一片印痕,四十年代尚有余緒,尤其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出現的新感覺派,更鼓蕩起一股波瀾。新感覺派作家們,有的唯新是務,唯洋是求,如劉吶鷗;有的總不滿足已取得的成績和風格,經常要尋求“新的路徑”,如施蟄存;有的十分強調在藝術上標新立異,極其注重“應該怎樣寫”,“努力創造著簇新的小說形式”,穆時英。經過他們的共同實踐,為小說藝術提供了一些新的因素。
一、人物——突現內心活動
新感覺派作家都竭力突破一般小說的法則,不把情節結構、人物性格、典型環境等看作小說的要素,而注重人物的內心活動,尤其注重對人物潛意識的挖掘和表現。在這方面,他們有一些獨特的手段,其中比較重要的是:
(一)心理分析和內心獨白。二十年代現代派作家已經比較普遍運用心理分析和內心獨白的手法表現人物的心理狀態,挖掘人物潛在意識。新感覺派作家對此更加熱衷。劉吶鷗的《殘留》中女主人公霞玲希望丈夫的朋友陪她睡覺;對胖房東始而討厭,繼而討好;且想以身相許,滿足房東的情欲,以替代房租;還有在河邊接受外國人親吻,擁抱等等,都是通過內心獨白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通過潛意識活動,刻畫她害怕寂寞,追求刺激,滿足性欲的特殊心理。穆時英的《白金的女體塑像》也是以內心獨白的方法,表現一個未婚男醫生對女患者的性意識。施蟄存的《梅雨之夕》寫“我”在雨天的黃昏送一位偶然相遇的沒帶雨傘的少女回家,幾乎沒有具體情節,滿紙都是內心獨白。一路上“我”回憶,思考,疑慮,推測,各種心理交織在一起。瞻顧之間疑慮重重,真中雜幻,是夢還醒。在一層層迭進、往復回環的心理描寫中,傳遞了都市薄暮里一個蠢蠢欲動而又帶有強烈抑制的幻美。當然,心理分析和內心獨白,并不是新感覺派的獨創,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本來也是現實主義的手段之一,但只是到了現代派小說家手里,才被奉為圭皋,在作品中占據重要地位。
(二)多種感覺綜合運用。新感覺派是一個重感覺、輕理性的小說流派。他們非常重視通過寫“感覺”來反映人的內心世界。他們的作品常把多種感覺,如視覺、聽覺、觸覺等復合起來,因而常常出現所謂通感的現象。在穆世英的《第二戀》中,女主人公剛一露面,男主人公就感覺到“她的眸子里還遺留著乳香”。這就把“視覺”、“味覺”、“嗅覺”復合起來,反映出男主人公的愛慕心理。在新感覺派那里是五官不分的。他們的作品中,常有“我聽到光的聲響”,“我看到聲的光”,“我的舌頭大叫”,“我的鼻子看到”這樣的句子。上述“通感”,和這種“五官不分”相比,倒容易讓人接受,而且運用貼切處,確實能給作品增色加分。
(三)具體的感受和抽象的情愫相結合。新感覺派作家在寫人的內心時,總是努力把具體的感受和抽象的情愫結合起來。他們不是用具體的概念來范圍或鑄定那種細微、隱秘、莫可名狀的感情,而是用感受來固定,賦予它以具體的實感。讓特定的情愫、復雜的感情成為可以理解、可以設想,可以琢磨的具體感受。在《第二戀》中,兩位男女主人公分別幾年后又見面時,彼此訴說離情。當女主人公把手“按到我的頭上,撫摸我的頭發”時,男主人公“我”產生了這樣的感覺:“那只手像只熨斗,輕輕熨著我的結了皺紋的靈魂”。你看,“我”的心情不好,這是抽象的,但作家用“結了皺紋”就使之具體化了;抽象的所謂“靈魂”得到安慰,他具體地寫成用熨斗“輕輕地熨著”,這就讓抽象的情愫具有一種實感,可以體會,可以言傳。而且這樣的文字不但要比“我的靈魂得到了安慰”形象可感得多,也更有韻味和情趣。
(四)通過主觀反映客觀。新感覺派作家在描寫中非常注重主觀色彩,顯現人在特殊境況下的特殊心理或潛意識。在穆時英的《PIERROY》(傻瓜)中,主人公潘鶴齡所看到的“街”上有各種“眼”:“街有著都市風魔的眼:舞場的色情的眼,百貨公司的饕餮的眼,教堂的偽善的法眼,電影院的奸猾的三角眼,飯店的朦朧的睡眼……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輪里邊展示了都市的風土畫……”
作家本來要寫“都市的風土畫”,但他沒有一筆對街道做具體描寫,而是通過主人公感受到的各種“眼”的印象,來展現都市的“風魔”、“色情”、“欺詐”、“淫蕩”、“偽善”的本質特點。同時,這是主人公的主觀感受的“風土畫”,所以這“風土畫”也就反映著主人公的心理。他是一個一切都不如意的人:創作被誤解、戀愛遭背叛、神往革命被逮捕、鐘情母愛被褻瀆、堅貞不屈受懷疑。他對一切都不滿意,所以他所見的“眼”,也就帶著他那種特有的情緒。
二、文體——頭緒紛繁,節奏急促
新感覺派的小說多取材于大都市的人和事,反映大都市的繁雜和生活的快節奏。與此相適應,他們往往以多線并進手法結構作品,同時,使作品具有快節奏。穆時英的《夜總會里的五個人》采用多線條向一點聚攏的結構,可以看作是這方面的代表。小說一開頭就并列地把五個經歷、職業、性格不同,但又都是“有所失”——失業、失戀、失去青春、研究文學失去方向、投機失敗——的人聚集在一個夜總會里,接著讓他們在爵士樂、狐步舞的伴隨下,各自以獨特的方式尋求刺激,排遣寂寞。當第二天早晨他們不得不離開時,一個人開槍自殺,其余四人為他送葬。這地點的選擇,人物的設置,氣氛的渲染,都可以看作是舊上海那個都市的縮影。小說在紛繁的頭緒里,以急促的節奏不露痕跡地把人物的命運和都市的瘋狂聯系起來,他們在燈紅酒綠的場景里,在瘋狂的音樂和失態的舞步中,尋找命運的歸宿,進而反映出這個病態社會的不同側面。他的《上海的狐步舞》線索更凌亂,節奏更急促:有匪徒攔截的恐怖,有開槍斃賊的敏捷,有貨車、汽車奔馳的繁忙,有富豪家庭的墮落,有窮苦人的悲哀……作者把街頭、飯店、洋房、陋室、舞廳、賭場等眾多場面,眾多線條交疊在一起,形成一個眼花繚亂、光怪陸離的世界,展示人物半瘋狂的精神狀態。顯示出小說開頭和結尾的同一句話——“上海,造在地獄上面的天堂”——的真實。施蟄存的《薄暮的舞女》把素文厭倦了舞女生涯,想過正常的家庭生活,但又欲罷不能,最后不得不重操舊業的辛酸苦澀的復雜心情,通過她在一個傍晚與舞場經理、投機商、另一個舞伴的五次電話反映出來。在凌亂的心理展示中,呈現出她的厭倦、追求、無奈、失望的情緒。她在電話中盡量把語氣放得平緩,但處境的尷尬,又無法控制語速的迅疾。
三、語言——務新求洋
新感覺派的唯新是務,唯洋是求,在語言方面表現得更突出。劉吶鷗善于用紊亂的語言,寫出破碎的形象,反映光怪陸離的完整生活。他的小說《游戲》開始的一段寫“探戈宮”,在五彩燈下,光亮的酒杯、光滑的地板和桌椅之間,突出人的肢體、嘴唇和眼光,在恍惚雜亂中,使人產生頭暈目眩之感,表現“人心都在一種魔力的勢力下”變態的現實。穆時英更善于創造簇新的形式:使用百余字不帶標點符號的長句,又有為了強調人物心理活動而大量運用括號,甚至以字體不同型號來表示說話聲音的大小。至于特殊詞句的運用,如擔心情人的病,則說“怕她瘦了黑玉似的眼睛”;欣賞別人的舞姿,則覺得“華爾茲的旋律繞著她的腳……”這些,如以語法常規求之,則未必合適,但仔細品味,卻意味醇厚別致。《夜總會里的五個人》有這樣一段描寫——
“大晚報!”賣報的小孩張著藍嘴,嘴里有藍的牙齒和藍舌頭尖兒,他對面的那只藍霓虹燈的高跟鞋沖著他的嘴。
“大晚報!”忽然又有了紅的嘴,從嘴里伸出紅舌頭尖來,對面那只大酒瓶倒出葡萄酒來了。
紅的街,綠的街,紫的街,……強烈的色調化裝著的都市啊!霓虹燈跳躍著——五彩的光潮,變化著的光潮,沒有色的光潮——泛濫著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酒,有了煙,有了高跟鞋,也有了鐘……
這一段將賣《大晚報》的孩子的嘴和霓虹燈相交迭進行描寫的文字,把半殖民地都市的繁華和緊張躍動的氣氛立體式的寫了出來。這段文字多被評論家所贊賞,楊義說“他以直覺的、印象式的描寫,使都市之夜的聲、光、色、形雜亂交錯,相互映襯,組成一副巨大的以畸形都會的物質文明和廣告文明壓迫異化人的現代派彩畫,它既刺激人的神經,又激發人的想象,其技巧和表現力是值得稱贊的。”
此外,他們還廣泛地使用詩歌的跳躍,疊句的技巧,或造新詞新句,都給人一些新穎之感。像“他手里拿著一大堆物品,被百貨店的建筑的怪物吐出在大門口”,“電梯把他吐在四樓上”這樣的句子,就把畸形大都市的機械化使人變得被動、變得渺小表現得很別致。
我們粗略地梳理了新感覺派作家在藝術上提供的新因素,它那特定的心理分析方法和表現手段有許多不但是可取的,而且突破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局限,具有新穎的藝術效果和美學價值,在某種程度上對其他流派也有積極影響。我們在欽佩他們勇于吸收外來文化的氣魄、感佩他們在傳播西方文化中的貢獻的同時,也需指出,其中還存在一些傾向性的問題,如醉心表現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而且缺少批判;為演繹弗洛伊德學說而違背生活邏輯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從他們的成敗得失中,從這個流派不同作家的不同走向和發展,我們更進一步理解了魯迅所強調的“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去“占有,挑選”,要“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的借鑒和繼承原則,對今天和以后的創作仍有指導意義。
(中國中央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