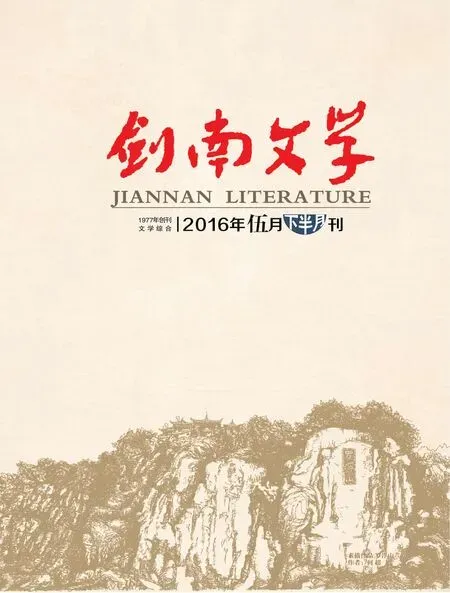圖形-背景視角下羌族情歌動詞連綴分析——以《賢妹住在山梁上》為例
□鄧 忠 張 茜
圖形-背景視角下羌族情歌動詞連綴分析——以《賢妹住在山梁上》為例
□鄧忠張茜
引言:本文運用圖形-背景理論對羌族情歌《賢妹住在山梁上》的動詞連綴現象進行認知分析,發現在具有敘事性的這類詩歌中,動詞連綴的運用是作品美學價值及文化內涵的得以體現的重要途徑,即動詞連綴在概念層面為作品的敘事構建了自洽的心理空間模型,圖形-背景的交替出現和適時逆反在該模型中表征了創作者完整的情感變化軌跡。以此為基礎,本文認為認知視角為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研究提供一條新思路。
一、羌族情歌研究現狀
總體而言,現有對于羌族情歌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對羌族情歌的發掘、收集、整理、漢譯和英譯階段。在周輝枝(1997)搜集整理編著的《羌族情歌精選》一書中收錄了89首羌族情歌,既有短歌也有較長的敘事詩,均為漢譯版本[1]。具體來看,當前的研究理路有如下特征:1)以這類作品出現的時代和文化背景為基礎,探討其文學和社會價值(楊梅 2015);2)以少數民族族群的產生和發展歷程為線索,討論其作為一個文化集體的情感、思想以及與社會背景的相互關系(王瑋立、鐘迪 2015);3)以一些特定的寫作技法、修辭手法、或語言風格為切入點,分析這樣的方式所產生的文學效果和詩學價值(陳玉堂2013);4)關注一些有代表性的羌族情歌作品,并進行鑒賞和評價(朱婷 2008)。
這些研究的共同點在于將詩歌本身置于更大的時空背景之下,涵蓋了人類學、文學、詩學、倫理學、社會學、美學等領域,體現出多學科、多維度的研究路徑。但局限性在于文學賞析多顯程式化,主觀化,印象化,缺乏思維性和創造性、缺乏對語言本體規律的細致考量、缺乏對敘事形成的文化效果的深入探究,致使羌族情歌獨特的文化魅力和強大的藝術感染力得不到更加深刻和廣泛地理解和接受。
二、認知詩學和圖形-背景理論
認知詩學的發展為上述的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全新的視角。這一概念由以色列學者Tsur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年提出,以認知語言學和認知心理學為基礎,是將認知科學和文學評論結合起來的全新文學解讀思路。認知詩學將文學活動視為人類普遍的認知活動和生活經驗的一種表征,認為對現實的感知是認知的基礎,認知又是語言的基礎,“現實-認知-語言”三者存在一個依次決定的序列關系(王寅2007)。換言之,通過研究人類的認知機制和語言機制能夠將文學閱讀和理解與日常生活體驗緊密聯系起來。“現實-認知-語言-文學”的發展過程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而認知詩學則是語言與文學效果之間聯系的橋梁,彌補了此前文學研究中對認知關注的不足,幫助讀者產生對文本內涵新的探究與思考[2]。對此,熊沐青(2011)指出:“認知詩學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不僅應該能夠解釋閱讀過程或閱讀機制,解釋特定文學效果,還應該解釋用別的分析方法不能解釋的文本涵義或美學涵義”[3]。
在認知詩學范式所使用的一系列研究方法中,圖形-背景理論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該理論于1915年由丹麥心理學家Rubin首次提出,其基本觀點是人們在進行某種觀察活動時,注意力往往會自然聚焦在某一個圖案上(figure),而將周圍的部分看作是該圖案的襯托和背景(ground)[4]。認知語言學繼承了這一看法,認為圖形-背景的分離也反映在語言結構上,如傳統的SVO結構就可被視為圖形背景二分化這一普遍認知原則在語言上的體現。具體地說,主語對應于圖形,賓語對應于背景,動詞表達則是圖形背景之間關系[5](Langacker,1990,1991)。以認知語言學為基礎,圖形-背景理論近來用于文學作品的賞析,幫助理解和感知作者想要營造的意境或氛圍。如王維的《山居秋暝》中寫道:“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句中主語“明月”、“清泉”作為動詞“照”、“流”的動作發出者從背景“松間”、“石上”中分離出來成為被凸顯的圖形。對于圖形背景的凸顯與虛化,使環境描寫變得細節化,構成一幅焦點突出,有動有靜,意境深遠的景觀圖,使讀者感受到山間的恬靜,自然的靈秀。
三、《賢妹住在山梁上》動詞連綴分析
盡管已經有了圖形-背景理論的零星嘗試,但學界尚未將這一理論進行深度發掘和廣泛使用。本文認為,這一理論的價值不僅僅在于解釋文學作品的意境,更在于提供一種對作品所涉及的事件和參與者的重新認知,并以此為基礎解釋作品動態推進中所體現的不同關注點和彼此關系,從而凸顯動態變化中作品的文學和美學涵義,如共鳴、感動、通感等。這在羌族民間情歌的研究中尤其有價值,因為這類作品大多具有敘事性,事件和參與者的關系常常處于變化中,不同的關系往往跟某種心理狀態直接相關。而體現這種敘事性的重要語言途徑就是動詞連綴,即在同一事件框架內若干動詞以較高頻次接續使用。這種方式在現代漢語中不很常見,但在羌族傳統情歌中則大量出現。下文將以《賢妹住在山梁上》的動詞連綴為例進行圖形-背景視角下的分析。
男唱:
賢妹住在山梁上,走到門前一道墻。
喂的狗兒像老虎,叫我咋個能到場。
女唱:
哥哥做事沒計才,回家燒個饃饃來。
狗兒咬你饃饃打,狗吃饃饃你就來。
如果把兩則唱詞看做一個完整的故事,那么在男方唱詞中,動詞的連續使用構建了整個情歌的基本事件框架。動詞“住”的施事是“賢妹”,“山梁上”受動詞的語義控制表征較遠及較高的距離(現實的和心理的),很顯然,這種距離感在該句中被前景化。動詞“走”除繼續體現距離感外,還勾勒出動態位移:由“山梁”到“門前”的“一道墻”,體現出事件場所由遠及近的推近。讀者視角由“山梁”拉近到“門前”,可見“哥哥”途徑山梁遠道而來,“走”這一動作被背景化,而位移本身被強化。來到門前卻被“一道墻”和“狗兒”阻攔,而這一場景成為了本詩的一個特寫鏡頭,再現了哥哥希望見到賢妹的嘗試此時竟然落空的場景,使得“哥哥”內心的失落、焦慮感在文本中得到自然而合理地實現。哥哥言賢妹“喂的狗兒像老虎”,是采用一種夸張的手法來表現自己難“到場”內心的失望與無奈,更加佐證了哥哥滿心歡喜落得一場空的心路歷程。此處,動詞依然處于被背景化的地位,但它們的存在使得“賢妹”、“上梁”、“狗兒”等參與者及其相互關系凸顯出來,奠定了故事的基本事件設定。簡單來講,男方唱詞是以動詞背景化為途徑呈現“我”所面臨的問題和亟須解決問題的焦慮感。
本詩的高潮是是女方唱詞,這中間的動詞連綴非常明顯,連用六個動詞“回”、“來”、“咬”、“打”、“吃”、“來”。妹妹讓哥哥先“回家”,燒個饃饃再“來”找妹妹,至于哥哥如何回家,如何燒饃饃,燒什么饃饃,哥哥的家在哪里,什么時間回家燒饃饃,都不是作者以及讀者所關注的重點,此處被凸顯的事件是哥哥得到了妹妹的指點。不難看出,這幾個動詞被前景化,而與該動詞在語義上勾連的其他“參與者”被弱化,這些動作才是妹妹所給出的建議的核心內容,至于表征“參與者”的語法上的賓語及狀語內容只是被浮光掠影般的提及;下一句的場景已是哥哥再次來到了妹妹門前,受到“狗兒”的阻攔,但是“狗兒”的動作被弱化,凸顯的是哥哥拿饃饃打狗兒的動作;末句狗兒吃饃饃時,哥哥已然來到妹妹家中,狗兒雖然在背景中存在著,但自始至終都處于相對次要的位置,在背景中心受到更多關注的則是哥哥的一系列動作。前一個動詞的含義被弱化,形成一種前景化效果,句末結果狀態動詞得到強化,使得句末動詞所展現的情景成為詩歌重要的特寫鏡頭。可見“賢妹”的善解人意,設身處地為哥哥著想,理解哥哥的難處;同時心中向往哥哥能來找她,內心十分焦急,所以她樂意為“哥哥”提出建議。賢妹對自己的心上人充滿理解與支持,表現出賢妹的耿直和質樸、對于愛情的真誠與勇敢,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動可愛。多個動詞的連綴因為有著清晰的圖形背景分離而顯得敘事完整、簡潔、詳略得當。
總的來說,這首情歌的動詞連綴有兩個重要作用:1)在男方唱詞中,動詞連綴體現基本事件元素,總體處于背景化地位,渲染距離感和焦慮感;2)在女方唱詞中,動詞連綴體現事件態勢的變化,總體處于前景化地位,凸顯問題的解決以及由此帶來的心理愉悅。把兩則唱詞結合起來,我們可以發現兩個事件線索:一是問題解決的過程,二是在這一問題解決過程中距離感和焦慮感的被克服,兩條線索都來自于動詞連綴所營造的物理和心理的動態過程。
四、結論
本文從認知詩學的角度出發,對圖形-背景理論進行了簡單的闡釋,并采用這種方法對羌族情歌《賢妹住在山梁上》進行解讀,通過對動詞連綴的分析,探討和再現了詩歌主人公的心理活動和與此相關的愛情感受。本文發現,這類羌族詩歌有時通過動詞的語義要求來設定事件參與者的性質、狀態和彼此關系,當這些元素被凸顯后,動詞本身的語義反而處在背景化狀態;這類作品有時則刻意突出動詞本身語義,而將其他參與者的諸多特點抑制,從而體現明顯的動態性和連貫性(這非常適宜于問題解決型語篇)。但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使用更多的個案進行分析從而發現羌族民間情歌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特征,這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來厘清。但本文要強調的是,認知詩學對于文學作品和文學活動有著強大的解釋力,對于少數民族傳統文學的研究和傳承具有積極的意義。
注釋:
[1].周輝枝,《羌族情歌精選》[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
[2].王寅,《認知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3].熊沐清,多樣與統一:認知詩學學科理論的難題與解答[J].外國語文,2011(1):33-38.
[4].Stockwell.P.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M].London:Routledge,2002.
[5].Langacker,R.W.Concept,image,and symbol: TheCognitiveBasisofGrammar[M].Berlin:the Cruyter,1990.
(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
本文系2016年西南民族大學學生創新項目羌族情歌敘事的認知研究(項目編號740109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