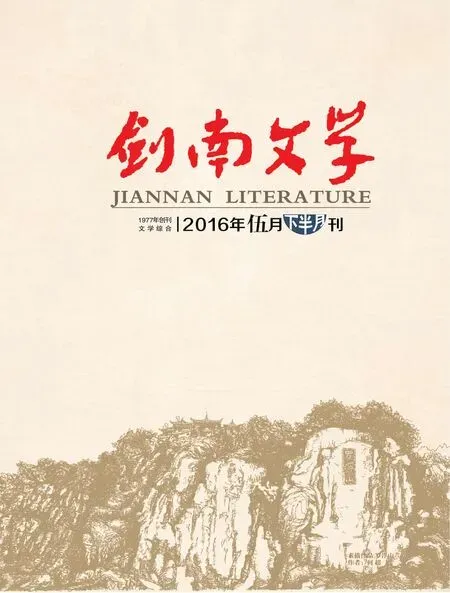從《三國(guó)演義》中塑造的方士形象談道教勢(shì)力對(duì)三國(guó)格局的影響
□尹伯鑫
?
從《三國(guó)演義》中塑造的方士形象談道教勢(shì)力對(duì)三國(guó)格局的影響
□尹伯鑫
《三國(guó)演義》是取材于史實(shí)又不乏虛構(gòu)色彩的演義小說,描述了漢魏之際群雄割據(jù)的壯闊場(chǎng)面,也著重描寫三國(guó)鼎立局面的形成,而天下最終歸于司馬氏的過程。其中,具有神秘色彩的方士形象是該作品創(chuàng)作的重要一部分,可以說道教的發(fā)展壯大間接影響了三國(guó)格局的形成。本文將主要分析《三國(guó)演義》中左慈、于吉和諸葛亮的方士形象,以及其他方士的出現(xiàn)對(duì)情節(jié)發(fā)展的作用,并通過他們的原型來探討道教勢(shì)力對(duì)三國(guó)時(shí)局的影響。
東漢末期,王室衰微,“十常侍”作亂,朝政日漸荒廢,“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漢室早已不是當(dāng)年興旺的漢室,證實(shí)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勢(shì)。當(dāng)時(shí),張角偶遇南華老仙,但見此人“碧眼童顏,手執(zhí)藜扙”,并以《太平要術(shù)》授予張角,讓張角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張角感慨自己三生有幸,隨即潛心鉆研,研究成符水咒法為人治病,自號(hào)“太平道人”。因張角的威望與日俱增,他的羽翼日漸豐滿,后來便借天下大亂的局勢(shì),率領(lǐng)徒眾造反起事。他走的是農(nóng)民起義的路子,以至于樹大招風(fēng),最終被曹操收編,順理成章,這組太平道黨人就成了曹操大軍的最初力量。由此可見,道教勢(shì)力曾被魏吸收,所以可以初步斷定,道教勢(shì)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塑造三國(guó)格局的。
一、被神化的方士在作品中的影響以及左慈的人物形象分析
首先,提及三國(guó)中被神化的方士,在《三國(guó)演義》中并不少見。比如:第十一回中南方火德星君化作一位美艷婦人請(qǐng)求與糜竺一同坐車,糜竺一路不曾窺視婦人一眼,火德星君佩服之心油然而生,因糜竺以禮相待,便把他奉旨往燒糜竺家的事告訴了他,讓他早做準(zhǔn)備。糜竺經(jīng)歷此事以后便扶貧濟(jì)困,后來被陶謙請(qǐng)去做了別駕從事,為人正直淳樸又不失韜略,這一系列事件的發(fā)生也為陶謙三讓徐州,將糜竺舉薦給劉備做了鋪墊。再如第六十二回,西川劉璋下令讓劉璝、張任、泠苞、鄧賢四人趕往雒城嚴(yán)加守備,在途經(jīng)錦屏山之時(shí),四人遇紫虛上人并且詢問此戰(zhàn)吉兇,紫虛上人預(yù)測(cè)了龐統(tǒng)之死,又透露四人定數(shù)難逃。諸如此類的方士還有大戲曹操的左慈,被曹操所傷的梨樹之神,預(yù)測(cè)劉備身死白帝城的李意,和指引諸葛亮平蠻的馬援廟的廟神。
這些方士在作者筆下被塑造得神乎其神,并不是毫無意義的。眾所周知,《三國(guó)演義》七分史實(shí),三分虛構(gòu)。羅貫中在三分虛構(gòu)中采用了包含方士神卜能力的“讖緯現(xiàn)象”,表達(dá)了民族集體的心理沉淀,體現(xiàn)的是集體忠于天命觀的意識(shí)和根植于種族記憶和人類歷史的經(jīng)驗(yàn)。在民間起義或是統(tǒng)治者樹立威信的過程中,他們通常會(huì)運(yùn)用讖緯來獲取人民的信任和敬畏。不得不承認(rèn),讖緯是一種有效把握世人忠誠(chéng)的有力工具。所以,即使是《三國(guó)演義》中虛構(gòu)的部分,也往往會(huì)使讀者感到撲朔迷離,真假難辨。
《三國(guó)演義》中被描寫得最精彩,最讓人難以置信的方士就是在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回出場(chǎng)的左慈。他可以不傷及柑子外殼而取其果肉,被曹操拷打卻齁齁熟睡毫無痛楚,“數(shù)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千羊亦能盡”,宴會(huì)上大顯神通被曹操視為妖人。曹操捉他,他竟走入羊群消失得不見蹤影,而后卻操控起了羊群,將死羊復(fù)活,他還可以幻化成諸多左慈追打曹操,最后聚成一真身駕鶴而去。
二、曹魏與江東地區(qū)對(duì)道教勢(shì)力的吸收以及于吉的人物形象分析
提到龐大的道教勢(shì)力,首先會(huì)想到張角的黃巾軍,聲勢(shì)浩大,勢(shì)力遍布豫、徐、幽、青、揚(yáng)、荊、冀、兗八州,幾乎占了全國(guó)的四分之三,此次起義是中國(guó)歷史上與宗教形式相結(jié)合的最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起義,同時(shí)也拉開了三國(guó)時(shí)代的序幕,為曹操的軍隊(duì)注入了一股新鮮血液。除此之外,最早的道教派別,東漢時(shí)期的符箓派發(fā)展到三國(guó)時(shí)期,也扮演了曹操一部分的勢(shì)力。據(jù)《后漢書·劉焉傳》記載:“順帝時(shí),張陵客居于蜀,學(xué)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五斗米,也稱“五斗米道”。后來,張陵把天師之位傳給張衡,張衡再傳給張魯。相比張角的“太平道”,張魯?shù)摹拔宥访椎馈币獪睾驮S多,沒有發(fā)動(dòng)起義,而是運(yùn)用了“政教合一”的手段,建立一方政權(quán)起。曹操也曾經(jīng)襲擊過張魯?shù)恼?quán),但是張魯實(shí)力沒有曹操?gòu)?qiáng)大,所以他沒有過多的掙扎,很快便向曹操投降了。這樣一來,曹操的勢(shì)力又?jǐn)U大了許多,以至于“挾天子以令諸侯”。
曹操之所以能收編黃巾軍和五斗米道,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自己就信奉以方術(shù)養(yǎng)氣的黃老道,并且知其道而用之。陳華昌曾經(jīng)將曹操與皇甫嵩等人對(duì)黃巾軍處置的做法進(jìn)行了比較,他發(fā)現(xiàn)曹操并不似皇甫嵩那樣對(duì)黃巾軍痛恨至極,手段殘酷,而是懂得安撫這一股勢(shì)力,將他們籠絡(luò)到自己旗下。而與曹操做法截然相反的人,要屬在江東起家的孫策。故事發(fā)生在《三國(guó)演義》第二十九回,孫策不顧所有人的勸阻,大發(fā)雷霆,將江東一帶影響力甚遠(yuǎn)的方士于吉斬首。
于吉,瑯琊宮方士,“身披鶴氅,手?jǐn)y藜扙”。相傳他在吳郡、會(huì)稽一帶潛心修煉,造福于人,曾得神書于曲陽泉上,號(hào)曰《太平青領(lǐng)道》。第二十九回對(duì)孫策怒斬于吉的整個(gè)事件做了詳細(xì)的描述。孫策設(shè)宴款待袁紹使節(jié)陳震時(shí),正欣喜于與袁紹結(jié)為外應(yīng)共同攻打曹操,卻不曾預(yù)料于吉來到。眾臣見于吉皆起而拜之。孫策見狀大怒道:“是何妖人?快與我禽來,違者斬”。于吉為活命而仔細(xì)辯解,然而孫策更加憤怒不堪。他說:“汝即黃巾張角之流。今若不誅,必為后患。”并叱左右護(hù)衛(wèi)速將此妖人斬首。雖然謀士張昭替于吉辯解,“在江東數(shù)十年,并無過犯,不可殺害”,也有陳震和眾將領(lǐng)的苦諫,可是孫策毫不動(dòng)搖。孫策母親怕他惹怒神仙,然而孫策依舊毫不動(dòng)搖,鐵了心腸要?dú)⑺烙诩.?dāng)孫策看到獄卒也“皆敬信于吉”的時(shí)候,他勃然大怒,對(duì)眾人皆崇信于吉的情景感到十分憂慮和憤怒,他甚至對(duì)于吉的影響力感到恐懼。最終喚來武士,將于吉一刀斬首。
三、元代道教對(duì)《三國(guó)演義》的影響以及諸葛亮的人物形象分析
《三國(guó)演義》是根據(jù)三國(guó)史書和民間傳說創(chuàng)作的演義小說,成書于元末明初。而且元朝正是道教發(fā)展的鼎盛時(shí)期。首先,元太祖十四年,全真道掌門丘處機(jī)接受成吉思汗的邀請(qǐng),以七十余歲高齡,不辭萬里跋涉,越過艱難險(xiǎn)阻,率領(lǐng)弟子十余人,赴西域雪山面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感嘆丘處機(jī)的不凡,并尊其為“神仙”。后丘處機(jī)東歸,他的全真道影響力與日俱增,已經(jīng)深入到民間。
其次,羅貫中的老師趙寶峰這個(gè)人,雖然身處山林,卻時(shí)常憂國(guó)憂民。并告誡他的弟子慈溪縣令陳文昭要“以治民事宜”為首要任務(wù),這與羅貫中在《三國(guó)演義》中歌頌的桃園結(jié)義和上報(bào)國(guó)家,下安黎民的思想一致。
再次,《三國(guó)演義》所寫東漢末年的朝局動(dòng)蕩,人民處于水深火熱的現(xiàn)實(shí),與金元之際的社會(huì)背景極其相似。而且,東漢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奉行的“周窮濟(jì)困、濟(jì)民救災(zāi)、治病勸善”教義,與全真道的教義“濟(jì)貧拔苦、先人后己、與物無私”類似。這兩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背景和宗教信仰都具有極大的相似性,更容易使羅貫中產(chǎn)生思想上的共鳴,所以他的情感更傾向于蜀國(guó)劉備仁慈的一方。
所以《三國(guó)演義》的創(chuàng)作勢(shì)必受到道教的影響。
談及諸葛亮,人人都會(huì)心生敬佩,作者將其塑造為羽扇綸巾的道教軍師形象,以極其傳神的筆法刻畫了他的神機(jī)妙算。諸葛亮既擅長(zhǎng)陰陽八卦,又具有未卜先知和知人善任的本領(lǐng),并在一次次軍事斗爭(zhēng)和外交雄辯中運(yùn)籌帷幄。在“七星壇諸葛祭風(fēng)”一回中,他自稱“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fēng)喚雨。”為了助周瑜破曹,在本無東風(fēng)的隆冬之際,他請(qǐng)求周瑜為他建造“七星壇”,他登壇為周瑜借來了三天三夜的東南大風(fēng),使得赤壁之戰(zhàn)中的東吳一方反敗為勝,從而正式確立了三國(guó)鼎立的局面。到“五丈原諸葛禳星”一回,向來相信“天數(shù)”的諸葛亮自知命不久矣,竟設(shè)法使用“祈禳之法”來延遲壽命,可見他能力超乎尋常。可以說有諸葛亮的情節(jié)是《三國(guó)演義》最精彩的部分,這位偉大的道教軍師,為蜀國(guó)鼎立一方做了最為巨大的貢獻(xiàn)。
民間曾流傳這樣一段話來形容諸葛亮一生的功績(jī):
“收二川,排八陣,六出七擒,五丈原前,點(diǎn)四十九盞明燈,一心只為酬三顧。取西蜀,定南蠻,東和北拒,中軍帳里,變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六出”是指六次出征祁山,討伐曹魏;“七擒”是指七次擒拿孟獲,平定南蠻。“東和”是指東與孫權(quán)和好,“北拒”是指北與曹操相抗。“火攻”是指火燒赤壁,“收二川”指收復(fù)西川和東川,指西川劉璋和東川張魯。“點(diǎn)明燈”是他北伐時(shí)感到自己命不久矣,在五丈原禳星續(xù)命。“排八陣”是指巧設(shè)八陣圖,阻擋了東吳陸遜的追兵讓劉備得以脫險(xiǎn)。
作品中的諸葛亮運(yùn)用了神秘莫測(cè),詭譎多變的方術(shù),以及他超乎尋常的智慧,立下了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戰(zhàn)績(jī)。
四、《三國(guó)演義》對(duì)道教的肯定
在整部作品中,方士的形象都如同仙人一般,他們都是善意的,有思想的。如:曾為汜水關(guān)鎮(zhèn)國(guó)寺長(zhǎng)老,后于玉泉山結(jié)草為庵,坐禪參道,點(diǎn)化關(guān)羽英靈的普凈;還有“松形鶴骨,器宇不凡”,曾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的水鏡先生;再如“竹冠草履,白袍皂絳”,助孔明平蠻的孟節(jié),以及幫助陸遜破解八陣圖的黃承彥。他們?nèi)缤瑸樘煜掠⑿埸c(diǎn)亮的一盞盞溫暖的明燈,指引著眾人前行。
綜上所述,《三國(guó)演義》中方士的存在為作品增添了趣味性和可讀性。方士善于占卜、遵循天命的特點(diǎn)給其自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也表達(dá)了作者及世人對(duì)道教的敬畏和好奇,以及對(duì)道教方士的肯定。同時(sh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道教在三國(guó)時(shí)期并沒有因黃巾軍起義失敗而銷聲匿跡,相反,吳、魏、蜀三國(guó)均有道教勢(shì)力的影響,只不過影響的廣度有所不同。曹魏對(duì)太平道加以限制又融合五斗米道;吳國(guó)由于得到統(tǒng)治者的推崇而得以公開傳播;巴蜀地區(qū)道教的影響則相對(duì)較少。三國(guó)時(shí)期雄霸各方的政權(quán)對(duì)道教都實(shí)施了懷柔的政策,才使得道教得以發(fā)展到今日,成為中國(guó)最具本土特色的宗教系統(tǒng)。
(黑龍江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