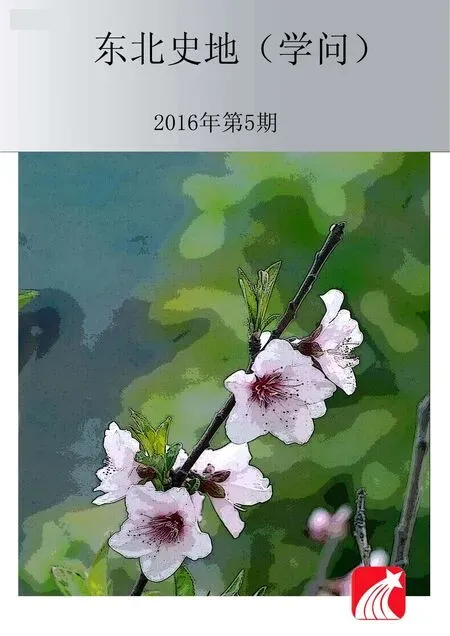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民族學研究評述
黃彥震 任宏偉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民族學研究評述
黃彥震 任宏偉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民族學經歷了一些困難,同時也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雖然學科團隊建設和個人培訓以及經費不足是阻礙俄羅斯民族學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但俄羅斯民族學研究依然取得了驕人成績,而“轉型”和“創新”始終貫穿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民族學學科發展的全過程。
俄羅斯 民族學 歷史發展
任何學科的發展都經歷過錯綜復雜且變幻不定的發展過程。社會科學中民族學也不例外,由于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需求不同,民族學在不同時期的研究主題、研究范圍及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差異。這種持續變化的過程就使得學科歷史更加豐富多樣。本文以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民族學的發展為研究對象,同時結合俄羅斯民族學發展歷史來分析其熱點問題,展示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民族學的發展概貌。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繼承了蘇聯時期留下的豐富遺產,包括科學、文化、教育、豐富的物質基礎以及精神財富,①這為俄羅斯新時期的民族學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俄羅斯此一時期的民族學理論知識以及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都已應用于實踐,所以此時期民族學的社會地位與蘇聯時期相比得到了極大提升,對社會的影響也日益加深。
關于俄羅斯民族學的研究成果很多,本文側重于俄羅斯民族學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缺陷及研究主題的改變。本文采用客體描述和概要分析方法分析整個俄羅斯民族學組織系統,②一方面能全面展示俄羅斯民族學的發展歷程,另一方面也希望俄羅斯民族學的研究成果能對我國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鑒。
一、研究內容
(一)俄羅斯民族學的歷史發展概況
根據俄羅斯科學家Pi May Andrianof提出的“民族學基礎”概念,可以把俄羅斯民族學的歷史發展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③。階段劃分及特點見表一:

表一:俄羅斯民族學發展階段劃分及特點
(1)萌芽階段:俄羅斯18世紀后開始出現具有現代民族學特征的文獻。雖然到了19世紀,已經累積相當數量關于民族文化與民族生活的文獻資料,但是民族學在俄羅斯還未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體系。④
(2)形成階段:19世紀前半葉,俄羅斯良好的國內政治環境,促進了民族學成為獨立學科的進程。19世紀40年代,一些民族學組織先后成立,其中俄羅斯皇家地理學會于1845年在圣彼得堡宣布成立,⑤這成為俄羅斯官方組建民族學學科的標志。20世紀前的俄羅斯民族學不重視田野調查,很大程度上都是“搖籃里的民族學”,導致其在民族理論與研究方法上與同時期的西方國家具有較大差距。
(3)發展階段:20世紀20年代,蘇聯民族學在理論,組織機構,人才培訓等方面都取得矚目成就。多元化觀點深入各研究領域,首先就體現在研究方法上,這時期進化論方法論占主導地位。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不僅民族學研究機構銳減,民族學研究范圍和教育教學機構同樣漸趨萎縮。⑥直到蘇聯衛國戰爭前夕,民族學研究系統才又慢慢恢復運轉。但是在衛國戰爭期間,民族學研究機構再次解體,解體后的機構轉移到阿什喀巴德(Ashkhabad)以及一些東部區域。
(4)理論發展階段:衛國戰爭后,民族理論開始在蘇聯社會中扮演積極角色。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為世界民族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最具代表性的要數托卡列夫(Tokarev)。20世紀七八十年代,形成了一系列影響重大的組織團體,其中有公立的,也有自發形成的。
(二)俄羅斯民族學“危機”與主體意識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繼承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20世紀90年代早期,整個俄羅斯社會都處于巨大變革之中,當然也包括俄羅斯民族學。社會的重大變革為民族學的發展提供了積極條件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負面影響。俄羅斯經濟生活陷入嚴重危機,民族學此時也處于發展的十字路口。⑦瓦列里·季什科夫(Valery Tishkov)在1992年寫道:“‘民族學危機’,這不但使我們研究的社會背景發生改變,而且民族學本身也因蘇聯解體而發生變化。不只是民族學,還包括人類學和民族學學會以及俄羅斯科學院的研究。”
瓦列里·季什科夫(Valery Tishkov)認為整個社會領域和科學領域都在經歷一次危機,而民族學危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瓦列里·季什科夫Valery Tishkov)認為,民族學學科地位、社會地位、物質保障都與社會需求極不協調,學科系統的不完善和學科發展模式的殘酷嚴重打擊研究者的創造力。更嚴重的是整個社會對研究成果并不買賬,這就導致研究者失去創造熱情。瓦列里·季什科夫(Valery Tishkov目睹了民族學從一個“健康有機體”轉變為“滿目瘡痍”的全過程。然而在所有危機中,最嚴重的莫過于缺乏民族學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剖析。
瓦列里·季什科夫(Valery Tishkov)的文章發表后,引起了關于民族學“危機”本質、學科發展狀況和未來發展趨勢的大討論。許多學者利用“民族學反思”平臺積極參與大討論并解釋各自觀點,詳見表二:

表二:民族學學者對“危機”的觀點
(三)史祿國(Shirokogoroff)的學術思想
史祿國(Shirokogoroff)是一位富有天賦的學者。他在民族學研究中融入了數學、醫學、生物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知識。他認為西方民族學中的進化論學派和文化圈都各有其合理部分,但也有缺陷。史祿國(Shirokogoroff)持民族學是一門專門研究人類科學的學術觀點,包含人類生存生活的一切領域,并且在國家以及文化元素之間并沒有明顯的界限。
史祿國(Shirokogoroff)在中國逗留時期提出研究民族群體的重要性。他用эTHOC來表示“民族”,盡管這一術語出現在19世界中期的俄語中,但史祿國(Shirokogoroff)卻是第一個使用эTHOC(Ethons)一詞在民族學學科分類之中。他還使用了一個核心概念——“民族平衡”(зТНИЧескоераВНОВИе)。民族平衡與否受民族群體數,民族群體居住區域以及民族群體與自然環境的適應程度決定。
費孝通先生對史祿國(Shirokogoroff)的學術觀點有過如下總結:“他的Ethons論最精彩的分析是可以用算術公式來表示的一個可視作Ethons單位,即民族認同的群體,在和同類單位接觸中所表現出各自的能量。所以在他的理論最后一句話是“Ethons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人類學研究就是研究Ethons的變化過程,用我們的話說就是民族的興衰消長,是一個動態的研究。”通過一些學者努力,史祿國(Shirokogoroff)在國外出版的書目和文章得以翻譯成俄語版本,他的學術觀點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甚至有學者認為史祿國(Shirokogoroff)才是俄羅斯民族理論的真正開創者。
(四)列·尼·吉米列夫(L.N.Gumilyov)的民族理論及其社會影響
1.一些未知的能量在地球特定的區域出現,可以激發當地居民的熱情去研究這些能量,這就使得在任何一個地區生活的群體都有“獨特的心理狀態”。
2.國家由人口組成,不但是一個生物性集合體,而且是自然存在。通過研究社會發展法則來研究國家現象極其荒謬。在民族群體生活中,“熱情”始終扮演特殊角色。“熱情”是個讓人覺得驚奇,而且可以幫助民族群體從生活環境中汲取所需能量。吉米列夫把國民劃分為兩種類型。分別是“激情澎湃型”和“無精打采型”。
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Gumikei在《國家地理》雜志發表的文章引起了廣泛關注。20世紀80年代末期,民族學理論的社會影響逐漸得到加強,吉米列夫也因此從一個學科“邊緣者”成為“學術大師”。他的影響即便在20世紀90年代后同樣不可動搖。阿爾泰共和國還因此在2002年把一座山命名為吉米列夫山。在社會領域和學術領域,列·尼·吉米列夫的民族起源及民族理論的影響不可忽視。
二、21世紀以來的俄羅斯民族學
(一)新方向的開辟
20世紀90年代后,俄羅斯民族學為了滿足社會需要,在傳統研究方法上基礎上發展出新的方法論。例如宗教研究,移民研究,性別問題,都市人類學,法學人類學,醫學人類學,動物行為科學,文化人類學,政治人類學,視覺人類學,以及民族沖突和民族關系的研究。俄羅斯民族學的研究主題成為民族學重要的研究方向。俄羅斯民族學研究了俄羅斯的歷史、文化、領土變化、正統歷史及功能、海外俄羅斯人的身份地位及俄羅斯移民史。
(二)俄羅斯民族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困難
1.科研創新不足
雖然有大量的科研成果陸續發表,但是研究質量卻表現出下降的趨勢,表現在很多文章缺乏現實意義且研究主題重復,不僅浪費了人力物力,還影響了學者的工作熱情。
2.人才培養不足和學科隊伍建設不夠
有的學者用“老態龍鐘”形容俄羅斯民族學研究團隊。近些年,年輕學者非常稀缺。很多中年學者鑒于經濟或者其他因素考慮因素,要么選擇到國外大學工作,要么選擇直接進入工廠。有很多客觀原因造成研究隊伍的“老態龍鐘”,其中民族學社會地位不高而且得到的報酬很低是主要原因。
3.科研資金短缺
俄羅斯民族學發展過程中,很多科研項目都需要資金支持。然而實際情況是,科研基金不足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問題。除了依賴國家的財政預算外,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組織也從多渠道支持科研項目的基金需求。但就當前情況看,科研基金申請制度還不完善,和國家中心研究機構相比,一些地方性的研究機構只能申請到少量資金支持,因而那些地方民族學的發展就受到嚴重阻礙。
4.俄羅斯民族學很難實現國際化
從20世紀90年代起,俄羅斯民族學被認為是國際民族學和人類學的一部分,要想取得更多發展,就必須縮小與國際學術圈的差距。在與世界研究團隊合作交流過程中,語言不通和基金不足成為最大阻礙,僅有少數學者能閱讀外文文獻,對國外研究動態也知之甚少。在美國舉行的兩次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名單上都沒有俄羅斯學者的名字便是一個佐證。只有少部分學者意識到與西方學術圈子接軌的重要性。于是他們就成為西方學術思想的“翻譯者”和“傳達者”。但是由于西方民族學學術觀點更新較快,許多傳播到俄羅斯的西方的學術思想都有所“延遲”。
5.缺乏群體“統一性”意識和“身份認同”
俄羅斯民族學在20多年的發展中,學者對俄羅斯民族學是否形成了一個穩定統一的學術群體還存在爭議。一些學者認為俄羅斯形成了穩固統一的群體,因為民族學學科很早就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學科,而且還有大量的民族學研究者客觀存在的。然而,另一些學者卻認為,不管是從組織團體還是精神層面來說都還不存在真正的團體。有的只是一些散亂的研究隊伍和學術內訌。
季什科夫(Tishkov)說:“民族學研究團體存在與否對我個人來說毫無意義。我想從事的是投入自身精力來鞏固和發展已有的學科隊伍,讓其成為名副其實的民族學研究團體,而我們,就是團體中的一員。否則,我們該為何人?”
許多學者為此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議。有學者希望像俄羅斯民族學學術期刊一樣,民族學反思應具備在學術團體建立過程中更重要的角色。另外,學者非常希望建立一個統一的研究網站與全國學者資源共享,在網站上刊發最新的論文,文章,田野筆記等。相信這些建議未來將有助于俄羅斯民族學朝一體化發展,并在發展中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
三、結論
綜上所述,可見盡管俄羅斯民族學在蘇聯解體后發展過程中還面臨諸多問題,但是也逐漸擺脫“危機”,并且還取得了一些小成就。但也應承認,民族學學科依舊面臨諸多困境。其中,學科團隊建設缺乏和人才培養不足是主要問題。要想解決這些問題,首先需要民族學科研機構的相互協作,在深化課程改革和教育系統改革的同時,進行人才培養模式和訓練機制的改變。縱覽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民族學20多年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雖然遇到了不少的阻礙與挑戰,但俄羅斯還是取得了一些驕人成績。其中,“轉型”和“創新”始終貫穿于俄羅斯民族學學科發展的全過程。
責任編輯:祝立業
K511.2
A
1009-5241(2016)05-0074-04
黃彥震 陜西學前師范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系講師 陜西 西安 710100任宏偉 貴州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碩士生 貴州 貴陽 550025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4YJC85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