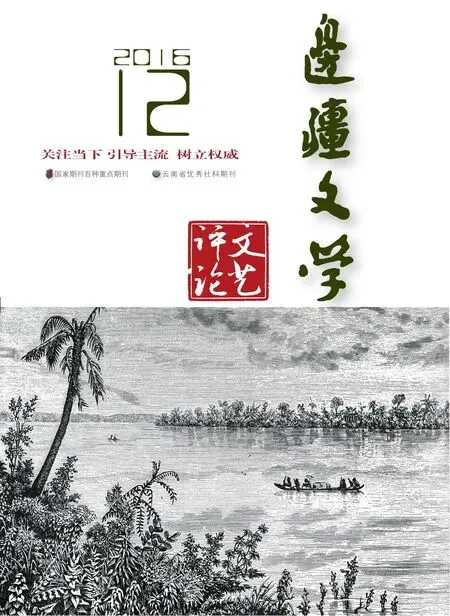寂寞與詩
——論鄭敏詩歌的生命詩學
◎李 琳
寂寞與詩
——論鄭敏詩歌的生命詩學
◎李 琳
學人觀點
主持人語:這一期的“學人欄目”刊發兩篇論文。焦印亭教授關注錢鍾書的宋詩研究,從宏觀整體、重大問題、名家評論三個方面深入闡析了錢鍾書關于宋詩研究的基本看法和詩學評價。讀此文,有關宋詩的基本詩學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李琳的論文是對現當代著名詩人鄭敏的生命詩學的解讀。論者抓住了“寂寞”這個關鍵意象,具體而細致地論述了詩人賦予“寂寞”的審美意義與文化價值。這篇論文為我們深入理解鄭敏提供了一條可靠的路徑。(胡彥)
九葉詩派,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曾被遺忘冷落的詩歌流派,直到1981年《九葉集》的問世,這個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詩歌流派才得以重回大眾視野。談到九葉詩派,不得不提鄭敏,鄭敏不僅是九葉詩派中為數不多的女詩人,還是九葉詩派中創作生涯最長的詩人。鄭敏詩歌哲思深邃幽遠,想象奇妙跳躍,以哲學比鄰而居的詩美在九葉詩派獨樹一幟。鄭敏的創作是典型的知識分子沉思式的寫作。在喧鬧的現實中,鄭敏始終是內斂靜謐的,從詩歌開啟的天地之境中尋找生命的詩意。正如蔣登科在《九葉詩人論稿》中提到的:“作為一個以思想文化建設為己任的知識分子,與其站在戰火邊緣空喊口號,還不如真正地進行一些生命思考。九葉詩人在自我定位上的準確是現代新詩史上較為獨特的情形,也是較為適合知識分子本性的選擇。”[1]知識分子本性的選擇,注定詩歌之途是寂寞的,在浮躁喧嘩中保持寂寞的堅守,對世事有冷靜的觀察,保持獨立的信仰,在寧靜中走向精神的皈依。“庸人為物欲所驅,永無心靈的寧靜。惟有克服這種躁動后才能消除異化,回歸與天地一心的寧靜心態。”[2]與天地一心的寧靜心態,一直是鄭敏詩歌自覺的詩學追求,也是鄭敏作為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價值選擇。當鄭敏把自己的第一首詩作給老師馮至看時,馮至對鄭敏說:“這是一條非常寂寞的路。”[3]無論是童年還是寫作,寂寞者的姿態始終伴隨著鄭敏。
海德格爾曾經說過,“每一首詩作都是出于這首獨一之詩的整體來說話的,并且每每都道說著這首獨一之詩。從這首獨一之詩的位置那里涌出一股泉流,它總是推動著詩意的道說。”[4]如果鄭敏詩歌的獨一之詩也是不能道破的,那么獨一之詩的位置應該是寂寞。寂寞,是鄭敏作為傳統知識分子的選擇,寂寞不是凝滯的,而是如雕塑一般,寧靜中流動著生命的思索。從鄭敏的詩歌出發,寂寞洞照著鄭敏的詩歌,寂
寞召喚著思與詩的對話,在寂寞中我們受到無意識深淵的召喚,挖掘無意識深處的生命力,自由出入于無意識與意識的混沌之間,重新體悟生存的本質,從詩歌的語言中找尋可能的源頭。
一、寂寞的生發與成熟
鄭敏的《寂寞》發表于1943年,在詩歌的開篇,詩人這樣寫道:“這是一顆矮小的棕櫚樹,他是成年的都站在∕這兒,我的門前嗎?我仿佛自一場鬧宴上回來。當黃昏的天光/照著他獨個站在/泥地和青苔的綠光里。”寂寞不是閨怨的私情,不是一己之私的沉寂,而是以天地萬物為背景的寂寞,棕櫚樹、天光、泥地、青苔等自然之物都同樣感受著寂寞,從鬧宴回來,是從現實中歸來,作為詩人,既參與生活,又能從浮躁的生活中抽身而去,保持寧靜獨立的思考。在這里詩人擺脫了流俗觀念中的寂寞,用寂寞的沉思開啟了天地人的對話。
詩人繼續道:“我是寂寞的。當白日將沒于黑暗,我坐在屋門口,在屋外的半天上,這是飛翔著那/在消滅著的笑聲,在遠處有/河邊的散步,和看見了:那啄著水的胸膛的燕子,剛剛覆著河水的/早春的大樹。”在這里,詩人感受到了寂寞的痛苦,飛翔的笑聲、河邊的散步、啄水的燕子,覆著河水的大樹各自找到了情感上的依賴,而詩人情感上無所依戀,她是寂寞的,想排遣寂寞。
什么是寂寞的排遣?通常意義上是情感的依賴與救贖,我們都是孤獨的漂泊者,在生命的征途中尋找情感的完整與成熟,用互相依附的情感排遣心靈的寂寞。然而,詩人給了我們相反的回應:“我想起海里有兩塊巖石,有人說它們是不寂寞的;同曬著太陽,同激起白沫,同守著海上的寂靜,但是對于我它們∕只不過是種在庭院里/不能行走的兩棵大樹。”身體與情感的相伴扶持依舊無法排遣靈魂上的寂寞,縱使相依相伴、生死相隨,依舊各自活在自己的生命里,寂寞沒有在情感中消隱,而在情感的召喚中陷入幽遠的深淵。中國傳統詩詞講究的是物我合一的學問,而在這里巖石、大樹卻無法與自我心靈相契合,對自我而言,依然是他物。這是鄭敏的徘徊與矛盾,也是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寫照,無法從困頓的現實中得到傳統的慰藉,在自我與他物無法合一中走向孤寂的人生旅途。
鄭敏在詩歌的最后,這樣感嘆道:“我把人類一切渺小,可笑,猥瑣的情緒都拋入他的無邊里,然后看見:生命原來是一條滾滾的河流。”從寂寞開啟的沉思,最終以生命的無限可能結束。老子《道德經》開篇這樣寫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5]詩歌的道說正如道的境界一樣,是不可言說的存在。海德格爾也認為所謂藝術作品開啟了一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就在真理中。詩歌的真理正如涓涓細流蘊含在詩歌之中,寂寞,是孤絕的生命狀態,是難以排遣的生命之苦,在寂寞的道說中我們進入寂寞的自然之境、心靈之域,于寂寞中開啟澄明世界的某種可能。
詩人的寂寞在詩歌與人生的沉淀中走向更廣闊的天地,發表于1989年的《成熟的寂寞》可以說是對早期詩作《寂寞》的互文與回應。輟筆三十年的鄭敏在1984年重新開始寫詩,三十年的歲月變遷與人世浮沉,對于一位敏感的詩人會形成怎樣的情感波瀾是無法預見的,我們試圖在《成熟的寂寞》中尋找詩人的寂寞之旅。“秋天成熟的果實,寂寞”,我們不能忽視一個標點符號對于詩歌的意義,在生命的成熟與豐潤而獲得心靈的短暫滿足后,依然無法消解寂寞,寂寞的生長甚至與生命的生死無關,寂寞甚至超越了歲月的游戲,吞沒的是生者與逝者,“只有寂寞是存在著的不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真正存在”。成熟的寂寞,不在之在,老子《道德經》第五章中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6]成熟寂寞與天地一樣,在歲月的風塵中保持著靜觀無私的姿態,穿越生死,無所不在,又無法捕捉。寂寞已經成為生命自然而然的狀態,不歷經寂寞無法通透生命,“過去,由于無端地為寂寞而惆悵,無法直面生命本身的豐富、復雜和強烈;而現在,詩人翻開了那寂寞的巨石——猛省了對寂寞的傳統看法,于是,對生命有了新的領悟”[7]。詩歌的最后,“我在口袋里揣著/成熟的寂寞/走向世界,一個托缽僧。”一個托缽僧,“托”這個動作意味著向上的索求,是物的索取;而缽是一種信仰的承載,是念的寄托;托缽僧的形象可以說是詩人理想的化身,在浮躁的人世中,詩人是要有所承擔的,承擔著對生命真與純的追求,對寂寞信仰的堅守,詩人的責任是指向世界和
人類的命運,在詩歌征途中體悟寂寞,開啟寂寞,在寂寞的征途中尋找人類的詩意棲息。
二、生死辨忘的寂寞
生與死都是人類生存中無法回避的體驗,在寂寞生命旅程中,人類的生存都無法回避生死的孤寂與恐懼。生與死是人類生存所面臨的根本矛盾,人類的悲歡離合被生死所耽,為生死所困,成為生命的常態。在鄭敏的詩中,生死的辨與忘是鄭敏詩歌重要的思想內涵與生命哲學。
陶淵明的《飲酒》:“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辨與忘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的思想追求與審美傳統,這一傳統在中國現代詩歌中也得到了傳承。李怡在《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中這樣寫道:“由于受到了來自古典詩歌傳統、漢語言自身穩定性及與之相關的基本哲學思維的影響,中國現代新詩的文法特征顯著地表現為“辨”與“忘”這兩重因素的循環往復。”[8]辨與忘是兩種不同的文學思維,辨是詩人智性的判斷,忘是詩人神性的放逐。在中國的詩歌發展中,辨與忘循環往復,互為增補。
在中國詩歌辨忘傳統中,鄭敏把生與死這個命題融入了自己對生命本質與意義的思考,與傳統詩歌重生輕死不同,鄭敏在《荷花(觀張大千氏畫)》中這樣寫道:“你們的根里,不是旋風的吹打/雨的痕跡,卻因為它從創造者的/手里承受了更多的生,這嚴肅的負擔。”將生視為嚴肅的負擔,可以說是詩人獨辟蹊徑,從生中讀出生命的隱患,詩人的態度是冷靜從容的。對于死,這個陰森恐怖的命題,在組詩《詩人與死》中,詩人發出如此憤慨的質問:“是誰,是誰/是誰的有力的手指/折斷這冬日的水仙/讓白色的汁液溢出/翠綠的,蔥白的莖條?”詩人對死亡的憤怒,詩人被無情漠視導致死亡的命運,嘲諷咒罵都無法喚醒已逝的生命,作者無奈而孤獨,詩人作出了這樣的重生愿景,“我們都是火烈鳥,終生踩著赤色的火焰,穿過地獄,燒斷了天橋,沒有發出失去身份的呻吟”,死亡真的能結束殘酷的寒冬嗎?詩人有了自己的沉思,死亡未必能終結生命的冷漠,哭泣、理想、太陽這些意象映襯著死亡的無情與痛苦,這是詩人的明辨之思。
生死同根,我國傳統詩歌中就有關于生與死的交融與升華,如元稹的《和樂天贈樊著作》:“天地為一物,死生為一源。”在鄭敏的詩歌中,我們也能找到對死亡的“友好”心態:忘卻死亡,將死亡視作一種對自然的歸屬,從死亡中尋找生命的意義,成為詩人在生死沉思上力圖達到的哲學境界。“詩人,你的最后沉寂/像無聲的極光/比我們更自由地嬉戲”(《詩人與死》),超越生死的界限,從死中悟出生的意義,獲取心靈的自由,是詩人對死的忘卻,在鄭敏的《墓園》《時代與死》《死難者》等詩歌中都可以讀出這樣的思考。正如詩人在《看不見的鯨魚》中所提到的:“她終于找到生命的燃點∕當那看不見的鯨魚∕將她吞食、消化時”,生命在自然中獲得永生,詩人忘卻生死,將神性在生死中自由出入。詩人試圖在生死之途中尋找生命的本真,這一路途會遭到世人的嘲諷,甚至自身會因為肉體的脆弱而懷疑怯懦。詩歌是墳墓上開出的奇異之花,召喚生命的歸鄉之旅。
對于生死的辨與忘,鄭敏試圖用孩子的純真挽回生死的希望,“是嬰孩在啼哭,人們聽著:期待、焦急、痛苦地等待/最終被啃透的繭壁”(《送別冬日》),“只有孩子和詩人看見這一切∕當樹還沒有從冬眠中醒來”(《冬眠的樹》)。《老子》二十八章:“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9]嬰孩般的純真,實際上是一種蒙昧無知、無欲無求的生命原始狀態,最接近混沌的生命之道,詩人贊嘆這種生命的原初希望,這是詩人的生命理想,復歸嬰孩,拋卻生死之懼,是心的回歸,善的回歸,在詩歌的馨香中抱樸見素,回歸生死同天地的合一。鄭敏曾寫《我的愛麗絲》述說自己的創作心路,夢中的愛麗絲不僅是詩人心靈的寫照,也是詩人在生與死中保持寧靜的要義。純真、好奇的童心,這是鄭敏在生死的辨與忘之間創造的理想,也是詩人在生死的喧囂與困頓中的寧靜思考,不回避生死,又不囿于生死,在生與死的辨忘中如孩童一般,與天地同心,自然從容。
三、母語寫作的寂寞
鄭敏曾經說過:“一個民族的詩歌如果脫離了它
自己幾千年積累下的詩學傳統進行創作,就像一個民族的建筑并無自己的設計風格和藝術個性,只能追逐她文化的外表,依樣畫葫蘆。”[10]母語,是集體意識和無意識的結合,是深扎在血脈中的語言文化傳統與文化思維。鄭敏,經歷了20世紀初“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動蕩,漢語對鄭敏而言有著劫后余生的珍貴,用詩歌的想象和感悟重新拾回漢語的閃光,在漢語的光輝中建構詩歌飛翔的境界。新詩的誕生已近百年,然而幾千年的詩歌傳統卻未曾真正切斷過。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是存在者的家園,語言最接近生存的本質。如果詩歌的語言脫離了賴以生存的土壤,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變成毫無意義的文化廢墟,陷入真正的文化失語。
鄭敏的漢語詩歌寫作,用凝練的語言構建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詩歌境界。早期的代表作《金黃的稻束》,我們的思緒又回到了那片金黃的稻田,有疲倦的母親,有高掛樹巔的滿月,有暮色里的遠山,在那里稻束、母親、滿月之間靜默地交流。金黃的稻束是母親生命力的象征,從稻束想到疲倦的母親,金黃意味著生命自然的張力,而疲倦則意味著生命的枯萎,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是對生命完整的詮釋。“歷史也不過是腳下一條流去的小河∕而你們,站在那兒∕將成了人類的一個思想”,把歷史與生命放在一起,歷史成了悄然而逝的河水,而生命的力量卻成為永恒的思想。在詩歌的境界中,生命的力量得到極致的禮贊,是詩人在俗世中獲得的一點通透詩心。鄭敏自己說過:“境界是知性進入悟性高度后的一種審美智慧,這是我國漢詩不同于西方詩品的一種特殊的心靈美學。”[11]鄭敏用自己的詩歌創作滋養著這一心靈美學,最終建構自己的審美詩學與詩歌理想。
這是一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各種思想的交融使快餐文化、網絡文化占據著文化的話語權,電影、電視在商業化的操作下成為文化的主流消費,詩歌陷入越發邊緣化的境地。物質的滿足,精神的貧困,那詩人的責任是什么?海德格爾在《詩人何為》說荷爾德林是貧困時代的詩人的先行者,出于未來而到達。詩人應該是堅定的信仰者和預言家,關心世界和人類的命運。在詩壇的眾聲喧嘩、浮躁凌厲中,鄭敏依舊用質樸靜謐的漢語建構自己關于善和美的審美理想與詩歌信仰。這樣的堅守來自于不斷的心靈修為與完善,在詩歌生涯沉默的三十年中鄭敏依然沒有放棄,她曾說:“除去這30年的空白,我的詩歌創作或者前后大約有30年,但靈魂的磨煉卻遠遠超過半個世紀。”[12]靈魂的磨煉,這是鄭敏作為一位詩人,一位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責任與承擔,在寂寞中磨煉升華生命的意義,建構生命的理想,在八十年代歸來之后,鄭敏出版了《尋覓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鄭敏詩集1979—1999》等,在詩學理論的建設上也成果豐碩。《詩呵,我又找到了你》作于1979年,是詩人經歷與詩歌分離重逢的際遇,是笑聲中悲凄的回憶,“我吻著你墳頭的泥土,充滿了歡喜。讓我的心變綠吧,我又找到了你”,冬眠的心靈終于得到解凍,在冷酷的寒冰中流動著詩人最炙熱真誠的詩歌信仰。
作為一位橫跨現當代,仍然在執筆寫作的老詩人,詩歌已不單單是一種寫作,更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命運。這命運不但指詩人自己,指涉的更是對歷史和生命的洞察。作于1982年的《曉荷》中,詩人力圖建構一種善與美的理想和信仰。荷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常見意象,荷花高潔,出淤泥而不染,是君子的象征。在詩人鋪設的荷花場景中,“風微微擺弄著荷花/雪白中泛出紅暈,在那微紅的尖端/平衡著理想和靜穆”,荷花色調分明的姿態是自然的神來之筆,而這姿態中正蘊含著一種生命最初的美:平衡。中國古代文化歷來講究陰陽諧和的美,乾道剛健,坤道柔順,中國詩畫歷來也追尋留白的美感。荷花是感性的意象,而平衡是知性的理想,詩人描繪的不是一幅觀物、詠物圖,而是試圖將理想的知性融合荷花的物性,自我與他物的合一,在這里沒有自我的狂妄,而是還原物的本真,還原那個被遮蔽的世界,“讓每個生命完成自己的歷程,這就是美”,鄭敏用自己的詩重構了平衡的生命美學,靜穆、舒展、順應自然,生長、成熟、死亡都是生命必經的歷程,不苛求生命,不扭曲生命,完成自然應有的變異。這不僅僅是詩歌的美學,也是人類的命運。
四、寂寞詩途,理想還鄉
八十年代以來,歸來的九葉詩人,依然用自己的詩歌創作為新詩現代化尋找某種可能,“現實、玄學、
象征”這樣的知識分子創作也許與當今的浮躁之風格格不入,從他們初登詩壇開始,這樣的詩歌旅途注定是寂寞的,或許就是在人們的漠視淡忘中才能保持對生命獨立冷靜的思考,指涉人類命運的歸鄉之途。我們始終認為,詩歌作為文學的塔尖,詩歌的命運是寂寞的,詩人也是如此。正因為詩人寂寞的堅守,在浮躁過后我們的心靈才得以自足。在九葉詩人中,鄭敏的創作生涯一直持續至今,歸來之后詩人無論是詩歌創作還是詩學理論都保持著持續的尋覓與探索。這對一位老詩人來說難能可貴,我們慶幸當今詩壇有鄭敏這樣寂寞的堅守者,以漢語古典詩歌傳統為根,吸收著外來文化的雨露,豐富著現代漢語詩歌的意義。現代漢語詩歌形式上是散文的,但內在思維仍然是詩歌的。寂寞,是鄭敏獨一之詩的位置,是詩歌的審美天地。寂寞的堅守,意味著孤獨的詩歌旅途,有嘲笑譏諷,卻能收獲血淚之后與天地一心的境界。在眾聲喧嘩、浮躁凌厲的時代,我們需要一種寂寞的聲音,撫平心靈的枯寂,用寂寞的詩歌,召回心靈的棲息之地和久違的信仰。鄭敏的詩歌,以寂寞為生命詩學,在靜默的對話中,生命的詩意棲居有了尋找的可能。
【注釋】
[1]蔣登科:《九葉詩人論稿》,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頁。
[2]鄭敏:《對21世紀中華文化建設的期待》,《思維·文化·詩學》,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頁。
[3]參考吳思敬、宋曉冬《代序:鄭敏——詩壇的世紀之樹》,《鄭敏詩歌研究論集》,2011年版,第2頁。
[4]海德格爾著 孫周興譯:《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0頁。
[5]老子著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頁。
[6]老子著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8頁。
[7]藍棣之:《九葉派詩選·前言》,《九葉派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頁。
[8]李怡:《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頁。
[9]老子著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13頁。
[10] 鄭敏:《新詩與傳統》,《思維·文化·詩學》,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79頁。
[11]鄭敏:《今天新詩應當追求什么?》,《思維·文化·詩學》,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頁。
[12] 鄭敏:《鄭敏詩集1979-1999·序》,《鄭敏詩集1979-1999》,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
[1]藍棣之編選.九葉派詩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2]老子著 王卡點校.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M].北京:中華書局,1993.
[3]李怡.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4]海德格爾著 孫周興譯.在通向語言的途中[M].商務印書館,1997.
[5]鄭敏.鄭敏詩集(1979—1999)[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6]鄭敏.思維·文化·詩學[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7]海德格爾著 孫周興譯.林中路[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8]蔣登科.九葉詩人論稿[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9]吳思敬,宋曉冬編.鄭敏詩歌研究論集[C].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
[10]馬永波.九葉詩派與西方現代主義[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
[11]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2]鄭敏.鄭敏文集 詩歌卷:全2冊[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作者單位:云南民族大學)
責任編輯:萬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