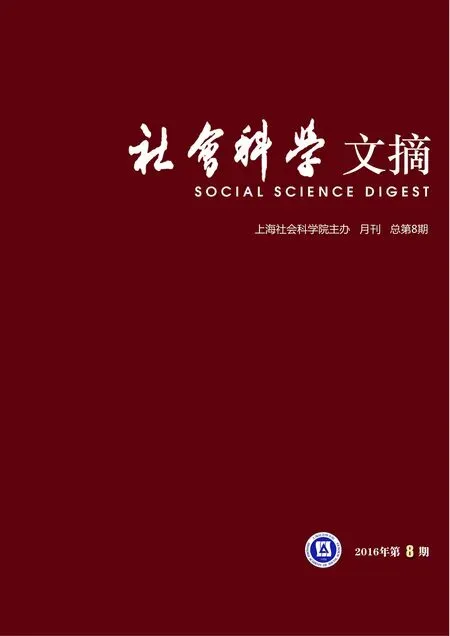啟蒙視野中的莊子
文/陳少明
啟蒙視野中的莊子
文/陳少明
新文化運動百年之際,以紀念或反思的名義舉辦的各種活動,可謂盛況空前。而反思的主題,多集中在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聲浪及啟蒙意義上。啟蒙與反傳統關系密切,但有所區別。一般來說,反傳統指稱的對象比較明確,多集中于以“打倒孔家店”為標識的反儒家文化,特別是反其政治功能與倫理價值的思想運動。而以啟蒙為對象的反思,除杜維明先生對“啟蒙心態”略有談論外,可能未有多大的共識。直觀地看,似乎是紀念啟蒙與反思反傳統,各有側重。我的問題是,由于孔子或儒學在時下的政治氛圍中,符號形象有了改頭換面的變化,為儒學辯護的吶喊雖然正當而合乎時宜,但是否會因此而遮掩反傳統思潮中其他重要思想流派的處境,便成疑問。例如,傳統不只有孔孟,還有老莊,不僅儒家,且有釋道。儒家以外的重要思想流派,在新文化運動或者啟蒙視野中的命運如何,并非可有可無的問題。以莊子為對象,探討它在現代思想學術中的地位,意義不僅在于加深對傳統豐富性的理解,還可能在于,由此而接觸到反傳統思潮的某種思想特質,后者與啟蒙有關。
莊學、啟蒙與新文化
莊學是古學,但它不是正統或者主流,其地位往往是通過參照儒學來界定的。對莊子比較完整的評估,當從西漢的司馬遷開始。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司馬遷說莊子“詆訿孔子之徒”、“剽剝儒、墨”,這就意味著莊子很早就被置于儒家的對立面。然至魏晉,儒道交匯,“三玄”之一的《莊子》,大行其道。因郭象注而影響深遠,取得與儒家經典相提并論的榮耀。宋明理學雖以辨道統,拒二氏為主旨,但為莊子抱屈的儒者大有人在。王安石就辨析說,莊子是在“天下陷溺以至乎不可救”的情況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于正”,“莊子豈不知圣人哉”。其后如蘇東坡的《莊子祠堂記》、王夫之的《莊子解》所持,大致不出王說的范圍。站在儒門的立場上,判斷莊子非儒、屬儒(或真儒)的關鍵,在于如何看待莊子對仁義觀念的態度。換言之,仁義是傳統莊學評判莊子的基本范疇。而在儒家傳統被受責難的年代,這評判的標準自然不再是儒家提供的。
新思想的標準來自“啟蒙”(enlightenment),不過它有借喻與實指兩種用法。有人用它來形容清代近三百年學術思想,這種啟蒙的用法只是借喻。至于實指,則是指受西方啟蒙運動所帶來的現代價值觀念影響而形成的思想運動,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是它的高潮。據伯林在《反啟蒙運動》中對啟蒙思想的概括,我們可以知道:啟蒙相信在自然、人類與社會中,存在一種普遍的內在秩序,它能為理性所把握。人類充分地運用這種能力,就能通過斗爭,從迷信與不道德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就能征服自然,改造社會,走向進步,迎接美好的明天。與此對照,一百年前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的主張,雖可簡化為要自覺地為科學與人權而奮斗,然而實際上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價值觀念,如自由、人權、平等、階級、斗爭、解放、科學、理性、進步等等,均已出現或包含在陳獨秀這篇吹響時代號角的戰斗檄文之中。雖然日后隨著意識形態的變遷,這些不同的詞匯重要性或其結構位置不一樣,但毫無疑問的是,它們基于共同的思想根源。它是反傳統的思想支柱,同樣也是現代莊學的評判原則。只是由于莊子的思想特質,使其呈現的形象,與儒家很不一樣。一般的讀者也許會好奇:作為傳統邊緣甚至異端的莊子,其新的時代形象,會來個大逆轉嗎?
時代形象
一開始,莊子研究的確出現順應時代情勢的新面貌。新形象的設計師,是真正大師級的學者與思想家章太炎,代表作是《齊物論釋》,其序曰:“畢竟平等,乃合齊物之義。”雖然該書成于20世紀,《新青年》創立之前,但它的核心范疇——平等,無疑與影響新文化的啟蒙觀念相關。當然,太炎對平等的追求,并不止于西式的啟蒙觀念。在他的心目中,文明與野蠻之分,或者進步與落后之別,同樣與莊子的平等義不相容,不過,這種對啟蒙的“啟蒙”,在啟蒙時期,并沒有太多的回響。
與啟蒙相應的另一面,是“科學”注莊的方式。新近的研究者指出在《齊物論釋》中,章太炎引用了包括生物進化論、細胞學說等在內的許多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知識。而新文化運動的健將胡適,則居然在《莊子·寓言》、《至樂》篇中發現了進化論的思想。胡適特重進化論,是因為達爾文學說挑戰神造萬物的觀念,在西方造成廣泛的影響。
馮友蘭論莊子也帶欣賞的態度,且也借助西學的觀念。《中國哲學史》論莊章節的標題,就有“變之哲學”、“何為幸福”、“自由與平等”、“純粹經驗之世界”、“絕對之逍遙”等等。關于自由,馮氏認為“莊學中之社會政治哲學,主張絕對的自由”,“主張絕對的自由者,必主張絕對的平等”,并認為在此點上,莊學與佛學有著根本不同。馮氏論莊,對自由與平等關系及莊、佛不同之理解,似乎是延著太炎的問題來的。不過,他的哲學詮釋,更傾向于西方哲學。例如,其以西方哲學的純粹經驗(Pure experience)來解釋莊子的“知無”觀念。
郭沫若的《十批判書》,辟有專章“莊子的批判”。他的特色是強調莊子的個性,并且是在同儒墨的對比中評價的。郭氏認為相對于墨家抹殺個性,在尊重個性這一點上,道家和儒家比較接近。郭氏是通過莊、顏一派的推測來界定莊子與儒家的關系的。他關于儒家主張個性的說法,不大可能得到當時主流意見的認同,但用個性來肯定莊子,無疑是納入啟蒙的思想范疇。
用平等、自由、科學、個性等觀念讀出來的莊子,與以辨道統或正道德為目標的傳統莊學相比,自然大異其趣。不過,這只是莊子現代命運中比較風光的一面而已。啟蒙視野中莊子的另一面,同樣引人注目,甚至可能更耐人尋味。
反面典型
其實,現代莊子的反面形象,比正面形象給人印象更為深刻。而且,批評與贊揚相比,常常更顯得理直氣壯。焦點在于《齊物論》引出的“齊是非”問題,它是莊子哲學的核心所在。在《莊子的進化論》一文中,胡適在侈談莊子進化論的同時,就表達他對其厭惡的一面。魯迅也針對無是非的觀點,在他的文章中,時不時拿莊子來開涮。
當然也有對此進行哲學分析的,代表作是侯外廬等著的《中國思想通史》。作者認為,齊是非的觀點,會導致實踐中互相矛盾的立場,即“一個是棄世的脫俗,一個是處世的順俗”,而最終的結果,便是“處世的宿命論”。侯著是革命意識形態未占領統治地位之前,一種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觀點。它不但同樣拒斥不利于革命的宿命論,同時,還把胡適或馮友蘭稱之謂神秘主義的東西,稱做“唯心主義”——這是日后給所有不符合新意識形態要求的哲學觀設計的黑標簽。關鋒便是順著這一套路,把批判莊子的立場推到極端,把虛無主義、阿Q精神、滑頭主義、悲觀主義,等等,都安到莊子主觀唯心主義頭上。他發明了對莊子哲學的解讀公式“有待—無己—無待”,并由此推出其主觀唯心主義的歸屬。他較有創造性的說法,是把“精神勝利法”的發明權歸于莊子,并認為“它是反動沒落階級的精神狀態,阿Q其人不過被傳染了這樣一些東西”。把莊子說得如此不堪,在莊學史上是很少見的。原因在于,關鋒嘴里說的是莊子,心里想的卻是現實的意識形態敵人。與其他反莊的前輩比,關鋒更強調階級的立場。
羞辱莊子幾乎成為20世紀50年代以后、80年代之前莊學的主調。雖然任繼愈極力為莊子“脫罪”,但成效不大。他是利用《莊子》文本的不同思想傾向,通過顛倒《莊子》內、外篇作者的歸屬,認為外篇才是莊子本人所作,而內篇反而不是,從而達成為莊子辯護的途徑。但是,這一說法證據勉強,且論莊的思想框架與關鋒也無實質區別,同樣講唯物、唯心,講階級,講斗爭,因而無力顛覆已經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莊子形象。所以,任也承認:“莊子這一派道家思想是不能有殉道者的。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的思想家,他們盡管對不合理的社會有所不滿,但他們不敢進行斗爭。這些人往往采取莊子思想中的消極態度。”
只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意識形態有所松動的狀況下,莊學的調子才開始改變。陳鼓應起了號手的作用,新的關鍵詞還是“自由”。陳認為莊子用“游”來表達精神的自由活動,而要求得這種自由則需要兩方面的提升,一是使精神從現實的種種束縛下提升出來;一是使人從封閉的心靈中超拔出來,從自我中心的格局中超拔出來。陳甚至斷定,“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中國的思想家,如陳獨秀、魯迅、李大釗,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尼采和莊子的影響,特別是在個性解放和精神自由方面。”這意味著,一個重新評估莊子甚至反思莊學的時代已經來臨。
從莊學看啟蒙
表面上看,現代莊子形象經歷了前后兩個階段的變化。一個是前期與新文化思潮關系更密切、更具正面意義的莊子,另一個是后期特別是文革前后呈現的只有負面意義的莊子。而莊子同孔子等儒家人物一樣被羞辱的時代,也是我們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特別壓抑的時代。這種區別很容易讓人覺得,從革命意識形態中把莊子再“解放”出來,同回到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理想,是可以合二為一的事情。但問題沒有那么簡單。
重讀當年的批判文章,可找到兩個指控莊子的基本概念,相對主義與唯心主義。與這兩種指控相聯系的當是《齊物論》和《逍遙游》的觀點。《齊物論》因“齊是非”而由相對主義滑向無是非,混世隨俗;而《逍遙游》則無視客觀世界的規定性,回避現實,是主觀唯心主義,并且是一種精神勝利法。而作為批判出發點的觀念,則是科學真理、唯物主義、階級斗爭等等。而這些觀念,幾乎都可以追溯到新文化運動體現的啟蒙價值上。在前面所列一組大詞中,自由、人權、平等、階級、斗爭、解放、科學、理性、進步,等等,幾乎就是百年來取代傳統的仁義理智或天理人倫而流行的主流價值觀念。革命意識形態對這些價值可能有所篩選或重新排序,如自由、人權的地位后來下降了,這使得莊子在啟蒙期的好時光變得短暫;又如階級與斗爭的重要性上升了,因此莊子剛好撞到槍口上。這部分解釋了現代莊子形象的變遷。然而,有幾個重要的觀念,如科學、理性與進步卻百年來幾乎沒有爭議。這幾個重大概念對現代意識形態的支撐關系需要深入分析。
科學是最沒有爭議的。從康、譚、章滿紙聲光電化,到嚴復對西方科學及其思想的譯介,再到新文化運動科學與人權(或民主)的口號;從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科學派的得勢,再到馬克思主義以科學的名義對意識形態的支配,科學扮演啟蒙最重要的角色,在中國現代史上可以說是一路高歌。而國人對科學的理解,首先是與技術的效能相聯系。在一個物質貧乏的年代,擁抱科學意味著追求富強,意味著現代化的展開,其正當性幾乎是無須證明的。而科學與客觀知識、物質利益的聯系,又恰好成了唯物主義哲學宣傳的依據。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科學派就有人把科學與物質文明、人生觀與精神文明對位連結起來的。這種思想邏輯演化出來的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的斗爭,就把一切重視精神生活意義的思想,都當成虛妄無用的觀念、甚至維護反動階級利益的說辭加以譴責。在科學派為說明科學如何支配人生觀挖空心思而未能服人之際,陳獨秀就聲稱唯物史觀就是能夠說明社會與人生問題的科學。對照前引伯林對啟蒙運動精神的概述,陳獨秀的這份信心,其實就是理性的獨斷。在這副啟蒙的照妖鏡里,任何懷疑主義、相對主義以及逃避主義,自然都會“原形畢露”。
莊子哲學的核心“齊是非”,在《齊物論》中有一連串的論述。其要點是指諸子尤其是儒墨的文化或政治立場,即那種今天可以稱之為“主義”的問題沒有是非。依其觀點,定是非的困難在于對立的各方之間沒有或不愿意接受公共評判標準,同時又不能以自己的標準作為標準。盡管有人會根據《人間世》中支離疏的行徑,指責其混世的人生導向。或者從邏輯上指出無是非觀點因自相矛盾而不能成立。但是,莊子不是在任何層次的問題上強調無是非,他對權勢者不合作與拒絕的立場非常清楚。今日各種宗教以及意識形態斗爭的現象,表明莊子的假設更合乎事實。任何一種以抽象信念為出發點的原教旨主張,都會造成沖突的激化而非是非的解決。
與“齊是非”相聯系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莊子向我們指出,什么是美好的生活沒有公認的標準。與孟子不同,他強調獨樂,不講共樂。其不講共樂的動機不是見不得別人幸福,而是每個人可以各樂其樂,但不要把自己的愿望、標準強加于人。從而也不能設計自以為讓每個人都能幸福的社會秩序。他懷疑儒家的仁義禮樂,就是懷疑這種制度設計不合乎人類參差不齊的自然天性,它可能在實踐中起反作用。
莊子這兩種觀點,在現代莊學中都沒得到應有的回應。它與斗爭哲學、進步主義及科學的人生觀隔隔不入。關鋒式的批判當然是革命意識形態的一種表述,社會主義不但是斗爭來的,而且要給每個人規劃有意義的生活。雖然這種理論受其革命勝利者的身份所左右,但思想來源與啟蒙思潮相關。其要點是相信自己(有知識者或進步階級)具有掌握真理的能力,相信依據某種科學的思想方式,就能發現、規劃讓每個人行為統一的整齊的社會秩序,如人民公社、五七干校之類的生活模式。同時,要清除那些落后的、非科學的,或者無用的觀念,給健康的精神生活規定方向。所以對莊子式的思想表現得特別的不寬容。
本文不是針對莊子而是莊學。其實,不論是褒是貶,現代莊學所依托的信念都與啟蒙有關,不管自由、平等,還是科學、斗爭(革命)。但莊子形象前后反差極大,意味著啟蒙雖有某些共同的傾向,但不是一個完整的思想系統,即不是從一個前提推演出來的諸觀念的集合。這些觀念必須在廣泛的社會生活實踐中協調起作用,而非按理性序列可自動實施。因此,每種價值的作用都有自己的限制,它們本身是需要被反思的。莊子思想可以被壓制,但不會被消解。你很難把它歸結為現代的什么“主義”。20世紀90年代以后,莊子又逐漸作為正面形象出現學術或文化讀物中,就是它思想不屈的證明。莊子哲學一直作為文明的批判者的角色而存在,其避世逍遙的主張也許對人類社會生活沒有普遍的吸引力,但它提出的問題,特別是對理性作用的質疑,對啟蒙的推動者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考題。
【作者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摘自《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