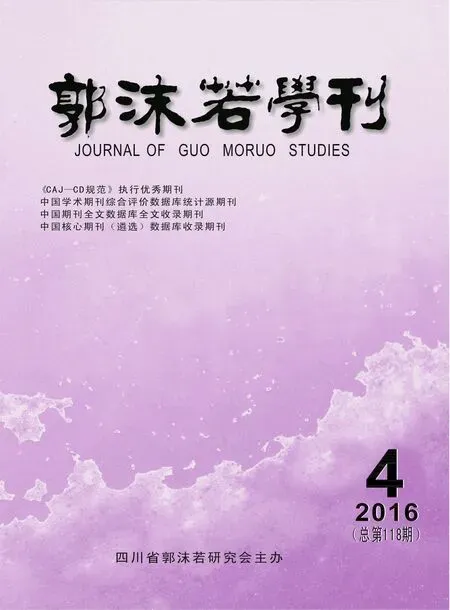回憶郭沫若先生*
杉原莊介著 趙藝真 譯 潘世圣 校譯
回憶郭沫若先生*
杉原莊介著趙藝真譯潘世圣校譯
編者按:日本作為郭沫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第二故鄉,他的詩碑(《別須和田》一詩)將在千葉縣市川市建造。郭氏1914年赴日留學,先后在一高特設預科、六高、九州帝國大學學習,和日本女子佐藤富子結婚,有四男一女。他于1928年到1937年期間逃亡日本,住在市川,期間完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給日本學界帶來不小的影響。本文是在今年(1964年)6月28日召開的“郭沫若詩碑建設發起人會總會”上,明治大學杉原教授(考古學專家)的演講稿。
一、初次與郭先生見面
建立郭沫若詩碑一事,我很高興也很贊成。郭沫若先生一生命途多舛,可以寫成一篇傳奇小說。
關于這一點,有很多書中都有涉及,應該有很多人了解。就我個人來說,對郭沫若先生有著自己的印象。接下來,我想談談我對他的印象。
如果有不對的地方,還請指正。無論如何,我認為,我作為一個日本人,對郭沫若先生的印象多少是有參考價值的。
初次和郭先生見面是昭和8年(1933年)。我在中學時代,跟著有名的考古學家古井久義先生考察了很多古跡。古井先生的弟子們成立了一個學會,叫做武藏野會。此學會雖形式有變動,但至今仍存在,聚集了各行各業的人。我在學會上聊天時,有人跟我說“既然你也住在市川,跟郭沫若先生見一面如何”,因此我拜訪了郭沫若的府邸,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郭先生。
那是昭和8年的事情,距今已有31年了。那時我剛從中學畢業,在東京外國語學校學習法語,還沒有進入明治大學,還沒學會觀察和認識他人。那時郭先生應該已經寫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了。這本書幾乎沒有涉及郭先生自己的事情,但從日本或中國的歷史研究史來看,無疑是舉足輕重的著作。日本有《古事記》、《日本書記》等成文史書,日本歷史研究不能脫離于此。因此,無需研究日本古代,已經有定本了。中國也是如此,有很多古代神話記敘了中國古代的事情,在很長一段時間發揮作用。歷史這一學問是不斷進步的,恩格斯的著作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以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研究為基礎并加以利用,將歷史置于唯物史觀歷史的一角,翻開了歷史研究史重要的一頁。然而,日本處在尚未接受此批判式歷史研究方法的時期。
中國亦是如此。因為中國是傳統國家,歷史多從漢代開始,這是東洋史已經形成的傾向。當時郭沫若正處于日本流亡時期,他的著作是將恩格斯歷史觀巧妙融入到中國歷史研究中去的第一本書。可以說,郭先生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著作,使中國歷史學研究步入了近代。這本在逃亡期間完成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意義重大。
當時我還是個少年,經常拜訪郭先生,從郭先生那里學到了很多定論。那時,在現在的須和田公園那里,有最初傳入須和田的原始農業的部落遺址。考古學家們認為,關東地區原始農業最初由須和田傳入,這里是標準遺跡之一。我決定去須和田的丘陵挖掘遺跡。郭先生知道后說“我去幫你吧”。有一天郭先生身著和服,蹲著幫我挖掘。我至今還記得郭先生拿著容器,我們兩人一起測量一處遺址。因為郭先生家離得不遠,他的孩子們,看起來還在上幼兒園或小學,也過來圍著我們,很是熱鬧。
如今再回想起那個時候,郭先生大概沒有考慮過再次回到中國,擔任重要職位參加革命吧。這次刻在詩碑上的詩中,他也寫到自己有可能埋葬于市川,我覺得那是他的真實想法。革命發生之際,他作為革命家很活躍,但應該沒有能夠預想到革命何時發生的歷史學家吧。因此,郭先生應該有隱居市川,在此度過余生的覺悟。
在這期間,郭先生的研究大有進展。他完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后,對中國古代產生了濃厚興趣。日本人學習中國古代史,需要學習漢字、中文。而郭先生因為具備本國的學識,所以了解得比我們更深入。而且,理解中國古代社會也需要考古學知識。這一點先生可謂頗有研究。此外,在中國,形成了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有關于在牛骨或烏龜殼上刻字占卜的記載,這些字發展成為現在的漢字。幸運的是,那時甲骨文字的閱讀已經相當發達了。因此,具有科學歷史素養的郭先生,利用這些科學的資料,開展了因循守舊之人無法進行的研究。
中國在殷商時期形成國家后進入周朝。殷商時期還處于石器時代之前的青銅器時期,周朝中期中國首次使用鐵器。中國發生了諸多變化,特別是刻在青銅器上興盛一時的文字作為銘文流傳下來。
郭先生在古代文化中尤其擅長解讀青銅器上的銘文。這些文字多是直接記載了當時的社會構成、社會樣貌,但到現在為止,古典的歷史學者還讀不懂。郭先生擅長解讀這些文字,在市川的時候,也寫了關于青銅器文字閱讀方法的書,這無疑對科學研究中國古代史非常有用。總之,他是科學研究中國歷史的開拓者。郭先生在研究上文提到的這些研究期間,我與他有來往,這對我的學習非常有益。如今我仍然珍藏著他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初版。
此后,日中關系日益惡化,我拜訪他的機會也越來越少,郭先生最終回到了中國。那時他的兒子們剛從小學畢業進入中學,很巧的是他們幾乎都進入了我的母校。我曾拜訪校長,并請求校長說,他的孩子們處境可憐,如果發生什么請保護他們。不久,我自己也應召在華北和華中呆了兩年。戰爭結束時我留在上海,從事新聞相關的工作。我想著和郭先生見一面,但沒有實現。
二、再會科學院院長郭先生
革命結束后,隨著新中國的建設,開展了很多工程,且多以城市為中心。中國很多地方都埋藏著重要的文化財產,因此,新中國建設開始后,考古學上的發現也比戰前進步顯著。那時,郭先生是中國科學院院長,在科學院開設了考古學研究,非常活躍。
我從心底感覺郭先生是非常稱職的科學院院長。在中國科學院,各學科學者分配在各個研究所,共同組成了科學院。
科學院與大學也有關連。中國科學院所屬的各個研究所培養的學者,來到各個大學的研究室成為教授,說各個大學隸屬于中國科學院也并不夸張。因此,中國科學院匯集了中國的所有學問。我很高興郭先生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一職。之后我去中國時聽說,郭先生常說“學問非常重要”,并竭盡全力為科學院籌集資金。只有像郭先生那樣的人才能切身體會到學問的重要性。
1955年,日本學術會議邀請并接待了訪日視察團的中國學者。我為郭先生擔任視察團團長感到高興。
郭先生安排了考古學方面的學者(?先生)參加視察團。他說要來市川視察一天,這個計劃得以實現,我在市川見到了先生。他將重訪市川舊居之感慨寄托于詩歌之中。在詩中他也寫到,他對須和田山川的所有角落都很熟悉,了解它周圍的墓地、古墳。他的詩歌也常常描寫這一帶的景色。這該是何等感慨之情啊。
之后,日本考古專家組成訪華團前往中國,在與周恩來總理見面時,周總理多次提到,是郭先生邀請你們來的。我以為郭先生真是性情中人。
我們被當作國賓得到款待。在五一勞動節前天晚上,我們和中國考古學者們充分交換意見。郭先生非常激動,跟我握著手熱烈討論了一晚上。他為我們安排了最好的行程,我們在中國呆了兩個多月,幾乎走遍了所有遺址。我們詳細了解了戰后迅速發展的中國考古領域,對我們回到日本開展新的考古研究大有裨益。也因此,日中兩國考古研究所現在仍有交流,形成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模式,這離不開郭先生的努力,我深表感謝。
我相信將來,日本考古學者和中國考古學者也會持續這種在其他學科領域沒有的密切關系。這當然也是郭先生努力的功績。
譯自《亞洲經濟旬報》第585期(1964年8月)
(責任編輯:廖久明)
*本文為2015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回憶郭沫若作品收集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5AZW011)的階段性成果。
2016-10-24
杉原莊介,生于1913年12月6日,東京人。1943年畢業于明治大學,歷任該校副教授、教授,1977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杉原莊介曾主持日本靜同市登呂彌生時代遺址和群馬縣巖宿舊石器時代遺址等重要考古發掘工作。主要著作有《原史學序論》、《彌生式土器文化の生成》、《群馬縣巖宿發現の石器文化》、《日本青銅器の研究》、《日本先土器時代の研究》、《日本農耕文化の形成》等。
趙藝真,華東師范大學日語系碩士研究生。
校潘世圣,華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主任、教授,日本九州大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