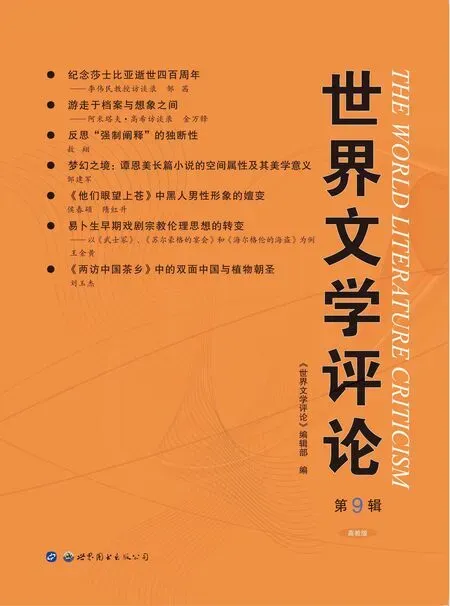記憶中的未來與魔幻中的現實
——《未來的回憶》中的魔幻時間觀
楊 力
記憶中的未來與魔幻中的現實
——《未來的回憶》中的魔幻時間觀
楊 力
墨西哥女作家埃萊娜·加羅是拉美文學爆炸前最早開始用魔幻的手法來創新拉美傳統小說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多具有濃烈的魔幻現實主義特色,雖不為大眾熟知,其文學價值卻絲毫不遜色于任何一位大家之作。長篇小說《未來的回憶》是一部教科書式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加羅通過游走于現實與虛幻之間的筆觸再現了大革命后最真實的墨西哥社會。本文將分析《未來的回憶》中所使用的主要魔幻元素——魔幻時間觀,并通過魔幻現實主義作品中魔幻元素對于描寫現實的重要意義來探討這部小說通過魔幻時間觀展現現實的方式及其對于表達現實的作用。
《未來的回憶》 魔幻現實主義 時間
墨西哥女作家埃萊娜·加羅(Elena Garro, 1916-1998)(以下簡稱“加羅”)并不為國內讀者所熟知,甚至在西班牙語國家也并不廣為所知,或許是她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奧克塔維奧·帕斯第一任妻子的頭銜遮蔽了人們的視線,又或許是丈夫太過耀眼的成就掩蓋了她的光芒。然而她被認為是“20世紀墨西哥最優秀的女作家”,她的代表作《未來的回憶》(Los recuerdos del porvenir)被一眾西班牙語文學評論家認為是一部杰出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這一作品的出版甚至比被奉上神壇的魔幻現實主義經典作品《百年孤獨》早上了四年:《未來的回憶》第一次出版是在1963年,而后者則是在1967年,而在此前的50年代末加羅就已經出版了同樣魔幻現實主義色彩濃重的劇作集和短篇小說集。因而《未來的回憶》雖是一部較早期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但加羅在經過早期作品的探索后,這部作品中她所運用的各類魔幻現實主義手法與技巧絲毫不遜色于后來拉美文學爆炸中涌現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小說中不乏各類精彩的魔幻情節。
《未來的回憶》敘述了上個世紀20年代發生在處于嚴酷的軍人統治下的墨西哥小城伊思特佩克的故事。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講述統治小城的軍官們和他們的“親愛的”們的生活,這其中又以伊思特佩克的絕對權力者弗朗西斯科·羅薩斯將軍和他的情人胡莉婭的情感糾葛為主線,直至最后胡莉婭與突然出現在小城的外鄉青年費利佩·烏爾塔多一起神秘消失。第二部分主要講述了蒙卡多家族的悲劇:哥哥尼古拉斯成為了反對軍隊統治的先鋒最終難逃被判死刑的命運;而妹妹伊莎貝爾因愛上了伊思特佩克的仇人羅薩斯而甘愿做他的新情人,卻因此廣受市民的唾棄,最終無法接受哥哥的被害和羅薩斯的背叛,受到刺激變為了一塊石頭。
人如何可能變身為一塊石頭?這樣看似荒誕的情節在普通的現實主義小說中當然不可能出現,但在魔幻現實主義中卻司空見慣:《百年孤獨》里的奧雷里亞諾遭遇了14次暗殺,73次埋伏和一次槍決后卻均幸免于難;《佩德羅·巴拉莫》中死人竟然能像活著的人一樣說話行動。這樣的情節當然就是小說中的魔幻部分,然而魔幻元素并不止于此,魔幻也絕對不僅僅限于荒誕不真實。諾貝爾獎獲得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曾在《百年孤獨》西班牙再版時在《國家報》上發表了一篇他為其做的序,其中指出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品具有兩張面孔:一張是客觀現實,另一張是想象的現實[1]。毫無疑問,這想象的現實便是作品中各類魔幻元素。可以注意到此處魔幻實際仍為一種現實,只是與普通大眾日常所見的廣為接受的概念下的現實不同——關于此類魔幻元素與現實的關聯將在本文后半段再做詳細闡釋。而關于這想象的現實具體包括了哪些內容,略薩也做了詳盡地解釋:“想象出的事件或人物其實是一個整體,因為它實際包含了四個層次的想象:魔術、神話傳說、宗教奇跡與虛構。”[2]
按照略薩的這種對魔幻因素的分類,《未來的回憶》中顯然并不存在前三種,而都屬于最后一類虛構。此處的虛構是指在讀者看來由作家憑借純粹的想象力創造出的情節,這類“創造”通常在大眾看來是夸張而不合實際的,比如上文提及的人竟可以變成一塊石頭。然而通過這些看似荒誕離奇的事件,讀者卻能更加深刻更加精準地感受到作家筆下犀利的現實,加羅正是用她細膩的想象給我們刻畫出了最真實的墨西哥社會。墨西哥學者勞爾·卡爾德隆·伯德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想象是這位女作家(加羅)和她小說中的人物所擁有的唯一與現實抗爭的途徑。”[3]《未來的回憶》中的魔幻情節遠不止結尾處女主人公變為石頭這一處,這其中給人留下印象最深刻也是最突出的魔幻元素當然是加羅所展現的奇妙的時間觀。
一、魔幻的時間觀——走進人物的“心理時間”
在加羅的世界里,時間并不是一根根永不停息不斷轉動的指針,她的時間是柔軟又極富彈性的,并沒有固定的前進方向,這些指針時而停止了轉動,時而轉向反方向,時而又以跳躍的方式轉動……她的時間觀或許正可以很好地解答我們對這部小說的標題的不解:一個人怎能回憶起自己尚未經歷的未來?然而伊思特佩克的居民卻正是在給我們回憶他們已經經歷過的不幸的將來。
作者在故事的開篇就提到了蒙卡多家族的一個傳統的習俗:每天晚飯后,傭人菲利克斯都會卸下時鐘的鐘擺,這樣時鐘就不再會發出聲音打擾家人休息,然而時間也就停止了。這實際是人為地將時間暫停:
“沒有了時鐘的嘀嗒聲,這間屋子和它的居住者就進入了一段新的憂郁的時間里,在那里所有的動作和聲音都活動在過去。堂娜安娜,她的丈夫,年輕人們和菲利克斯都變成了他們自己的記憶,沒有了將來,他們分別迷失在各自的一束昏黃的燈光里,這燈光將他們與現實隔開,將他們變成了回憶中的人物。”①
沒有了時間的流逝,時間軸上一直向前的箭頭也消失不見,只剩下了一條過去的直線,于是所有的一切都變成了過去,包括未來。所有發生過的正在發生的和即將發生的都成了回憶的一部分,這樣人們就可以有兩個回憶了:過去的回憶和未來的回憶。就如同書中伊莎貝爾對弗朗西斯科·羅薩斯將軍所說的:“弗朗西斯科,我們有兩個記憶……以前我活在這兩個記憶中,現在我只活在那個一直提醒我將要發生什么的記憶中。尼古拉斯也在這未來的記憶中……”(273)此時伊莎貝爾已經不想回憶曾經的那些和哥哥尼古拉斯一起玩耍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她的記憶現在只容得下那關于未來的回憶,而這未來就是尼古拉斯和她自己的死。而獄中的尼古拉斯此時也已丟棄了他關于過去的回憶:“他也記不清楚他家的結構,那些在那里度過的日子也不記得了……他記得自己的未來,而他的未來就是在伊思特佩克的原野上死去。”(286)無論是伊莎貝爾還是尼古拉斯都停止了他們自己的時間,就想他們家的那口鐘一樣,苦澀的未來成為了他們僅存的記憶。
他們二人所停止的時間實際是他們的“心理時間”,而并非客觀時間。兄妹二人深知等待他們的是什么,想要逃避這痛苦的結局的唯一辦法或許只能是麻痹自我,告訴自己時間已經停下來,而另一方面客觀時間卻一直向前,死亡的腳步也在漸漸向他們靠近,沒有絲毫同情,最終變成了回憶。而對于所有伊思特佩克的人民來說都是這樣,對于一座一直籠罩在軍人暴力的陰影下的小城來說,他的每天都充滿了不幸與悲傷,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反抗斗爭后,情況并沒有得到好轉,居民們明白未來依舊是一片陰霾,這種情況下,時間流逝與否于他們來說也就毫無意義:“不幸就像是身體上的疼痛將每一分鐘都變得一樣……未來就是過去的重復。”(67-68)如此看來,伊思特佩克會有關于未來的回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人物對心理時間的掌控在這部小說中出現了相當多次,而對整體情節發展影響最大的一次出現在小說第一部分結尾胡莉婭與外鄉人費利佩企圖出逃之時,這一次在全體伊思特佩克人的集體記憶中他們一起經歷了時間的停滯與跳躍。當費利佩已經無處可逃準備走出屋子坦然面對死亡之時,時間再次發揮了它的魔力:時間憑空停止了,就如同一場夢境降臨一般,隨之而來的是持久的沉寂,一切在那一刻都停止了,所有人仿佛都置身在了超脫時間之外的某一個永恒的空間里,只有胡莉婭與費利佩似乎并未受此影響,不知去向,直到整部小說的結尾,加羅也沒有向讀者交代這對年輕人究竟下落如何,他們最終的命運就永遠被從伊思特佩克的記憶中抹去了,而在第二部分中,伊思特佩克也跳過了這段時間,繼續講述這之后的回憶。這時間的停滯與跳躍顯然看似違反了自然規律,但實際也是伊思特佩克人對他們的心理時間的一次集體掌控,在那一刻或許是發生了一場殘暴的悲劇,人們不愿再記起這些畫面而共同選擇抹去這段時間的回憶,從而留給讀者也留給自己最后一絲希望,而這一絲希望就是對殘暴的軍官們的一種無聲卻有力的抗議。正如伯德在他的文章中評論道:“這個事件不僅僅觸犯了支配著我們生活的世界的物理定律,也是對小說本身所敘述的世界的價值觀的違背。很顯然這里運用的魔幻元素就像一支對抗統治權力的武器。”[4]而透過這魔幻的時間,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伊思特佩克所有的不幸與悲劇,因為透過這看似隨心所欲可以掌控的心理時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伊思特佩克人在殘酷現實中痛苦地掙扎。加羅透過這些不可思議的時間的停止與跳躍成功地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力,從而將現實更深刻地烙在了讀者的腦海中。
如果說在文中的多處細節處,加羅成功地“掌控”了時間,就小說的整體結構來看,她也賦予了時間一股魔幻色彩。整部作品從頭至尾幾乎沒有提到具體的年月日,只在末尾處提到伊莎貝爾生于1907年,死于1927年。作為敘述文的要素之一,故事發生的時間背景從頭至尾不被提及這一寫作手法是極其罕見的,這顯然并不是作者的疏忽。故事的開頭伊思特佩克這座小城作為敘述者坐在一塊石頭上講述它的回憶,而故事的結尾女主人公伊莎貝爾悲憤地化為了一塊石頭,而這塊石頭正是開頭所提及的石頭,這種首尾呼應的情節宣告了小說的結束,然而小說中的故事,未來的回憶卻并沒有結束:
“我是伊莎貝爾·蒙卡達,馬丁·蒙卡達和安娜·古埃達拉的女兒,于1907年十二月一日出生在伊思特佩克。于1927年十月五日在葛萊高莉婭·胡亞雷斯眼前變成了石頭……我將一直孤單的在這里,跟我的愛一起,作為未來一個又一個世紀的回憶存在著。”(317)
由此看見,小說的最后伊莎貝爾成為了新的回憶敘述者,而她自己的經歷就是未來一個又一個世紀的回憶,每一次的敘述就是一個新的輪回。加羅以這樣的結尾告訴我們對于伊思特佩克,甚至對于整個墨西哥來說,時間是循環的,客觀時間雖一直前進,社會的悲劇現實卻始終持續著,沒有任何改變,這也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了小說的標題——未來的回憶與過去的回憶并無區別。或許加羅在這部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中給我們指明的墨西哥最大的現實就是從來沒有進步,革命爆發了一場接一場,統治者換了一代接一代,卻沒有實質的變化,殘酷的現實也依舊殘酷。
二、魔幻時間觀下的深刻現實
縱觀整個墨西哥文學史,從20世紀初開始就不斷涌現出以墨西哥革命及其后續運動為背景的小說,加羅的這部《未來的回憶》雖然也是以這一時期的歷史事件為背景的創作,卻與它之前大量涌現的所謂墨西哥革命小說不同,后者的創作手法屬于19世紀后期開始流行于歐洲的傳統現實主義文學,而加羅在小說中運用的這些魔幻因素顯然已經跳出了這傳統現實主義的范疇,正如上文提及很多拉美文學研究者將加羅的很多作品均歸為魔幻現實主義作品,甚至有人提出《未來的回憶》可能是拉美文學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
實際上,就在《未來的回憶》出版的十多年前,古巴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向讀者和作家們提出了“神奇現實”這一概念,并指出通過這一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認知拉美的現實,傳統的歐洲模式并不適用于拉美這塊神奇的大陸。幾乎同一時間段,委內瑞拉作家烏斯拉爾·彼特里首次提出了“魔幻現實主義”這一術語。從這兩個名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不乏文學研究者試圖探索這二者之間的界限,但是對于更多人來說這兩個文學含義的精髓完全可視為相近甚至是相同。在這里我們不對這個爭議話題做進一步探討,因為至少對于《未來的回憶》而言,加羅所運用的處理現實的方式是“神奇現實”與“魔幻現實主義”所共同提倡與認可的。
眾所周知,無論是“神奇現實”或是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品,虛幻奇異的元素都是其至關重要的部分,也正是這些元素將它們與歐洲的傳統現實主義作品區分開來。然而這些元素并不就是作家憑空創造出來的,它們雖帶著魔幻的面具,卻是深深植根于拉美的印第安文化中的,它們或來源于印第安人的神話傳說,或是印第安人信仰的一部分,對于印第安人而言這就是現實。例如阿斯圖里亞斯的代表作《玉米人》中玉米人的形象實際就是取自瑪雅人的圣書《波波爾·烏》中造物主用玉米創造了人類的故事,對于瑪雅人而言,最初的人是由玉米造出來的這一點已成為了不可變更的事實。而卡彭鐵爾與烏斯拉爾·彼特里二人也均在自己的理論中強調了所謂神奇或是魔幻實際都脫離不了現實作為基礎,只不過這現實是拉美獨有的現實。在小說《人間王國》的序言中,卡彭鐵爾指出神奇是現實的一種變體,一種特有的揭露現實的方式,是對各個層次現實的豐富。[5]作為第一位提出用拉美的方式講述拉美現實的作家,卡彭鐵爾口中的現實自然是指拉美所特有的現實,是與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占據世界文化中心位置的歐洲現實所不同的現實。這種拉美現實包含了歐洲殖民者帶來的西方文化,也包括著本身就植根于這片土地的印第安民族的信仰。對于外部世界而言,這現實的印第安成分就是它神奇或是魔幻部分,然而對于拉美大陸的居民來說,卻只是他們所經歷的現實的一部分,它與歐洲文化的融合才構成了完整地拉美現實。因此,在其另外一篇文章中,卡彭提爾提到:“那些奇特的因素其實是日常的,一直都是。”[6]
與卡彭鐵爾的觀點一樣,烏斯拉爾·彼特里同樣認為拉美的現實包含著一些傳統西方概念的現實中所沒有的因素,而這些獨特因素構成的現實也應當使用一種與傳統歐洲模式不一樣的方法使之呈現出來。因此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中創新的部分并不在于大量的魔幻因素與神奇的想象,而是這種經過融合而形成的拉美現實和作品中呈現的感知這種現實的方式。他在一篇名為《魔幻現實主義》的文章中寫道:“(魔幻現實主義)不是一場想象力的游戲,而是一種忠實反映了當時還不被人所知的極其特殊的現實的現實主義,它相較于傳統文學顯得不同尋常。”[7]
不難發現《未來的回憶》的創作手法,加羅在其中對魔幻因素的運用與卡彭鐵爾和烏斯拉爾·彼特里關于拉美新文學的理解正相吻合,書中荒誕虛幻的因素在作者眼里,在拉美大陸的印第安人眼里只是拉美日常的一部分罷了,因而許多拉美新小說大師都拒絕將自己的作品歸為魔幻現實主義這一流派,比如馬爾克斯。而加羅也曾多次強調《未來的回憶》并不是所謂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在一次采訪中,她提到伊莎貝爾變成石頭這一情節時解釋道:“那是真實的,因為在格雷羅州有許多人變成了石頭。人們經常講述說:‘某某人狀況很糟糕,最終變成了一塊石頭’,我相信這話,但這并不是魔幻,這遠遠不止是魔幻。”[8]摒棄這些爭議,或許拉美學者烏特·賽伊德爾對于加羅的創作手法的評論是最合適的:“這是一種面對自身周圍的現實的一種眼光,一種態度,或是一種觀點,某種意義上說,她是用了文化融合這一術語定義了拉美現實。”[9]我們無從考證是不是在印第安人世界是否真的有人曾經變成了石頭,甚至大多數人并不相信這類事情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對于印第安人而言這就是他們的現實,而對于許多曾經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深受印第安文化影響的拉美人,比如加羅,選擇相信這些魔幻因素就是他們自己對于拉美現實的態度。這其實也正是魔幻現實主義的意義之所在,作家們的用意并不在于讓讀者去相信魔幻因素的真實性,而是試圖啟發讀者透過魔幻去感知現實,感知隱藏在克里奧約外殼之下的拉美獨特的現實。
簡言之,魔幻因素雖看似荒誕,卻實際是另一種真實,透過它我們更好的認識現實。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絕非是一場精美的純虛構的藝術創作,而是對現實更加深刻的揭露。
在《未來的回憶》中,魔幻因素的作用正如上文所提,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不被多數人所熟知的現實,它是墨西哥現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對眾所周知的官方歷史的補充。魔幻的時間觀貫穿了這部小說的始終,從小說的標題一直到結尾變成石頭的伊莎貝爾開始再次循環講述伊思特佩克的回憶,這里的魔幻時間觀并不像科幻小說中人物可以乘坐時光機來回穿梭一般,這里所謂的魔幻部分實際是人物的心理時間。在瑪雅人的神話傳說里,宇宙時間是無限循環的又是可以被打斷暫停的,他們把人類的時間及其語言記錄在交替出現的五個太陽的歷史里:水的太陽、土的太陽、火的太陽、風的太陽和我們的太陽,每一個太陽毀滅之時,這段太陽歷史就終止了,轉而進入下一個太陽歷史的輪回。因而在小說中的人物的心里,他們自己的時間也是這樣被切割成一段段而后又周而復始的。
伊思特佩克人通過對自身心理時間的控制時時刻刻向讀者傳達他們彼時的心理感受,而這心理感受的產生必然又是現實的反射。從小說的標題說起,伊思特佩克和它的居民會關于未來的回憶實際就是過去的和他們正經受的現實的一面鏡子:對于大部分人而言,我們期待未來,因為我們并不知道未來會怎么樣,而對于經歷了墨西哥革命以及后期一系列動亂的小城人民來說,他們曾經每一次燃起的希望都被無情的澆滅了,我們也曾看到他們在尼古拉斯的帶領下奮起反抗,試圖追隨“基督王”的腳步,將軍隊統治推翻,然而伴隨著失敗而來的是更加令人窒息的獨裁統治手段,至此伊思特佩克人心中僅剩下了悲哀與絕望,他們認清了殘酷的現實,這現實過去是這樣,當下是這樣,未來仍將是這樣。這現實也正是加羅想呈現給讀者的墨西哥現實,它比普通墨西哥革命小說中所反映的現實更加全面,也更加殘酷,因為她同時揭示了未來墨西哥的國家命運,人民命運——未來的現實。
而小說中其他部分出現的魔幻時間,同樣是每一次的運用都像一發有力的子彈再次有力地戳穿了現實。當胡莉婭與費利佩試圖逃走之時,時間靜止了,我們雖無從得知二人的下場,然而無論他們出逃成功與否,這一集體暫停心理時間的做法顯然都是對以羅薩斯將軍為首的軍政府無聲的抗議,是對他們殘暴統治的無視;而當尼古拉斯被關進監獄準備接受審判時,他和伊莎貝爾都斬斷了自己的過去,只剩下將來的回憶,此時過去的美好已經在當下和未來的殘酷面前失去了所有的光彩,只有絕望與無助還歷歷在目。
結 語
眾所周知,全面性與真實性是所有現實主義小說所追求的品質。小說畢竟與歷史不同,如果說教科書上的歷史是宏觀歷史,那么小說中所展現的現實就是一部部詳盡地微觀歷史。現實主義文學作品與很多其他形式的藝術作品存在的一條重要的意義在于它們幫助人們更好更全面地了解歷史,我們學到的歷史是經過歷史學家們高度精煉過的,大眾都認可的“官方歷史”。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很多時候“官方歷史”并不是歷史的全部,需要普通人民群眾的歷史去補充完善,這樣的“人民歷史”就是文學作品可以提供的微觀歷史了。《未來的回憶》是以上個世紀20年代墨西哥全國范圍爆發的一場聲勢甚為浩大的“基督戰爭”為背景的,彼時墨西哥大革命已經結束,早期的迪亞斯獨裁政府早已被推翻,資產階級開始掌權,然而一切是否真如官方歷史所述,獨裁制度早已滅亡,社會矛盾得到解決,墨西哥有了嶄新的形象,邁入了新的篇章?答案都在這部微觀歷史中,這里我們看到伊思特佩克人民始終生活在軍隊殘暴統治的陰影下;印第安人會莫名失蹤,隔段日子被懸掛著出現在樹枝上;參加了基督戰爭的積極分子都被無情的處以極刑……小說中曾經提到法律是用來制裁背叛祖國者的,然而什么是背叛,又什么是祖國?“我們都知道祖國每六年就換一次姓氏”(268),所以背叛祖國實際就是違背統治者的意志,因為祖國是跟著統治者姓的。這些就是加羅給我們提供的微觀歷史,這就是現實。
魔幻現實主義歸根結底依然是現實主義,因而魔幻并不是作品的重點,它只是一種新的感知現實的方式,展現更加真實的微觀歷史才是這些作品的焦點,而魔幻的時間觀恰恰幫助加羅更加全方位地展現了現實。這現實披著風情萬種的魔幻外衣,實則拖著一具千瘡百孔的軀殼,觸目驚心,發人深省。當我們讀《未來的回憶》,我們聆聽伊思特佩克和它的居民講述他們的回憶,就是在聽一部近代墨西哥丑陋卻最真實的歷史和墨西哥人民艱難又絕望的抗爭史。而這未來的回憶并不是按照官方歷史發展的“官方時間”來講述的,而是按照講述者的心理時間線呈現在我們眼前,在我們進入他們的心理時間之時,我們也走進了他們的心理,走進了他們心里的現實。
注解【Notes】
①Garro, Elena, Los recuerdos del porvenir, Madrid, 451 Editores, 2011. p. 20. 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頁碼,不再一一做注。本文引用該小說的部分為筆者自譯。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Vargas Llosa, Mario. "lo mgico y lo maravilloso", en El País, 24/03/2007, pgina cultura.
[2] Vargas Llosa, Mario, "lo mgico y lo maravilloso", en El País, 24/03/2007, pgina cultura.
[5] Carpentier, Alejo, El reino de este mundo, Barcelona, Seix Barral, 2012, pp. 7-8.
[6] Carpentier, Alejo, "Lo barroco y lo real maravilloso", en Ensayos, La Habana, Editorial Letras Cubanas, 1984, p. 122.
[7] Uslar Pietri, Arturo, "Realismo mgico", en Godos, insurgentes y visionarios, Barcelona, Seix Barral, 1986, p. 138.
[8] Ramírez, Luis Enrique, La ingobernable. Encuentros y desencuentros con Elena Garro, México, Raya en el Agua, 2000, p. 28.
[9] Seydel, Ute, Narrar historia(s): La f ccionalizació n de temas histó ricos por las escritores mexicanas Elena Garro, Rosa Beltrn y Carmen Boullosa, Madrid, Iberoamericana, 2007, pp. 207-208.
Title: Future in Memories and Reality in Magic: the Magical Time Concept in Los recuerdos del porvenir
Author: Yang Li is from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Mexican female writer Elena Garro is one of the writers who started to innovate traditional novels f rst before the literary boom of Latin America. Magical realism marks most of her works off the traditional ones gives them lots of literary value, although these works are not so well-known as the ones created by those great magical realism writers. Los recuerdos del porvenir (Memories of the future) is a classic magical realism novel, in which Garro uses a lot of magical elements to show us a real Mexican society after the Revolution. This paper will mainly analyze the magical time concept demonstrated by Garro in this novel and investigate the way the writer tell the story with the magical time concept and its effect 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reality.
Los recuerdos del porvenir Magical realism Time
楊力,安徽大學外語學院,研究方向為拉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