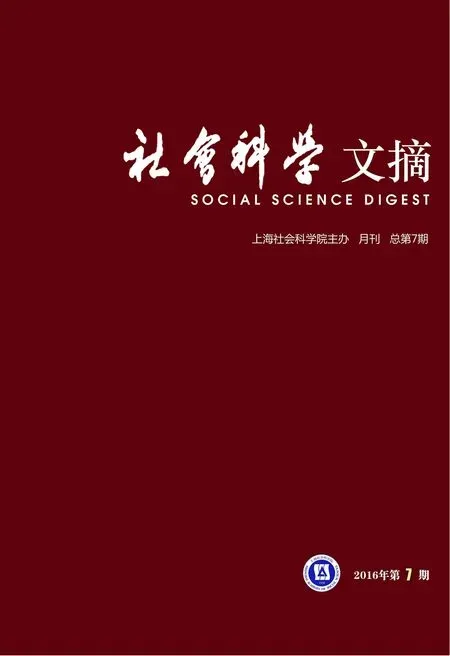“新泛突厥主義”運動及中國意識形態安全:挑戰與應對
文/侯艾君
“新泛突厥主義”運動及中國意識形態安全:挑戰與應對
文/侯艾君
近年來,在中亞、高加索、俄羅斯的某些地區,泛突厥主義作為主導性意識形態之一,其影響不斷擴大,是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相對于1991年后迅速高漲、其后一度沉寂的泛突厥主義來說,新一輪現象或可稱為“新泛突厥主義”。“新泛突厥主義”進程大致從2007年土耳其“正義發展黨”再度執政并推行所謂“新奧斯曼主義”政策開始,而泛突厥主義正是“新奧斯曼主義”意識形態兼容的部分,獲得新動力。土耳其政治家用“新奧斯曼主義”來凝聚國民、自我擴張,在爭奪中亞、高加索的“大牌局”中獲得地緣文明、地緣政治優勢。與之前時期相比,土耳其推行該政策更積極、明確;與中亞、高加索相關各國互動更頻,中亞、高加索各國積極配合,合作水平提升;突厥語國家初步具備了機制化的合作平臺。
在中亞,新泛突厥主義與其他地緣文明形成復雜互動,而中亞與中國國家安全緊密相關;泛突厥主義也給中國帶來意識形態—文化挑戰,甚至安全威脅。因此,必須深入觀察其動態和趨勢,并積極應對。
“泛突厥主義”:發展階段及其特點再審視
泛突厥主義是19世紀中后期出現的政治意識形態,同時也是一場社會政治運動,其宗旨是所有突厥語族聯合起來(往往與泛伊斯蘭主義思潮合流)。迄今為止,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
第一,泛突厥主義思想及運動是帝國主義征服的產物,是一種反抗的意識形態。泛突厥主義本身是突厥語民族為了對抗西方殖民征服而產生的一種思想,同時也是一種國際政治現象。在帝國主義時代,這種思潮具有積極意義,表明東方民族在政治上走向覺醒,有利于對抗西方列強對東方民族的殖民征服,推動東方民族建立現代民族國家。
第二,作為一種政治能量,泛突厥主義在興起后既用于民族解放,同時也具有一定的攻擊性、排他性。在19世紀英、俄爭奪高加索、中亞地區的過程中,泛突厥主義往往被西方挑唆,用于打擊俄國。西方既將俄國作為對手、也將土耳其視為東方異類,積極瓜分土耳其帝國的遺產,因此樂于挑動土耳其與俄羅斯的爭奪,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而泛突厥主義就是很好的杠桿,堪稱是西方對俄羅斯植入的政治病毒。當英、俄爭奪中亞的“大牌局”結束,中亞和高加索的突厥語族都成為蘇聯的民族,泛突厥主義思潮受到壓制。
第三,在“冷戰”時期,西方將泛突厥主義視為對蘇“冷戰”的意識形態武器。“冷戰”開始后,土耳其的戰略地位上升,成為美國的軍事盟友和北約成員國,與蘇聯對抗。西方試圖借泛突厥主義來肢解蘇聯。相應地,泛突厥主義在蘇聯始終是政治禁區,蘇聯政府竭力弱化突厥語族,將其分而治之。打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泛突厥主義者”,是蘇聯歷次政治清洗的重要內容。
另一方面,在1940年代,斯大林也曾策略性地利用泛突厥主義,推動中國新疆的民族分裂勢力,只是由于中國國內形勢迅速變化,蘇聯與美、英共同以犧牲中國在外蒙古的利益作為交換,蘇聯最終放棄了對分裂運動的支持。
第四,1991年蘇聯解體后,對抗泛突厥主義的堡壘消失,中亞出現了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真空。土耳其的雄心膨脹,立即與五個突厥語國家建立關系,定期召開會議,推動泛突厥主義運動。經過一段時間,該進程走向低迷。原因是:土耳其經濟實力不足以支撐其地緣政治構想,中亞國家看到,土耳其的經濟實力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強大;土耳其在中亞遭到俄羅斯、伊朗等國抵制;中亞國家從自身利益考慮,外交方針發生變化;2005年后,“顏色革命”導致中亞國家與西方關系惡化,而土耳其站在西方一邊,希望借“顏色革命”將“親俄”領導人替換,引起反感。
“新泛突厥主義”:“新奧斯曼主義”的支柱
從2007年開始,土耳其推動新一輪泛突厥主義。標志性事件是“正義發展黨”在土耳其執政,確立了“新奧斯曼主義”政策——而泛突厥主義正是新奧斯曼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艾哈邁德·達武特奧盧曾撰寫《深層戰略》,分析了土耳其的地緣政治利益,強調土耳其必須加強在巴爾干、近東和北非的政治、經濟和外交作用,積極運用軟實力工具(經濟援助和文化滲透)。土耳其精英強調了奧斯曼主義、伊斯蘭主義、突厥主義三種戰略思想成分:突厥主義是保存民族自我意識的主要思想,借以引導突厥語族走向奧斯曼主義。
首先,“新奧斯曼主義”思想是土耳其國內政治發展的結果,也與西亞乃至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變化有關。土耳其因塞浦路斯問題、庫爾德人問題等,到2007年仍舊未能加入歐盟。土耳其國內的西化派精英地位下降,主張歐亞主義、民族主義的派別上升。民眾認為土耳其多年來為西方提供軍事基地,服務于西方的經濟—政治利益,卻未得到接納,因而感到失望、怨憤。在東方的拓展可能成為土耳其對西方外交的籌碼,土耳其還希望利用自己的優越位置,使東西方各國都依賴土耳其。
其次,新奧斯曼主義是美國植入的意識形態。土耳其“正義發展黨”得到美國支持,“新奧斯曼主義”與美國的“大近東”方略契合。美國希望借此軟化土耳其國內的民族主義和凱末爾主義的力量,平衡伊朗。“新奧斯曼主義”體現了土耳其精英的“帝國思維”——對土耳其帝國時代記憶的重新喚醒,同時也是土耳其精英應對新局勢的地緣政治觀念。“新奧斯曼主義”乃是總綱,而“新泛突厥主義”是其分支。
“正義發展黨”對青年進行某種奧斯曼精神的灌輸。通過加強經濟、政治、文化存在,提高土耳其在阿拉伯國家中的地位,擴大勢力范圍,積極介入和干預相關國家,土耳其宣揚的“與鄰國零糾紛”政策已經破產。2009年中國新疆爆發“7·5”事件后,土耳其迅速表態指責中國政府,儼然是突厥語族的保護者;“阿拉伯之春”之后,土耳其立即表示歡迎,強力介入敘利亞問題。2011年,埃爾多安前往埃及訪問,數千名“穆斯林兄弟會”支持者夾道歡迎,視其為穆斯林世界的領袖。土耳其至今未能就歷史問題與亞美尼亞和解,與阿塞拜疆的緊密關系也導致土—亞關系正常化緩慢;支持波斯尼亞的穆斯林,承認科索沃獨立。
土耳其的多數政黨都支持泛突厥主義,其國內有非常廣泛、堅實的社會—政治基礎,并得到許多知識分子認同,他們炮制歷史神話,為泛突厥主義提供材料,成為土耳其外交的重要推動力量,對中亞、高加索國家的影響很大。
泛突厥主義者試圖將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吉爾吉斯人、土庫曼人等突厥語族都變成土耳其人,將突厥語族的民族語言在土耳其語的基礎上進行改造,變成通用語言,用土耳其認同取代民族國家認同。
土耳其是泛突厥主義活動的資助者、召集人。進入21世紀以來,土耳其與突厥語國家的合作機制是突厥語國家峰會。2009年10月2-3日,在阿塞拜疆召開第十次峰會,成立突厥國家合作理事會(或稱突厥委員會),總部設在伊斯坦布爾,并通過了憲章。阿塞拜疆是泛突厥主義運動的支柱,更是土耳其在高加索的地緣政治支柱。在中亞,由于土耳其與烏茲別克斯坦的關系不再緊密,哈薩克斯坦成為泛突厥主義的支柱。
中亞各國與“新泛突厥主義”
中亞國家響應新泛突厥主義,既出于語言、文化的親緣性,也有經濟需求——希望獲得土耳其的資金和技術;土耳其模式是參考范例,也是意識形態資源,更是外交選項,是平衡其他大國的力量。同時,土耳其與中亞的合作已具有戰略性質,取得很大進展,而泛突厥主義滲透在幫助土耳其推進對中亞政策方面獲得巨大優勢。
第一,中亞國家的政界和學界乃至普通國民都有支持泛突厥主義的基礎。哈薩克斯坦的“阿拉什”、烏茲別克斯坦的“比爾利克”、吉爾吉斯的“埃爾克”、“阿薩巴”等政黨對泛突厥主義思想很感興趣。
一些學術精英試圖論證突厥人的共同歷史、文化遺產等。如烏國學者運用歷史語言比較法研究二十四史等中國古代文獻,得出結論:從中國的《詩經》時代甚至更早,中國文獻記載的許多周邊部落和民族都是突厥人,證明突厥人有古老歷史。
第二,土耳其在中亞的存在是全方位的。通常認為,土耳其在中亞主要是一種經濟、文化存在,但也向政治領域滲透。土耳其與中亞國家合辦大量高級中學和大學,不少學生來自公檢法機關官員、知識分子家庭。這些學校除了教阿拉伯語、英語、土耳其語,還對學生灌輸泛突厥主義思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想。
土耳其與中亞國家也有軍事合作。中亞國家認為,土耳其作為北約成員國,裝備優良,軍隊訓練有素。土耳其希望中亞軍人赴土耳其培訓,確保中亞穩定,并培養軍界的親土人士。
土耳其為美國代言,積極推動吉爾吉斯與美國合作,甚至希望在吉國建立一個與美軍共管的基地。2014年6月美軍撤離吉爾吉斯后,土耳其加緊斡旋,呼吁吉國繼續與美國合作。
第三,哈薩克斯坦是新泛突厥主義運動在中亞的支柱,提高了該運動的分量,其他各國與土耳其的合作各有側重。沒有中亞大國哈薩克斯坦支持,泛突厥主義在中亞難有前景。哈國內許多以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者都有泛突厥主義傾向。納扎爾巴耶夫總統多次發表熱情洋溢的泛突厥主義言論。土庫曼斯坦多年來與土耳其關系緊密。不過,土庫曼作為永久中立國,無意與土耳其建立特殊關系。吉爾吉斯經濟相對困難、政治薄弱,容易認同泛突厥主義思想,為其敞開大門。
當然,突厥語國家距離政治一體化還有很多路要走。土耳其與高加索、中亞國家并不接壤;作為突厥語國家的核心,土耳其經濟還不夠強大;其發展模式能否被中亞國家效法仍舊存疑;對于合作目標,各國存在分歧。近年來,烏茲別克斯坦精英宣揚“烏茲別克斯坦模式”,哈薩克斯坦則宣揚“哈薩克斯坦模式”,顯示無意于照搬土耳其道路。此外,在突厥語國家加強合作的同時,也出現截然相反的逆進程——與土耳其保持距離。一些中亞人士擔心泛突厥主義滲透將導致中亞各族喪失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甚至土庫曼斯坦也發生微妙變化。新派觀點認為,土庫曼人的祖先不是奧古茲汗,而是與古安息國關系密切。新史觀首先表明自己的民族歷史更古老,否定了與土耳其人的種族親緣性。
在大眾心理層面,中亞國民與土耳其公民并不融洽。一些土耳其勞工與中亞當地人產生矛盾,引起當地居民反感。哈國統計,多數違反《勞動法》的情形都發生在土耳其企業。
“新泛突厥主義”挑戰及其應對
對于泛突厥主義,應該將源自歷史—文化親緣性的交流與擴張性運動加以區分。從語言、宗教和文化的親緣性出發,進而希望走近并加強聯系和合作,是可以理解的,其他國家并無反對的理由。但是,一些狂熱泛突厥主義者的目標始終是實現所有突厥語族(包括沒有獨立建國的族群)聯合,具有意識形態乃至地緣政治擴張性。土耳其推行了并非和平的外交政策,因而理所當然地遭到相關國家的警惕和抵制。
第一,我國曾是狂熱泛突厥主義的受害者。現實中,泛突厥主義主要構成文化—意識形態挑戰,導致我國突厥語族群的國族認同弱化甚至被蠶食、歪曲(突厥人認同、乃至宗教認同優先于國族認同),尤其對我國新疆的民族和諧、社會政治穩定構成意識形態挑戰和威脅。我國特定族群的人士會將中亞某鄰國作為祖國;將其領導人視為民族領袖;族群認同超越了對國家的感情,而國家認同薄弱。與泛突厥主義伴生的,往往會出現地方民族主義、甚或民族沙文主義,排斥和仇視其他族群,破壞社會政治穩定。
第二,土耳其國內始終有中國新疆分裂組織的重要背景。民族分裂勢力在西方和土耳其得到庇護和政治、財政、意識形態支持,土耳其的民間,甚至官方組織為其提供各種物質和資金。
第三,中亞國家有近60萬維吾爾族人。受泛突厥主義影響,一些人對土耳其有親近感,對中國懷有敵意,同情新疆分裂勢力。土耳其國內也有不少維吾爾族人,對中國抱有敵意和成見,影響政府政策。
第四,如果把泛突厥主義合作視為土耳其主導的一體化進程,對我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構想形成競爭。
近年來,土耳其與我國有良好的經貿合作,兩國貿易額逐年增長,2010年10月,兩國上升為戰略合作關系。這樣的良好關系來之不易,值得珍惜;經過各方努力,土耳其政府已對“疆獨”問題的政策有所調整,這些進展值得肯定。但是,對于泛突厥主義運動應該有清醒認識,并積極應對。
首先,應該完善并重建意識形態,強化我國突厥語族群的國族認同,解決好我國內部的社會—經濟和社會—政治問題。我國的突厥語族可以成為中國與土耳其友好合作的紐帶,而不是用來損害中國利益的手段。土耳其應該認識到,突厥語民族和國家的合作,應該以尊重他國的主權—領土完整為前提,否則只會引起對抗和沖突,損害土耳其自身。
在高加索、中亞地區,也都有對抗泛突厥主義進程的因素。例如,亞美尼亞和塔吉克斯坦反對泛突厥主義,俄羅斯、伊朗等國都對泛突厥主義保持警惕。俄羅斯在防范土耳其擴張方面已有舉措;伊朗也不樂見土耳其在毗鄰的中亞、高加索地區占主導性影響。
其次,學術界應該對泛突厥主義加強研究,揭穿以學術面目出現的泛突厥主義滲透。土耳其和中亞、高加索國家的史學家、政治精英論證的突厥語族的共同起源往往都是政治神話,缺乏學理依據。突厥語族之間多半并無種族方面的親緣性。所有突厥語族的族源都非常復雜,與古代突厥人并無直接關系。
最后,應該對泛突厥主義狂熱予以回擊。中國應該加強研究1915年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事件,并重新審視我國在該問題上的立場。土耳其對歷史問題的否認態度損害了其自身形象,妨礙其與相關國家關系的正常化。我國應在非官方立場上,就1915年大屠殺問題對亞美尼亞表示同情和支持。首先,這是出于道義考慮。中華民族也曾苦難深重,而日本政府與土耳其在相關問題上的態度相似。其次,我國利益向高加索延伸,亞美尼亞有一定的資源稟賦和科技潛力,且對華友好,對我國的意義繼續上升。美國有150多萬亞美尼亞族裔,中國的立場將使亞美尼亞裔成為友華力量。最后,在對抗泛突厥主義侵襲方面,我國和亞美尼亞有共同利益。就1915年大屠殺問題,我國應該加強與亞美尼亞科研機構的合作。我們當然珍視與土耳其的友好關系,應該保持對土耳其外交的靈活性。而作為“歷史牌”,1915年事件乃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儲備武器。如果土耳其政府在支持“疆獨”方面走得很遠,就可以用來敲打和牽制該國的狂熱政客,迫其改正錯誤做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摘自《國際安全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