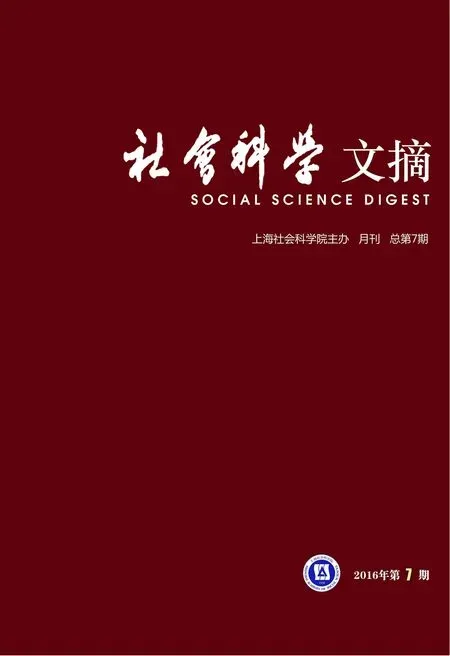“被裹挾的國家”與基層治理困境
文/田雄 鄭家昊
“被裹挾的國家”與基層治理困境
文/田雄 鄭家昊
中國30多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使GDP增長成了衡量地方領導政績的主要指標,這種“晉升錦標賽”模式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領導的積極性,但也使一些地方付出了極大的生態成本。而大氣污染成了最直觀、最顯著的民生問題,如何應對生態危機成為執政黨推進國家治理的重大目標之一。與此同時,隨著鄉村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原本用作燃料飼料的秸稈如今卻被農民原地焚燒,產生大量煙霧。為此,在生態治理的政治任務要求下,環保部將秸稈焚燒納入衛星監測范圍,地方政府把禁燒作為每年“毫不松懈、全力以赴”、確保必須打贏的“硬仗”。
國家、農民與基層干部的行動邏輯
筆者認為,在愈發強調執政黨的執政環境和“國家主導的社會治理”的話語背景下,快速轉型時期的國家與社會關系需要在動態的事實中進一步把握。本文以長三角區域的黃江縣秸稈禁燒為例,將米格代爾的“國家人類學”視角與肖瑛“制度與生活”視角相結合,“進入具體的制度實踐,以事件為中心”,除普通民眾外,把國家及其縣級以下基層代理人作為行動者納入社會當中分析,考察他們對國家及其官僚體系運作的影響很有必要。對中國社會來說,縣及以下正是國家官僚體系等級最底部的公務人員的集聚區,也是國家與社會、公務人員與普通民眾參與互動的耦合重疊領域。環保部、省和市將秸稈禁燒重任逐級轉包給縣級政府,黃江縣則通過集體動員、層層分解任務、精細設計考核指標和抓過程監督等舉措重新進行打包,共同組成了為滿足“合法性和效率”目的的高壓網絡。基層官僚組織和基層干部在高壓下如臨大敵,惟有直面農民,通過各種方式完成禁燒任務。
黃江縣利用電視、手機短信等現代傳播手段,發傳單、巡邏隊到村宣傳等傳統手段,以及衛星監控,還有省、市、縣督查組流動督查,基層三級干部駐村現場查看等手段來落實任務。在高度組織和全方位監控下的鄉村社會實施秸稈禁燒,卻遭遇了農民多種策略性抵制。在整個組織運作體系當中,上級組織和官員以官僚科層制為基礎,以自上而下的精細化考核和過程監控為手段,層層下壓,但官僚制體系內每個層級和個體都有自己的行動邏輯。因為基層干部大都生長于農村,在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生活世界,熟稔鄉村社會的各類規則,這些認知促使他們對禁燒政策產生質疑。處于上級和農民夾縫中的他們明知每年投入超過2000萬元禁燒經費也難以奏效,但為了對上負責和應付考核不得不勉力為之,同時,他們又要竭力避免激化與農民之間的矛盾,為此他們必須小心翼翼地協調和平衡這種復雜關系,努力采取“軟硬兼施”的政策執行方式。
“被裹挾的國家”狀態與成因
從國家、基層干部與農民各自的行動邏輯可以看出,在工業化和城鎮化推動下,鄉村社會急劇變動,國家與農民之間嬗變、疏離的關系狀態使基層干部缺乏權威性和號召力,也使基層實際難以自下而上地反饋到官僚體系的頂層。在官僚組織體系內,明知政策低效卻要求全力以赴的做法使處于夾縫中的基層干部甚至對治理體制產生了質疑,因此站在農民立場或者與其達成某種妥協。在官僚組織體系外,禁燒政策導致農民對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頗有怨言。國家雖以生態治理為目的,但禁燒政策與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轉型并不一致,雙方自然產生了目標和現實的沖突。表面上看最后仍是原地焚燒的農民是贏家,但全縣每年耗費的巨資其實還是源于各類稅收,這既沒有使公共財政資金逐步積累,又沒有增加鄉村和農民的公共福利,也沒有達到生態治理的目標,最終只是一個多方俱傷、沒有贏家的事實。
農民及其構成的鄉村社會是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政策執行的土壤。基于鄉村社會的錯綜復雜,基層干部不可能完全按照正式權力要求執行政策,因而,正式與非正式的權力相互依賴、并行運作成為“帝國治理邏輯”的重要特征,也符合當下的事實。然而,盡管非正式權力運用受到上級默許,但面對來自官僚體系自上而下的內在壓力,更有鄉村社會自下而上的普通民眾外在抵制的事實,基層干部既是國家基層治理的主體,又是國家和鄉村社會重疊區域的行動者,他們在個體層面被鄉村社會的各種關系網絡包裹并制約著,甚至是挾持,導致自身難以逃脫或有力反抗,不可能完全按照上級要求執行政策。這種包裹和挾持的普遍性力量進而上傳至基層政府,使相關政策制定和實施受到制約,最終形成了基層政府被“裹挾”的狀態。面對這種困境,基層政府希望通過整合官僚體系內部資源,以“運動式治理”手段快速達到規制目的,但因基層干部無奈且理性的心態使官僚體系底部出現了動搖,進一步導致基層“運動式治理更多地考慮政府本身的有效性,而非社會有效性”。
受“國家人類學”視角和“制度與生活”視角的啟示,筆者提出的“被裹挾”狀態只是對國家與鄉村社會關系的嘗試性判斷,其具體含義是指國家在基層治理過程中,基層干部作為政策執行的主體,被所處的鄉村社會中的情感、地方知識和利益關系所形成的復雜細密的網絡所制約。也就是說,普通民眾對執行政策的基層干部和認為對自身不利的國家政策形成抵制力量,進而施壓并影響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被普通民眾外在的各種抵制策略和基層干部內在的消解行為所共同形成的反作用力“包裹和挾持”。換言之,基層鄉村社會力量對國家政策設計的抵制以及國家對基層社會的妥協更改了政策原來的目標和作用方式,甚至可能還會改變國家性質。這種自下而上的反作用力向上逐漸傳遞,迫使國家投入更多資源去應對卻難以壓制和主導,反而形成了被裹挾的狀態。黃江縣秸稈禁燒的多方俱傷、沒有贏家的“低效治理”是國家被具有自主性的鄉村社會所裹挾的結果,而“被裹挾的國家”狀態則是“低效治理”的成因之一。不可否認的是,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體制優越性的國家仍然有強大的組織動員和壓制能力,但基層政府的“運動式治理”手段是上級任務下壓和普通民眾反作用后在基層的一種被迫選擇。這種選擇應是上級政府默許甚至是支持的,代表上級做了“不易做、不便做”的工作。顯然,無論是“運動式治理”,還是“行政發包制”、“官民分治”和“集權與分權”,都無法忽視這種常識性事實。諸如官員之間的“共謀”,商人“圍獵”國家公務人員形成公權尋租,垃圾焚燒廠選址引起民眾抵制,農民“要挾型上訪”促使基層政府花錢維穩,利用網絡媒體影響司法審判的“唐慧案”等等,這些大量的具體事件中或許都可以看到的是,官僚體系中的個體、基層政府以及國家被社會逐漸裹挾的狀態和結果正在形成。
國家“被裹挾”狀態何以去除?
一般而言,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三個基本問題: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在理想意義上,“治理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但在秸稈禁燒類似的政策中,多個主體之間并沒有以良性合作的正式制度共同致力于其中,最終呈現出了國家難以主導鄉村社會,而被鄉村社會所裹挾的狀態,這種狀態的形成進一步導致國家基層治理成本的加大和自身政治權威的流失。秸稈由飼料肥料成為“無用之物”,這些變化是國家以高度集中的權力作為推動社會經濟改造與發展的強大杠桿后的結果。國家推動了鄉村社會的發展,其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又轉而影響國家的治理職能和治理手段。國家以高度組織化的官僚體系來應對發展中出現的秸稈處理等問題,希望通過系統內部的強力動員和層層管控來支配復雜變動的鄉村社會,但在自身治理理念、體制和方式未能改進的情況下,自上而下的體系內部高度分化,也沒有將更多的治理資源投入到技術改進和惠企惠農的政策完善上,因而,國家動員和管控的范圍自然是有限的,最終陷入了“強發展”與“弱治理”的困境。
國家作為組織制度的宏觀抽象體系,其相對于快速而深刻變革的社會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又因為以各自利益為中心的社會個體的關系形成在客觀上使社會具有了自主性的力量,可以與國家相抗衡,形成了強大而分散的去中心化的力量和國家“被裹挾”的狀態。二者必然會產生不協調不一致,甚至是沖突。當然,不可否認國家對社會強大的建構作用,但這種建構也往往是基于社會既有的現狀而做出的后續反應。國家因社會需要而產生新的職能,但靜態而僵化的官僚體系與變動的社會不相適應,國家權力執行方式也難以發生根本性變革。
當前國家治理的鄉村社會基礎已發生了深刻嬗變,國家官僚制體系的內部以及治理對象已高度分化或關系復雜化,以官僚科層制為主的國家治理體系并沒有完全適應和做出合理反映,仍依賴于傳統的動員和強制模式來應對,導致非常態的“運動式治理”常態化。國家治理體系中各個層級的主體因有各自不同的價值取向和行動邏輯,自上而下的政策執行和自下而上地反饋遭受著民眾的消解和抵制,這又進一步強化了“強動員、低成效”手段的運用。因而,正視鄉村社會自主性力量,增強國家自身權威性和公共政策設置的科學性,提高權力運行的公開透明,有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自身改革,這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不可回避的重要改革導向。
(田雄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鄭家昊系陜西師范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摘自《公共管理學報》2016年第2期;原題為《被裹挾的國家:基層治理的行動邏輯與鄉村自主——以黃江縣“秸稈禁燒”事件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