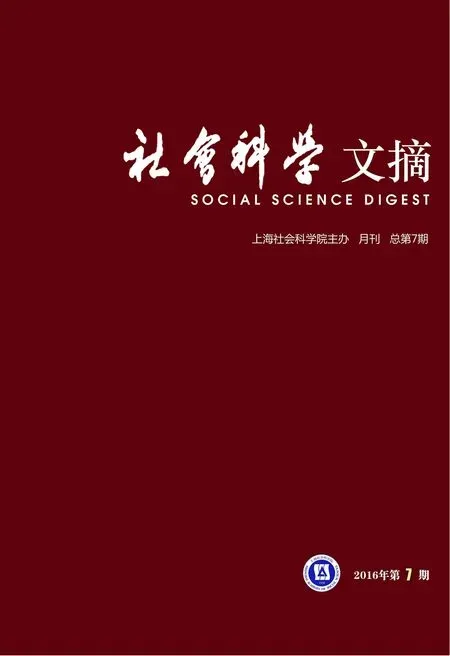約翰·奧尼爾及其“野性社會學”
文/孫飛宇
約翰·奧尼爾及其“野性社會學”
文/孫飛宇
在關于當代西方社會理論的權威敘事例如《布萊克維爾社會理論指南》中,約翰·奧尼爾(John O’Neill)作為兩個傳統的交集而頗為引人矚目。一方面,他被視為現象學社會學傳統之中在舒茨(Alfred Schütz)與古爾維奇(A. Gurwitsch)之后的新代表;另外一方面,他又因為《身體五態》以及《溝通性身體》等代表作品,而被視為身體理論的開創者之一。不過,這兩種對于奧尼爾之研究的“權威界定”可能都忽略了其學術工作的真正起點與內在理路。
就其工作而言,奧尼爾的翻譯、編輯和寫作等工作所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梅洛·龐蒂的現象學,蒙田的散文寫作和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而他對于時代核心問題的把握與傳統的繼承發揚,主要體現在他對于北美社會科學整體轉向的敏銳感知與回應。作為一位真正意義上的“世紀老人”,奧尼爾親身經歷了以《美國社會學評論》和《美國社會學期刊》等代表性學術期刊在寫作體例與研究風格方面的巨大轉變,意識到了這一轉變所代表的巨大的現代性潮流,并借助于既有的經典理論資源及其發展來應對這一轉變,提出了野性社會學的鮮明主張。他堅持將自己的理論工作放置于更為廣泛的西方思想史傳統之中,堅持運用一種散文體的寫作風格,明確主張學術研究的目的要關心人類與社會疾苦,直面生活,反對方法論至上主義,同時將學術寫作視為一種在人類文明歷史中自有其傳統的文學藝術創作。
第一,奧尼爾將社會學研究視為一種文體。這種研究性文體,可以被看作某種呈現與提交、某種開始、某種照面。在提交的同時,需要關注提交的基礎。提交并不意味著對于作為其基礎的日常生活/生活世界的斷裂,盡管這同時必然意味著某種鄉愁(nostalgia)與理念的開始。然而,野性社會學的溫柔之處,就在于它會環顧四周,發現那些不言而喻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存在之現象。這是一種同時將自身安置于生活世界之中的、詩意的棲居——盡管這一棲居絕非意味著對于那些愛欲、憂愁以及苦難的無視,而是恰恰相反,置于世界之中,就意味著要用整體性的方式來看待事物本身,關注行動者的生死愛欲,恩義情仇,及其“建筑世界”(world-building)的過程。野性的社會學絕不愿意犧牲自己,而換回某種“合理的”、去身體化與去世界化的思考方式,因為后者盡管可能會獲得某些在現代性制度中的發展前景,然而卻往往對于最值得被注視之事件,熟視無睹。在這個意義上,奧尼爾所主張的野性社會學毋寧說就是社會學的應有之義。
第二,奧尼爾將野性社會學視為一種日常的自我培育而非僅僅是一門職業。日益科學化和專門化的社會學,要求其研究與研究者的日常生活嚴格區分。然而奧尼爾的主張恰好相反,要求作者本人與其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所以野性社會學既是一門關于自身的科學,同時又是一種自我培育的路徑。這一研究既關于其對象,也關于研究者自身,關乎他們共同的自由與解放。這是奧尼爾關于現象學社會學之方法的詩意宣稱。然而這是一種帶有危險的宣稱,因為方法打開/遮蔽了我們的眼睛,激發/形塑著我們的感知與激情,決定了我們所看到的是何種的世界。所以身處于現象學傳統之中的奧尼爾,力圖將現象學社會學的眼光與視域拓展至政治、道德與社會等傳統大陸理論的領域。
第三,由此出發,野性社會學要求研究普通人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貼身(skin)” 之處。這一宣稱在思想史傳統之中有其根源。雖然奧尼爾明顯受到來自于梅洛·龐蒂與卡爾·馬克思的影響,不過阿爾弗雷德·舒茨以及加芬克爾對于日常生活的勘察,首先為奧尼爾的野性社會學提供了入手之處。奧尼爾希望可以從身體出發,來理解日常生活,進而重構對于社會和歷史的認知。這一工作的意義在于重返人類原初的能力,在社會機制乃至國家政策對于生命、性以及家庭的設計造成重大影響的當今時代里,試圖恢復人性的形態。
第四,野性社會學需要一種“身體性寫作”的實踐。這是奧尼爾在其工作的晚近時期的入手點與寫作視域。對于自身已然是一個自成一體的意義世界的日常生活來說,社會學研究與這一世界的遭遇天然面臨著闡述的問題。奧尼爾將世界看作是身體性的世界。這是一種整體性的無處不在(omnipresence),無法簡單地被科學化的目光在拉開一定距離的前提下注視。如果我們將社會學研究視為一種敘述,那么真正的敘述就不應該是空洞地去復述,而是靈魂的交談,是傾注于我們的棲居之處,并且以此方式來棲居。作為貼身行當的野性社會學,本身的研究與寫作恰好就是現代性緊張的體現。奧尼爾主張社會學需要除魅,需要以一種樸素直白的目光,在看待世界的同時,體會自己也身處其中的這個世界,需要以一種“照面”而非客體化的方式來寫作。而寫作就是與讀者的直接交流。這是現象學傳統之中的描述性“風格”。奧尼爾在其現象學的視域之中,所看到的不僅僅是知識,還有權力、交換、經濟以及愛欲,是整個世界的綻放與遮蔽,壓抑與反抗。這是對于生活世界概念的重大發展。
在奧尼爾對于作為貼身行當的野性社會學的研究中,代表性成果是《身體五態:重塑關系形貌》(Five Bodies:Refiguring Relationship)以及《溝通性身體:溝通性哲學、政治與社會學研究》。在這兩部作品中,奧尼爾提出要以“活生生的身體”為線索來理解生活世界以及人類社會,以“擬人論(anthropomorphism)實踐”為起點,討論了人類是如何通過身體來思考自然、社會與世界,以及其中的種種制度、歷史、家庭甚至是道德、政治與社會問題。社會科學如果想要徹底理解世界,那么這一對于身體的理解就要成為其根基,因為這種徹底的擬人論是日常生活之中常識的歷史性基礎,而這樣一種常識態度對于任何更高層面的人類統一體而言都是“一種至關重要的成就”。
第三,野性社會學對于社會學傳統本身也提出了挑戰。他并不否認經典三大家的殿堂地位,然而卻在同時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愿意從更廣泛的思想史傳統之中汲取自己的思考靈感與資源。從這一對于學術的理解和主張出發,在奧尼爾看來,在社會學的經典時代里,對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和理解最具有啟發性質的工作,乃是弗洛伊德的經典精神分析。所以,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奧尼爾經由梅洛·龐蒂而重返弗洛伊德的經典文本,尤其是他那五個重大的案例史。這一工作的成果,同時也是野性社會學的重大成就,就是他在2011年的新著《靈魂的家庭經濟學》(The Domestic Economy of the Soul)。他通過對于經典文本的精讀,首先將文本置于文本之中,也就是置于歷史、文化、社會與個人的生死愛欲之中去加以理解,同時將這一文本視為是一種作者與作者之間進行表達與理解的身體藝術;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將弗洛伊德所討論的主題與問題,以及弗洛伊德的治療與寫作工作本身,放置于歐洲思想史傳統之中來加以研究。最終,身體理論還要在其開掘者那里,在去蔽式寫作的同時被實踐著,或者說,在實踐的同時被“理論著”。
在其解讀之中,奧尼爾力圖構建起一套理解現代主體性的方法論框架。在這一關乎最為隱蔽的瑣屑平常之事的敘事行為里,奧尼爾開始融合尼采式哲學、精神分析、現象學社會學、結構主義人類學乃至神話學等,并將人類社會理論傳統之中的重大議題,如家庭、交換、契約、勞動等,都納入了對于這一經典工作的考察之中,同時既從思想史的傳統來加以研究,又將弗洛伊德及其患者放置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西方歷史中來進行研究。
奧尼爾這一作品的重要特點,就是同時既精讀文本,將討論的基礎嚴格限定在文本中,又能夠放開視域,以豐富浩瀚的知識與磅礴的氣勢打開在每一個案例的那些小小故事之中所潛藏的豐富的文化、歷史與社會性視域與意象,同時將其與社會與政治理論最為核心的問題結合在一起。奧尼爾這一研究主題的初衷,就是要通過研究“人成為人”的歷史,來解釋日常生活之中作為“在世之在”的那些宏大視域,以便獲得現代人與現代社會的深度知識。
在這本書中,奧尼爾顯露出了某種同時既生成結構又去結構的視域觀與成熟的表述方法。在這樣一種觀看之中,奧尼爾所看到的精神分析,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去/結構。在寫作中,奧尼爾發現了精神分析與西方文明史中某種雙重誕生之間的親和力:我們每一個人在母體(mother-body)之中的起源,以及“給予生命的欲望之起源”,這一欲望既有其生物性與身體性,又有其社會與文化性,簡言之,既有母親一般的性質(如同母親生育每一個“我們”),又有父親一般的特質(如同父親生育法律、藝術與科學這三位一體的自體/單性繁殖領域)。這兩種都堪稱單性繁殖(parthenogenesis)的幻想——奧尼爾相信這一單性繁殖的幻想居于弗洛伊德之工作的核心,同時也是理解棲居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西方文明的核心線索之一。
在這一關于懺悔者與生活世界的去/結構之中,分析師弗洛伊德首先成為了一位聽眾,然而這位聽眾,作為尼采意義上的歌隊成員,在聆聽的時候,也在闡釋。所有的案例史,在這一過程之中,都在成為一種體現出人類文明實質問題的深度理解社會學的同時,還兼具了對于現代社會學的深度反思。社會學到底是什么?社會學何為?在這個意義上,野性社會學不僅要求直面生活中的愛恨與苦難,還要求對于學科本身的屬性,從文明歷史變遷的宏大視野中加以理解。這是奧尼爾將社會學研究視為一種文體的深層意義所在。
(作者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摘自《山東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