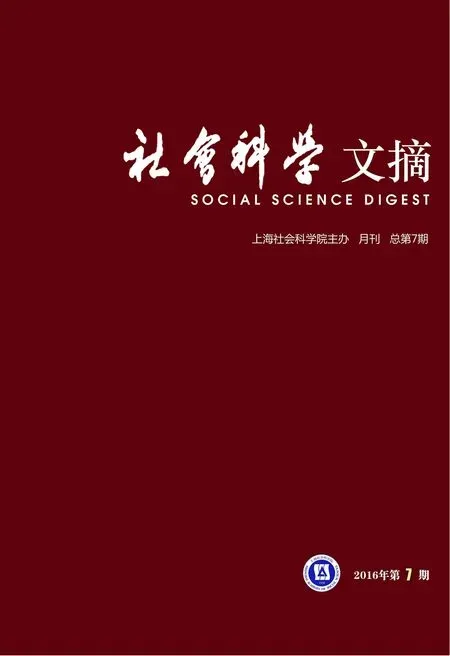憲法的法律性闡釋及證立
文/陳端洪
憲法的法律性闡釋及證立
文/陳端洪
憲法的法律性即憲法的規范性,和憲法的政治性對立,通常被分解為三個子命題:憲法是法律;憲法是根本法;憲法是最高的法律。不夸張地說,這三個命題已經成了現代立憲國公民宗教的教義。
“憲法的法律性”命題的了義包括兩個方面:(1)憲法效力的理由;(2)憲法權威的來源。兩個方面換一種方式來表述就是兩個問題:憲法為什么是有效力的?憲法為什么必須被尊崇甚至信仰?
憲法的法律性解析
(一)憲法是法律
當我們說憲法是法律的時候,我們的意思是:1.憲法具有法律的形式;2.憲法具有法律效力。
中國憲法序言宣告“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其中的“以法律的形式”包含這樣幾層意思:1.憲法是實定法、制定法;2.更確切地說,憲法具有一種特殊的法律形式,即真經大典;3.在否定的意義上排除了其他形式屬性,即是說,憲法不是協議,不是綱領,等等;4.進一步說,預設了制憲權的統一性。在上述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博爾納茲克說憲法轉變為一種“法律類型”是“當代政治文化的一個成就”了。拋開理論話語,在日常生活中成文化意味著憲法可以隨身攜帶、隨時取用。
美國詹姆斯·威爾遜指出,美國憲法之所以是政治科學的一個飛躍,不僅僅是因為它寫了什么還因為它是書寫出來的這個事實。
(二)憲法是根本法
根本法在16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的時候,算不上一個專門的術語或概念,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法。根本法在字面上包含一個隱喻:基礎——建筑,即把國家比喻為一個建筑,而把某些東西比喻為這個建筑的基礎,有時也用支柱的意象來表示。究竟什么才算是根本法?什么是非根本法呢?其實,根本法完全是一個松散而模糊的概念。絕對主權論者不給根本法留什么空間,主張主權者不受(實定)法律約束。
當歐洲人在圍繞根本法的理論問題爭執不休的時候,美洲一些殖民地已經把根本法這個詞當作文件名稱在使用了。1776年到1780年之間,美洲制定了11部憲法,均用憲法文本把根本法固定下來,1787美國憲法把根本法或高級法的觀念確定下來,首先體現在制憲會議的特別程序中。
在根本法作為概念確定下來成為標準說法之后到美洲各殖民地立憲之前,應該說根本法等于憲法。在美洲殖民地獨立立憲,特別是1787年美國聯邦立憲、1791年法國制憲以后,幾乎可以說憲法等于根本法。
(三)憲法是最高的法律
這個子命題包括兩層含義:憲法具有法律效力;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1.憲法具有法律效力
無論一國的憲法是否具有法典化形式,只要它是有實效的,它都具有法律效力。對于憲法,就像對于整個法律秩序一樣,效力以實效為前提。對于一般的法律規范而言,效力指向約束力和強制力。但對于憲法而言,其效力的根本體現在于,憲法是全部法律秩序及一切法律規范效力的源泉,是一切的強制力最終的唯一的合法性根據。憲法的根本功能是把權力事實轉化為法律主權,即把暴力轉化為法律權力,不僅使國家成為暴力的壟斷者,而且在觀念上把國家從一個暴力機器轉換成一個法律秩序。為此,憲法要具體地承載兩項功能,一是建構和賦權;二是限制權力。不過,憲政主義者更多地強調第二個功能。
2.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憲法至上的觀念在純粹法學上的涵義是,法律是一個內在和諧的規范等級體系,而憲法是這個體系的頂端,任何與憲法相悖的規范都不應該是有效力的。它還有政治的一面,即: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服從憲法,特別是立法機關。政府如果沒有憲法就成了一種無權利的權力。
憲法至上是國家主權對內的一種體現。即便在聯邦制下承認所謂的聯邦與州的雙主權,憲法至上也是中央或聯邦主權的標志。
如何看待“違憲的法律”?漢密爾頓主張,“違憲的立法自然不能使之生效”。作為一種政治論述,漢密爾頓的觀點影響深遠。然而,從純粹法律的觀點看,凱爾森認為,“違憲的法律”無效,是個沒有意義的陳述;“‘違憲的法律’這一表示的意思就是,根據憲法,一個法律可以因特殊理由以異常方式廢除”。此話反過來說就是:如果根據憲法,一個法律不可以因特殊理由以異常方式廢除,那么,“違憲的法律”要么自相矛盾,要么沒有意義。
凱爾森的困境:歷史上第一個憲法的效力只能依靠預設
憲法為什么是有效力的?憲法為什么必須被尊崇甚至被信仰?凱爾森的純粹法學試圖回答第一個問題,完全拋開了第二個問題。
何謂基礎規范?在1925年第一版的《一般國家學》中,凱爾森是這樣論述的:“法的層級秩序最終歸結于基礎規范,正是通過它,法秩序的自我創設運動才有堅實的根基,且不同層級的規范才能構成一個統一體。”
在《法與國家的一般原理》中,他試圖回答為什么憲法是有效力的。“這第一個憲法的效力是最后的預定、最終的假設,我們的法律秩序的全部規范的效力都依靠這一憲法的效力。人們假設一個人應當像制定第一個憲法的那個人或那些人所命令的那樣行為。這就是正在加以考慮的那個法律秩序的基礎規范。”《純粹法律理論》對歷史上的第一個憲法的描述得很具體,結論依然相同。“如果我們追問歷史上第一個憲法的效力理由,那答案只能是(不考慮“上帝”或自然的話)這個憲法的效力——即它是一個有效的規范——必須被預設……由于一個規范的效力理由只能是另一個規范,所以,這個預設也必然是一個規范。”
凱爾森指出:“基礎規范并不是由造法機關用法律程序創造的。它并不是像實在法律規范那樣由一個法律行為以一定方式創造的,所以才有效力。它之所以有效力是因為它是被預定為有效力的,而它之所以是被預定為有效力的,是因為如果沒有這一預定,個人的行為就無法被解釋為一個法律行為,尤其是創造規范的行為。”說到底,基礎規范僅僅是一個邏輯預設。
人民制憲,如是我聞
共和國憲法,以人民的第一人稱做出決斷,仿佛是人民自己在制憲。“人民—憲法”,這很像一個神學敘事結構。人民是誰?人民何時出場制憲了?人民制憲是一個偉大的神話還是一個善意的謊言?我嘗試在思維中構建,或者說還原人民制憲的場景。
(一)人民直接出場條件下的憲法
在主權者人民直接出場立法的時代,政府的創設以制憲為第一步,但在這里,憲法就是組織法,不具有最高法律的特殊地位,且需要在人民的每次集會上被審查,甚至可能予以廢除。今天我們所說的憲法都是某種代表制之下的憲法,它與盧梭的根本法有質的不同,要探討這種憲法緣何產生、何時產生以及如何產生,須得深入代表制民主的精神結構。
(二)從直接的人民主權到代表制民主的鴻溝
一旦人民不能再(經常)出場,政治體還如何存在?在人民直接出場的條件下,政治體的精神圖式為:主權者—政府—臣民。一旦人民不再(經常)出場,主權者不能(經常)行使主權,政治體的精神圖式就會蛻變為暴政結構:政府—臣民。在這個結構中,只有臣民,沒有公民;只有奴役,沒有自由。如何防止暴政?辦法有二:(1)把人民作為主權者供奉為神,高高在上,但人民不親臨統治,而由少數人代表其統治。于是,政治體的精神結構演化為:【主權者】—政府(代表)—臣民。(2)作為主權者意志的憲法登場。憲法作為人民的根本意志被尊奉為最高的法律,似乎它可以替代主權者出場。于是,政治體的精神結構增加了一個環節,變成:【主權者人民】—憲法—政府(日常代表)—臣民。
然而,人民是如何心甘情愿地被當作牌位供奉起來的?憲法由何而來?憑什么以人民的口吻言說?怎樣的憲法才能有效地控制代表者呢?
(三)最后的人民集會:從社會契約到神圣憲法的邏輯驛站
設想經過若干時間的人民直接出場的政治實踐后,由于諸多原因,公民大會往往湊不夠半數,很難舉行了。在這種情況下,假定在某個時刻,人民極不容易地舉行最后一次公民集會。在最后一次集會上,人民要決定未來的政治生存方式。我設想人民作出如下決議:“第一,全體人民構成一個政治民族,社會和國家是神圣的。第二,共同體一切權力屬于民族(人民)。人民主權不可轉移,不能被篡奪。第三,實行代表制。第四,人民作為人保留若干自然的自由,作為公民行使基本權利。第五,制憲。”
結語
最后的人民集會不是一個歷史事實,而是一個假設。這一點和凱爾森的基礎規范有某種相似性,但又有重大的差別,因為在最后的人民集會上做出的人民決議是有實質內容的,而不是純邏輯的。這絕不是說凱爾森的基礎規范過時了,更不是否定其意義,而是主張憲法學把基礎規范和制憲權理論對比互參,如此方得見識憲法之真面目。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清華法學》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