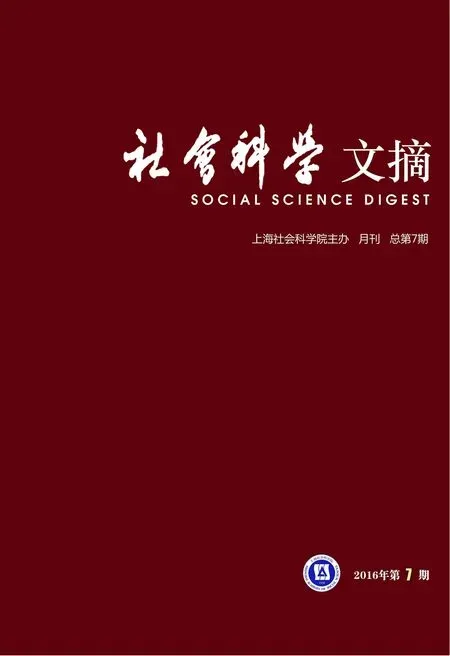作為哲學問題的“中國向何處去”
——理解馮契哲學思想的一個視角
文/童世駿
作為哲學問題的“中國向何處去”
——理解馮契哲學思想的一個視角
文/童世駿
馮契先生的工作可以用“三三三”來概括:研究真善美,融貫中西馬,連接往今來。“三三三”的最后一項,“連接往今來”也有三層意思:第一,他通過對以往哲學歷史的研究、與同輩哲學同行的討論為未來哲學發展留下“經得起讀的”(他對毛澤東和金岳霖著作的評價)的文本;第二,他繼承發揚其老師的學術傳統認真參與其所在的學術共同體的建設,悉心指導年輕學子的成長;第三,他立足李大釗所說的“今”,對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精神文化進行“述往事”而“思來者”。
因為馮契先生主張在“述往事”和“思來者”的基礎上“通其道”,“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在馮契開始其哲學生涯時被全國各界急切討論的社會問題,在追求“以道觀之”的智慧說當中,就成了一個哲學問題。
在其《智慧說三篇》導論中,馮契幾乎是一開頭就這么寫道:“真正的哲學都在回答時代的問題,要求表現時代精神。中國近代經歷了空前的民族災難和巨大的社會變革,‘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成了時代的中心問題。”
“中國向何處去”為什么是一個哲學問題,馮契自己提供了解釋,那是因為這個問題在思想文化領域中表現為“古今中西之爭”,而這個問題需要從歷史觀的角度,來回答如何看待社會歷史和把握歷史規律的問題,也需要從認識論的角度,來回答如何解決主觀愿望和客觀實際的關系問題、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問題,更需要把歷史觀和認識論結合起來,解決邏輯和方法論的問題、自由學說和價值論的問題。這里其實也體現了馮契“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的基本思想。
在我看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之所以是一個哲學問題,還可以進一步理解為,是因為馮契先生實際上是把這個問題也看作是“中國人向何處去”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正是他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特別重視的原因。
在抗戰期間閱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中,馮契說“最使我心悅誠服的,是在抗戰期間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新民主主義論》”。如果說《論持久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回答了“抗戰向何處去”,那么,《新民主主義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本著作對一百年來困擾著中國人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做了一個歷史的總結……”。
《新民主主義論》開篇就提出的這個問題,作者是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三方面加以回答的。盡管如此,這本書的重點是放在文化上的。這不僅因為該文的基礎是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隨后發表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而且是因為在我看來,就像對一個人來說,“做何事”“有何物”和“是何人”這三個人類最基本問題當中,“是何人”是最重要的問題一樣,對一個民族來說,“是何人”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政治涉及的是“做何事”的問題,因為它涉及集體行動的原則、方式和途徑;經濟涉及的是“有何物”的問題,因為它涉及物質資源的生產、流通和分配;而文化涉及的則是“是何人”的問題,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就是這個民族之成員的價值取向、知識水平和文明程度。毛澤東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
“是何人”的問題與康德的四大哲學問題(“我知道什么”“我應該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什么是人”)中的最后一個問題即“什么是人”這個哲學人類學問題顯然有密切關系,但我覺得,它與“我可以希望什么”這個宗教哲學問題也有密切關系,因為在中國文化這樣一個世俗化程度很高的語境當中,“我可以希望什么”更適合在價值論和歷史觀的范圍內加以回答。或者說,把“中國向何處去”理解為“中國人向何處去”加以回答,既預設了對“我可以希望什么”和“什么是人”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也會豐富對“我可以希望什么”“什么是人”這兩個問題的回答。
康德把“我可以希望什么”“什么是人”這兩個問題與認識論分開,而馮契則把類似的一個普遍的問題,“人能否獲得自由”或者“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當作廣義認識論的四個問題之一。在這里,馮契把一個看似屬于價值論的問題作為認識論問題來對待,似乎與有些西方哲學家近年來談論的“德性認識論”(virtue epistemology)比較接近;但在我看來,他不僅是要用價值論來豐富認識論討論,不僅是要討論認識過程中德性、價值和規范的重要性,而且是要讓對于價值觀(以及歷史觀)問題的討論,反過來受到認識論的影響,是要使得認識論當中對于理性的討論,對于客觀實在、主觀認識和概念范疇之間關系的討論,對于理論與實踐關系的討論等等,也影響對于真善美價值的討論,影響對于人的自由觀的討論,影響對于人的存在和本質的關系的討論、對人的內在性和超越性的關系的討論。確切些說,他是要在價值論和認識論的互動當中超越狹義價值論和狹義認識論的局限性,一方面克服價值論領域的虛無主義與獨斷主義之間的非此即彼,另一方面克服認識論領域的實證主義和神秘主義之間的非此即彼,從而對理想和現實的關系問題,對這個我覺得唯一真正具有“哲學基本問題”地位的哲學問題,做出恰當的回答。
價值論和認識論的結合,或者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價值論和認識論的結合,就是馮契看作是“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的最重要成果(沒有之一)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馮契提醒我們,“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這個概念,并不是在《矛盾論》《實踐論》這樣的更加典型而且更加出名的毛澤東哲學著作當中提出的,而是在《新民主主義論》當中提出來的。這可以說是馮契把《新民主主義論》作為哲學文本予以高度重視的最直接原因。在《智慧說三篇》導論中,馮契在說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是“站在哲學的高度”來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之后,緊接著就寫道:“他在這本著作中提出了‘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一詞,既概括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關于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的基本觀點,也概括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關系問題的基本觀點。所以,這個詞集中地體現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統一。這個概念把客觀過程的反映、主觀能動作用和革命實踐三個互相聯系的環節統一起來,而實踐則可說是主觀與客觀之間的橋梁。”
說到這里,我們或許可以把馮契先生和馮友蘭先生做一個比較。馮友蘭在其晚年完成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中,也討論了《新民主主義論》,也是把毛澤東這個文本當作一個哲學文本來討論的,但是沒有提到其中提出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這個全新的哲學概念。
再往前面看,馮友蘭在抗戰開始后不久寫了《新事論》一書,其副標題是“中國通往自由之路”,可以說也是在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但馮友蘭先生并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提高到認識論的角度來提出和回答問題,更沒有“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的高度。因此,該書雖然討論了許多關系問題,如共殊、城鄉、家國,等等,但就是沒有討論理想與現實的關系問題、客觀規律與主觀能動性的關系問題,尤其是知行關系、群己關系,以及自覺原則與自愿原則的關系問題。
從總結中國近現代革命的經驗教訓的角度來看,馮契對于“自覺”和“自愿”的討論,尤其值得重視。馮契強調真正自由的行動既要符合理性的自覺原則,也要符合意志的自愿原則。在他看來,重自覺原則而輕自愿原則,容易導致聽天由命的宿命主義,在中國文化中這種危險尤其值得警惕;而重自愿原則而輕自覺原則,則容易導致隨心所欲的意志主義,在西方文化中這種危險尤其值得警惕。馮契認同中國文化的理性傳統,但提出不但要防止“以理殺人”的獨斷主義,而且要防止因為克服獨斷主義而走向虛無主義,尤其要防止獨斷主義的唯我獨尊與虛無主義的沒有操守的獨特結合:拿獨斷主義嚇唬別人,拿虛無主義縱容自己。
馮契把“中國向何處去”作為一個哲學問題來討論,不僅是因為他把這個問題當作“中國人向何處去”的問題來討論,而且因為“中國”本身的重要性,而使他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具有歷史哲學的意義。“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某個國家某個民族向何處去的問題,因為古代中國是差不多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同時誕生的幾大“軸心文明”之一,也因為當今中國已經在經濟上位居世界第二,在政治上因為其發展道路的獨特性和有效性,而對全世界引起越來越強的反響。“中國向何處去”越來越意味著“世界向何處去”。
最后,把“中國向何處去”理解為一個哲學問題,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這個問題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哲學向何處去”。對這個問題,馮契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從哲學本身來看,也有一個古今中西的關系”,“與民族經濟將參與世界市場的方向相一致,中國哲學的發展方向是發揚民族特色而逐漸走向世界,將成為世界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方面,就像在其作為學者、教師、普通人的所有方面,馮契先生也是言行一致的。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他接待一批又一批來自國外和港臺的哲學家,創立中西哲學與文化比較研究會,承擔許多西方哲學博士論文的評審,主持西方哲學博士論文答辯,尤其是在其著述中,廣泛征引歐陸和英美各派哲學家的論著,利用中西哲學資源,對理性和意志、存在和本質、邏輯和歷史、內在性與超越性等世界性哲學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摘自《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