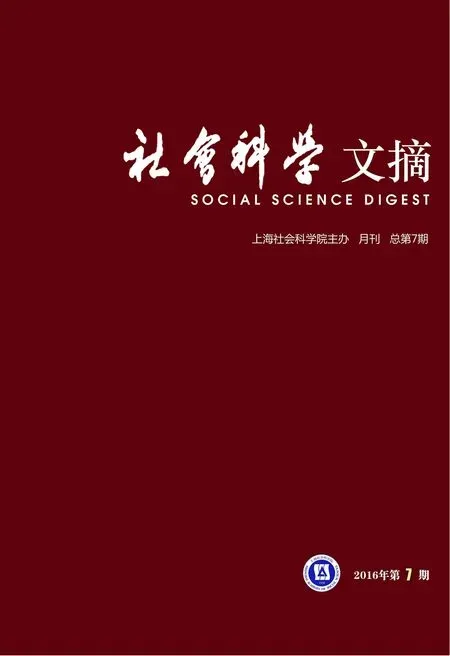論禮學脈絡與禮學史分期
文/田君
論禮學脈絡與禮學史分期
文/田君
從遠古殷商以“致敬鬼神”為核心的宗教之禮,到西周以“人文道德”為核心的“人文之禮”,周公“制禮作樂”是一大關鍵;從西周以“人文道德”為核心的“人文之禮”,到東周以“禮緣情而作”為核心的“觀念之禮”,孔子“克己復禮”是一大關鍵。西周“制禮作樂”實現從天道到人道的轉折,直接扭轉中國文化走向;東周禮樂思想,實現“禮”的學術化,深刻影響中國學術史與思想史。禮學在先秦已實現關鍵性變革,由秦漢迄于清代皆循其軌而有所發展。秦漢至隋唐的主體特征是“體制禮學”,宋明時期為“心性禮學”,清代為“禮學整合”。
遠古至殷商——“宗教之禮”
主體特征是“宗教之禮”。“禮”產生于文字之前,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根據現代考古學材料,與遠古祭禮相關的大規模禮器群、大型祭壇,考古多有發現。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也用事實證明,夏禮的真實存在。而商代的“宗教之禮”,更是走向極致,根據甲骨卜辭,商人為了取悅鬼神,舉行大規模祭祀,已經到了“佞神”的程度,經常使用活人祭祀。如果沿著商文化發展下去,中國一定會出現龐大的神權階層與真正意義上的宗教與神學。可是,歷史畢竟不能假設,從周代開始,中華文化實現重大轉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使得遠古至殷商的“宗教之禮”轉變為“人文之禮”,誠如《詩經》所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西周——“人文之禮”
主體特征是“人文之禮”,體現為“制禮作樂”。如此強大的“天邑商”,沉迷于祭祀活動,竟然傾刻覆滅,“小邦周”瞬得天下,雖然表面宣揚周得天命,實際內心卻是誠惶誠恐,高度警惕重蹈覆轍。“殷鑒不遠”,周人吸取殷商滅亡的歷史教訓,在很多方面反其道而行之,從而產生“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的觀念。天命無常,天佑有德,這是從“宗教之禮”向“人文之禮”轉變的思想根源。西周時期,以周公“制禮作樂”為標志,由鬼神之道轉向人道,認為“天道遠,人道邇”,實現從“宗教之禮”到“人文之禮”的轉變,并不斷加以鞏固,中華文化也從此大轉向,具有重大的歷史與文化意義。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認為,“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周公用以綱紀天下的宗旨,是要“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制作之本意,實在于此”,可謂一針見血。周人之禮,并非全部獨創,有不少借鑒殷商之禮的地方,但都不是簡單移用,而是巧妙地在殷人儀式中植入人文精神,宗教道德化,而這一切都蘊涵在“制禮作樂”的具體制度規定之中,潛移默化,誠如《樂記》所論“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東周——“觀念之禮”
主體特征是“觀念之禮”,“禮”走入理論之域,開始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歷史車輪行進到春秋戰國,社會發生巨大變革,這是從封邦建國的宗法制度,逐漸向專制中央集權制度過渡的歷史時期,社會階層流動加劇,原有等級秩序被打破,“禮壞樂崩”,是這一時期顯著的社會問題。由于西周建立的外部禮法遭到破壞,東周所提到的“禮”,開始向內發展,成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左傳》觸目皆是“禮也”、“非禮也”,對西周的“人文禮制”,進行理論探討,從而向“觀念之禮”深化發展。孔子提出“克己復禮為仁”,并不是主張完全照搬周禮,春秋戰國的社會現實不允許,這一點孔子當然明白。其實,孔子的原意是,“復禮”要以“克己”為前提,“復禮”是“克己”的目標。營造起內心的秩序,才是重建社會秩序的根本。東周的“觀念之禮”到孔子手中,得到理論提升,嚴格意義上的“禮學”誕生了。禮學由孔子發其原,孟子、荀子各得一端,都進行了深入探究。荀學是孔學分支,荀子受“復禮”的啟發,所以荀子禮學偏于“道問學”,主張“隆禮”,是西周制度之禮的繼承者。“隆禮”的極致,到荀子學生韓非那里,成為“重法”,這是“禮”之“制度性”發展的必然趨勢。孟子受“克己”的啟發,所以孟子禮學偏于“尊德性”,營造內心的秩序,強調心性的修養,是東周“觀念之禮”的繼承者。孔子關于禮樂的談論很多,其核心思想,是弘揚周公人文禮制的精神,至于“禮”對于人生的意義何在,“禮”與人心關系如何,孔子尚未來得及詳細論述。孔子之后,思孟學派便發展了“觀念之禮”,“觀念之禮”的主旨,是要從內到外解決人性與道德相一致的難題,即人性管理。從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強調修身,走向心性之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認為關鍵在于“求諸己”,沿著“求諸己”的方向去尋找“中道”,就會發現性、情、心、志等范疇,這是“禮”之“道德性”發展的必然趨勢。
秦漢至隋唐——“體制禮學”
主體特征是“體制禮學”。縱觀人類觀念史,人類有兩大思考:一是對于體制的思考,一是對于生命的思考。秦漢至隋唐的禮學實踐成果,正是對于體制的思考,可稱之為“體制禮學”。秦漢至隋唐的“體制禮學”,是由先秦“制度之禮”、荀子禮學、韓非法治思想這一系發展而來,是“禮”之“制度性”的進一步發展完善。秦漢至隋唐這一階段,社會精英關注的焦點在于,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管理與行政運作體制,于是將歷代積累下來的有關制度之禮的內容,經過選擇整理、修訂完善,以國家法典形式,得以明文確定,成為國家體制的范本。如西漢初年,叔孫通制定禮儀,有利于安定國家秩序,劉邦大加贊賞;《史記》設有《禮書》,《漢書》設有《禮樂志》,東漢編有《漢官儀》,《后漢書》還專列《禮儀志》,亦可見對體制禮學的重視程度。又如隋唐禮學,猶得秦漢之淳樸,儒者不敢輕疑經注,歸納總結六朝以來義疏成果,并且加以發展;唐統治者也重視“禮”的實用,如陸續編成《貞觀禮》《顯慶禮》《大唐開元禮》《唐六典》《通典》,對禮制的方方面面,大到國家政體官制,小到服裝規制,都做出細則說明。直到現代,我們還常常提起“漢服唐裝”,就是漢唐禮制在后世的遺跡。
宋明時期——“心性禮學”
主體特征是“心性禮學”。從后世看宋明學術,以“理學”著稱,這正是關于生命思考的思想成果。“禮”的本質,是文明的秩序,而“理學”所追求的境界,實際上就是內心的秩序性,可稱之為“心性禮學”。宋明時期的“心性禮學”,是由先秦“觀念之禮”、思孟禮學思想這一系發展而來,是“禮”之“道德性”的進一步發展完善。宋明“心性禮學”之所以興起,既受到宋明文化性格趨于內斂的總體影響,同時也是出于對漢唐“體制禮學”的深刻反省。有了好的體制,還需要有素質的人去施行,從唐玄宗以后,天下大亂的局面接連不止,社會精英認為問題不在體制,而在人心。深入探討人內心的秩序性,并將其提升到哲學本體的地位,稱為“天理”,看作永恒的客觀道德法則,這是對先秦“觀念之禮”思想的理論升華與深入發展。這種心性研究的取向,發展到明代特別是到王守仁,在繼承思孟學派“盡心”“良知”與陸九淵“心即理”等學說的基礎上,批判性吸收朱熹以“天理”為本體的學說,創立王學流派,或稱陽明心學。陽明心學論其實質,屬于體驗哲學,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但是如此學風浸淫所致,也使得后來明儒談“禮”,越來越脫離實際。這一傾向愈演愈烈,逮及明末,陽明心學的末流,越來越陷于佛家空虛之境,空談心性的弊端也越來越嚴重,逐漸走向空疏,最終導致清代禮學的全面反思與整合。
清代——“禮學整合”
主體特征是“禮學整合”。清代是傳統學術集成時期,禮學在這一時期,也體現出全面整合的特征,是清學的顯著成果之一。明清朝代更迭,社會動蕩不堪,社會精英沉痛反思明朝滅亡教訓,宋明理學尤其是晚明心學的空疏學風,首當其沖,成為士林批判攻詰的對象,于是有識之士將研究重心回歸經學元典。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大學者紛紛投身于禮學研究,從而為清代禮學發展奠定雄厚的學術基礎。由于清初崇實學風引導,清代禮學與宋明禮學不同,向舍“理”而言“禮”的方向發展。漢唐禮學,研究制度之禮,重視名物訓詁,走的是“外王”的路子。宋明禮學,研究觀念之禮,重視義理發揮,走的是“內圣”的路子,宋明禮學,是在漢唐禮學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升華。而清代禮學,試圖整合漢宋禮學成果:既不同于漢唐禮學,清代禮學蘊涵著深層理論結構;也不同于宋明禮學,清代禮學從經學元典解讀出發,結合現實禮制問題,將宋明禮學的理論形態,又重新拉回到實踐領域。清中葉以后“以禮代理”說,不僅僅是學術史上漢宋之爭的產物,也是清代學者通過整合漢宋,走出的一條獨具特色的思想解放道路。長期以來,學界認為清學“有學術而無思想”,這是歷史誤解。考證研究的背后,往往有著思想企圖,這需要通觀整部著作,結合時代思想,方能體會得出。清代第一流的學者,以文獻考據研治禮學,背后有一整套思想體系蘊含其中,“通經求義”的思想脈絡貫穿始終,這就是清代禮學的整合特征。
(作者系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講師;摘自《孔子研究》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