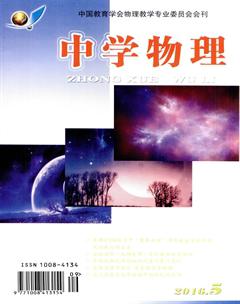追根求源尋自然 咬文嚼字學物理
張協成 王若智



高中物理教學,一直是中學學科教學中的難點。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高中物理在知識結構的全面性和完整性、思維特點的抽象性和邏輯性、解題要求的的推理性和發散性、實驗分析的量化性和推論性等方面,與初中物理相比,在質和量的方面,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標準。但是,在高中物理教學,特別是高中物理定義、概念和規律的初始教學中,我們很多老師,只教學生物理知識是什么,不指導物理知識是怎么產生的;強調物理概念(和規律)的內涵和外延,忽視物理概念產生(和規律發現)的社會、經濟、科學和技術發展的背景,忽視物理概念產生的人文背景;重視物理習題的解題過程和技巧,而忽視物理認識的前因后果,造成學生對高中物理的認識和理解,“只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在很多學生意識中培植下“物理難,是物理學科的特點”的必然思想。
十余年來,我們在高中物理教學中,試探著從物理知識產生、物理規律發現的源頭上追根求源,在物理定義的方法、物理概念的描述中咬文嚼字,有效地降低了學生學習物理的畏難情緒。
現舉幾例論證說明,以求廣大同仁指正。
1從漢字的源頭學物理
學習物理,較早遇到的一個概念當屬“力”。初中物理對“力”的定義是:力是物體對物體的作用;高中物理對“力”的定義:力是物體間的相互作用。如果再深入一點,我們對力的描述通常用三句話:力是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力能使物體產生加速度;力能使物體發生形變。
我們知道,定義是對于一種事物的本質特征或一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所作的簡要說明。比如速度可以如下定義:運動物體的位移和產生此位移所用時間的比叫物體運動的速度。可以看出速度是用位移和時間兩個簡單的概念來描述的。
若不假思索,“力”的定義好像很簡單。但略一深究,問題就暴漏出來了——什么才叫“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什么叫“作用”呢?比如,老師批評學生說:“我已經說過你多少次了,怎么對你毫無作用?”這也是力嗎?當然不是。
這就是說,學生對“力”是什么,認識其實是很含糊的。
在長期的物理教學探索中,我們發現,對于有些物理初始概念的教學,若從漢字產生的源頭上尋找根由,可以實現物理初始概念教學的重大突破。
大概在進入夏紀年之際,先民們在廣泛吸收、運用早期符號的經驗基礎上,創造性地發明了用來記錄語言的文字符號系統,在那個時代,漢字體系已經成熟起來。
殷墟遺址發現的商代文字,在造字方式的結體特征之一,就是以勞動創造物和勞動對象為構字的基礎。如“力”字,就是個象形字。
從上述字形我們不難看出,“力”字無論如何演變,都頗像農具中的犁形或權形,上部為犁把或權把,下部為耕地的犁頭或鏟柴草的杈排,犁或權,有柄有尖,用以耕地或鏟柴草。
也就是說,我們的先人很早就意識到,在用犁頭耕田、拿權把鏟柴草的過程中,就存在著“力”。這樣,“力”的概念——物體對物體施加作用的過程中,就建立起來了!
諸如此類,“光”、“熱”、“電”、“功”、“原子”等,人們通常“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概念,仿照這種教學思路,我們都可以實現對這些原始的、抽象概念在初始認識與理解的突破。
2“鐳射”原來是“激光”
上世紀80年代初,曾幾何時,在我國的大街小巷,各種電器商城、影院、迪廳,無不炫示著“鐳射音響”、“鐳射唱盤”的廣告招牌。“鐳射”,一時成為現代化、酷時尚的代名詞。
“鐳射”是什么?從字義上理解,很多人誤認為它與放射性相關,因而對“鐳射音響”、“鐳射唱盤”畏懼不已
“鐳射”——Laser,中文港臺地區譯名“萊塞”,大陸地區譯名“鐳射”。它是英文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首字母縮寫,意指受激輻射的光放大。名字雖然很具體,但太長不好記。
1964年,錢學森致電長春光機所《受激光發射情報》編輯部,建議將“受激輻射的光放大”改成了“激光”;同年,我國物理學界在上海開會,這一具有中國特點的科學名詞便被國內學人正式采納。《受激光發射情報》也順勢更名為《激光情報》(后隨科技形勢的發展,多次更名,成現在的《激光與光電子學進展》)。
現在,廣大中華學人對“激光”這一簡約明快、直觀形象名詞,耳熟能詳。
目前,除了大陸地區,其他使用中文的地方仍然叫鐳射、萊塞。
噢,原來“鐳射”是“激光”!
在高中物理教學中,如果我們適時插入像“激光”名詞創生和變遷的花絮,就會讓學生感到物理概念也并不那么深奧難測,物理規律并不那么什么無理無據。物理研究是富有情趣的,物理認識也是富有詩意的。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與學生一起認識激光的產生,探究激光的原理,構建激光器的結構,拓展激光的應用,就會像詩人身入深山幽谷,心生探幽攬勝之情,漸入教學佳境。這樣,我們的物理課堂教學,也會自然而然,順心隨意,有效高效。
3“簡諧運動”就是“簡單而和諧的運動”
簡諧運動,顧名思義,就是“簡單而和諧的運動”。簡單,和諧,恰恰是物理美學的基本特征。
牛頓曾說:自然界喜歡簡單,不愛用多余的原因夸耀自己。愛因斯坦也把簡約當作鑒別科學理論的重要美學標準。他曾說:要通過最少個數的原始概念和原始關系的使用來達到科學的目的。
物理學的簡單性并不是指物理內容本身簡單,而是具有深刻的物理內涵;物理量的關系及運算給人簡潔明快之感;一個理論的假設條件很少,而概括的經驗事實或演譯出的推論卻很多。同時,一個具有簡單美學屬性物理學理論,必然與數學結合得完美統一。也就是在說,具有美學屬性的物理學規律,一定能用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去表述,一定能用完美的圖像去描繪。
當質點作簡諧運動時,質點的動力學、運動學規律,及其數學描述方式,必然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①質點所受的力跟位移成正比,并且總是指向平衡位置,即F=-kx。
反過來,如果我們發現質點受力與位移滿足F=-kx的關系,那么,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這一運動,就一定是簡諧運動。
②它是一種由自身系統性質決定的周期性運動,如單擺運動和彈簧振子運動。
周期運動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對稱性。而對稱性是物理美的另一主要特征。
美和對稱緊緊相連。對稱,既有空間對稱又有時間對稱。因此,處理簡諧運動的問題,周期性和對稱性,是我們考慮的首選的方法和觀點。
③簡諧運動的圖象,一定是正(余)弦圖象。
反過來,如果質點的位移與時間的關系遵從正弦函數的規律,即它的振動圖象(x-t圖象)是一條正(余)弦曲線,這樣的振動一定是簡諧運動。
這樣,根據數學性質,我們也可以把任何一個實際的簡諧運動設想為一個勻速圓周運動的投影(因為作勻速圓周運動的質點,其投影的運動是簡諧運動),這個設想的圓周叫參考圓。如圖1所示,它以簡諧振動的平衡位置O為圓心,以簡諧振動的振幅A為半徑,以簡諧振動周期T為周期,它的角速度ω=2π/T。
同理,我們可以通過對參考圓的討論來推導出簡諧運動的位移、速度、加速度與時間的關系。
這樣,從物理美學的角度,確定簡諧運動的研究方法,探尋簡諧運動各物理量間的關系,就使這一教學難點,變得自然而然、簡單直接了。
4動量、動能的“同”與“不同”
動量和動能,都是度量物體運動大小的物理量。而且,它們對運動進行度量時,都用到物體的質量(m)和運動的速度(v)這兩個物理量。
那么,為什么既要引入動量,又要引入動能呢?這是高中物理教學中,經常被人們忽視,并且是困擾很多師生的一個教學難點。在動量和動能這兩個概念的教學中,若只講動量和動能在公式表述形式上的區別,而不講它們在研究對象和物理本質上的異同,其結果是學生只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雖然會解題了,但他們卻不知道為什么要這樣解題。
原來,在17~18世紀,由于“力”的概念還不能完全確定,對力的各種效應以及與之相應的各個物理量的意義和使用范圍也是不清楚的,因而引發了物理學史上著名的笛卡兒學派和萊布尼茨學派關于力的正確表示方法的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
當時,人們常把力同現在所說的力矩、動量、功、動能等物理量相混淆,習慣于把外加的力稱為“運動的力”;把“物體的慣性”稱為“物質固有的力”、“阻抗的力”。
笛卡兒學派認為,所謂“運動的力”,就是指一個正在運動的物體所具有的使另一物體運動的能力,如推開物體或迫使它向前運動,或者運動物體克服障礙和阻力的能力。那么,這個力決定于哪些量呢?最初,伽利略就認識到“推動者或阻擋者的力(動量)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它是由兩個共同決定運動量度的觀念所決定。其一是質量,其二是速度”;笛卡兒在研究碰撞的過程中,沿襲了伽利略的觀點,提出應該把物體的質量和速度的乘積作為“力”或物體“運動多少”的量度;1687年,牛頓在他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明確提出了動量的定義,提出在物體的相互作用中,動量這個物理量反映著物體運動變化的客觀效果。這樣,把動量作為運動的量度,一度得到了科學界的普遍承認。
萊布尼茨在他的論文中,對笛卡兒學派的這個量度方法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力必須由它所產生的效果來衡量,例如用它能將一個重物舉起的高度來衡量……”,他由此得出,應該用量值mv2來量度物體“運動的力”。
后來根據科里奧利的建議以1/2mv2代替mv2,這就是后來所說的運動物體的動能。
萊布尼茨也看到了笛卡兒提出的運動的量度在某些情況下是適用的,因此在1696年萊布尼茨指出,“力”有兩種,一種是“死力”,另一種是“活力”。“死力”存在于相對靜止的物體間,如吊繩的拉力、桌面的支撐力等。“死力”可用物體的質量和該物體由靜止狀態轉入運動狀態時所獲得的速度的乘積來量度,所以,動量(mv)是“死力”的量度;1/2mv2就是物體的“活力”的量度,正是由于自身具有這種“活力”,物體才能運動而永不靜止。
萊布尼茨也看到,在有些情況下,如非完全彈性碰撞中“活力”會減少,但實際上“活力”并沒有損失,而只是被物體內部的微小粒子吸收了,微粒的活力增加了。
19世紀中葉以后,自然科學家們仍然沒有從運動量度的這場爭論的混亂中完全擺脫出來。恩格斯根據自然科學的最新成就,尤其是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的發現,提示了兩種量度的本質區別。
恩格斯指出,在不發生機械運動“消失”而產生其他形式的運動的情況下(如簡單機械在平衡條件下的運動傳遞,完全彈性碰撞的運動傳遞等),運動的傳遞和變化都可以用動量mv去量度。就是說,“mv表現為簡單移動的,從而是持續的機械運動的量度”;但當發生了機械運動“消失”而其他形式的運動產生,即機械能和其他形式的能(包括勢能、內能、電磁能、化學能)相互轉化的過程中、運動的傳遞和變化都應以1/2mv2去量度。在這里,1/2mv2表現為已經消失了的機械運動的量度。
這樣,恩格斯便得出結論:機械運動確實有兩種量度,每一種量度適用于某個界限十分明確的范圍之內的一系列現象。一句話,動量(mv)是以機械運動來量度的機械運動;動能(1/2mv2)是以機械運動轉化為定量的其他形式的運動的能力來量度的機械運動。
5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發現的偶然和必然
關于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的發現,我們不少的教科書,幾乎都會繪聲繪色地這樣介紹:1820年,奧斯特發現電流磁效應后,根據電和磁的對稱性,有許多物理學家便試圖尋找它的逆效應,提出了磁能否產生電的問題。
英國科學家法拉第是“磁電對稱”思想的積極支持者,法拉第堅信,很強的磁場,一定可能會在鄰近的閉合電路感應出電流。在這種信念的支持下,他進行了長達10年的艱苦探索。他做了多次嘗試,經歷了一次次失敗,1831年他終于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
很多勵志書,也多把法拉第的這種“在堅定信念支持的堅守”,總結為“機會和成功總屬于有準備的人”。
但是,法拉第究竟怎樣終于成功的,并沒有真正揭示出來。學生對于法拉第為什么會成功,像夢幻一般,認識朦朧,不知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給物理發現增添了一種神秘感,使學生學習物理添加了一種困難。
其實,在1820年到1931年的十年間,法國著名物理學家安培、菲涅耳、阿拉果,瑞士年輕科學家沃拉斯頓等,都投身于磁生電的研究中去。他們用各種方法產生強磁場,希望發現磁生電的途徑,但都無功而返。究其原因,都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受思維定勢的影響。他們認為,奧斯特的磁效應是一種穩定效應,因此在研究磁生電時,也都是從穩定條件出發,而沒有考慮到這是一種動態效果。
1820年,阿拉果得悉奧斯特發現電流的磁效應后,親自訪問了日內瓦的實驗室,驗證奧斯特實驗結果;又在巴黎重復此實驗,發現軟鐵的瞬時磁化;1822年,他和洪堡測量格林威治附近小山的磁場強度時,注意到磁針附近的金屬物對磁針的振動有阻尼作用,他考慮是否存在逆效應,即旋轉的銅盤能帶動附近的磁針轉動,但磁針的旋轉與銅盤不同步,稍滯后。
電磁阻尼和電磁驅動是最早發現的電磁感應現象,但當年阿拉果并沒有認識到。
同年,安培為了驗證他的分子電流假說,安培又設計了這樣一個實驗。其實驗裝置如圖2所示,a是一個固定在支架上的線圈,由很多匝導線繞成并與電池連接;b是一個由很細的銅條彎成的銅環,并用一根穿過線圈的細線L把銅環懸掛在O點,銅環正好在線圈b中且使兩者同心。將一個強磁體放在銅環附近。在未接通電流時,銅環與線圈之間沒有相互作用,當線圈中通以電流時,發現銅環發生了偏轉。安培認為,在電流通過線圈時,在銅環中感應出了分子電流,銅環被磁化了,銅環的偏轉是由于強磁場對磁化了的銅環作用的結果,他竟沒有發現環中出現了電流,更未意識到這一電流就是感應電流。
1823年,瑞士物理學家科拉頓曾企圖用磁鐵在線圈中運動獲得電流。他把一個線圈與電流計連成一個閉合回路。為了使磁鐵不至于影響電流計中的小磁針,特意將電流計用長導線連后放在隔壁的房間里,他用磁棒在線圈中插入或拔出,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跑到另一房間里去觀察電流計是否偏轉。由于感應電流的產生與存在是瞬時的暫態效應,他當然觀察不到指針的偏轉,發現電磁感應的機會也失之交臂。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引導法拉第邁進電磁感應發現的大門?
原來,就在1822年,阿拉戈和呂薩克發現當有電流通過其中有鐵塊的繞線時,它就能使繞線中的鐵塊磁化。這就是電磁鐵的雛形;1823年,英國人斯特金將一根并非是磁鐵棒的U型鐵棒繞了18圈銅導線,將線接通伏打電池后,U型鐵棒就變成了一塊更強“電磁鐵”。它能吸起比自身要重20倍的鐵塊,而當電源切斷后,U型鐵棒就完全沒有了磁性,回歸為普通的鐵棒;1829年,美國電學家亨利對電磁鐵裝置進行了一些改革,他用絕緣導線代替裸銅導線。導線有了絕緣層,它們就能一圈圈地緊緊地繞在一起,因為線圈越密集,產生的磁場就越強,這種方法就大大提高了電磁鐵的效能。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電磁鐵在工業生產中的應用價值,愈來愈得到人們的重視。
苦苦尋找電磁感應途徑的法拉第,于1825年左右,也轉向投身于電磁鐵的研究和應用。
法拉第想,既然U形電磁鐵的磁性比條形電磁鐵的磁性強得多,那么,環形電磁鐵的磁場是否應該比u形磁鐵的磁場更強呢?
正是“有心插花化不開,無心栽柳柳成蔭”,1831年8月,法拉第的實驗終于得到了突破性進展。環電磁鐵失去了外線的磁性,但是,卻發現了感應電流!
法拉第的實驗大致是這樣設計的:
在一個鐵環上繞有A、B兩組線圈,如圖3所示,B線圈抽頭接成閉合回路,A線圈兩端接于電池組。在一次實驗時他突然想到,每次將電池接通后才去看指針是否偏轉,會不會是把電流表放得太遠了。法拉第抱著試一試的心情把電流表放在眼前,結果當電源接通時,電流表指針立即發生明顯的擺動,而切斷電流時指針向方向相反擺動,這表明線圈B中出現了感應電流,這就是著名的法拉第圓環實驗。
這一實驗使法拉第豁然開朗:由于磁感應電的現象是一種暫態效應。發現了這一秘密后,他設計了另外一些實驗,并證實了自己的想法。就這樣經過近10年的思考與探索,終于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找到了電磁感應現象產生的條件。1831年11月24日,法拉第向英國皇家學會報告了整個實驗的情況,并把這種現象正式定名為“電磁感應”。
這樣,潛心發掘物理學史素材,精心鏈接物理發現的史實,使學生認識到物理發現既具有偶然性,又具有必然性,從而破解了物理發現的神秘莫測感。顯然,這對降低物理教學難度,是一貼良方。
實踐證明,在高中物理教學,特別是初始概念和規律教學中,追根求源,咬文嚼字,對增強學生物理學習興趣,降低物理教學難度,是有一定的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