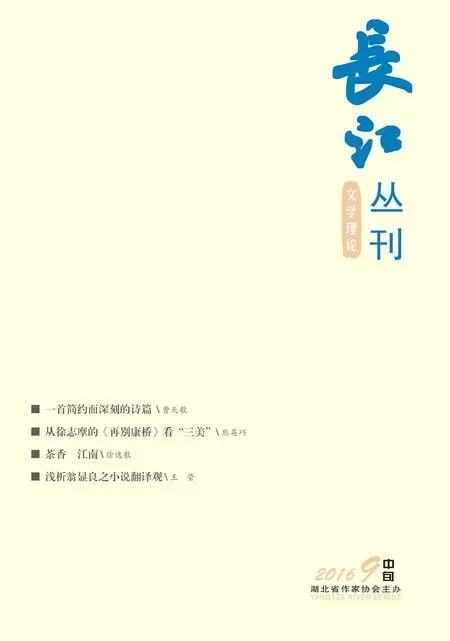淺論村上春樹(shù)小說(shuō)主人公形象的“物哀”情結(jié)
張澍樹(shù)
淺論村上春樹(shù)小說(shuō)主人公形象的“物哀”情結(jié)
張澍樹(shù)
作為日本當(dāng)代著名的文學(xué)家,村上春樹(shù)如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世界范圍內(nèi)掀起了一股“村上熱潮”,對(duì)世界文學(xué)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有人認(rèn)為村上春樹(shù)的成功之處在于對(duì)于傳統(tǒng)日本文學(xué)的“背叛”和“脫離”,他作為一個(gè)深受西方文學(xué)影響的作家勢(shì)必會(huì)在作品中打下“歐風(fēng)美雨”的深深烙印。其實(shí),村上的作品在“西化”意味濃厚的同時(shí),也對(duì)日本傳統(tǒng)文學(xué)有著明顯的繼承。本文中,我們就以村上春樹(shù)長(zhǎng)篇小說(shuō)中的人物形象為例,分析村上作品中透出的日本文化的“物哀”情結(jié)。
村上春樹(shù) 日本文化 物哀
一、“物哀”的定義和成因
日本作為位于亞洲最東端的島國(guó),“從地理?xiàng)l件來(lái)看,世界上沒(méi)有一個(gè)國(guó)家能像日本一樣在狹窄地域集中了如此之多的美景——雪山、海灘、山澗、峽谷、溫泉、瀑布、落櫻,林木蔥蔥,繁花似錦,小橋流水,庭院幽雅。然而,世界上也沒(méi)有一個(gè)國(guó)家像日本一樣,自古以來(lái)被如此之多的自然災(zāi)害所頻頻襲擊——火山、地震、雪災(zāi)、海嘯、颶風(fēng)、戰(zhàn)亂……多少年來(lái)日本人常看到的是美稍縱即逝,頃刻化為烏有。”[1]這樣的環(huán)境給日本的國(guó)民性造成了雙重的影響,一方面,他們對(duì)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具有敏銳的觀察能力;另一方面,“自古好物不堅(jiān)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的現(xiàn)實(shí)也容易讓他們產(chǎn)生“世事無(wú)常”之感。這種感情在受到中國(guó)傳來(lái)的魏晉玄學(xué)和佛教的影響后,進(jìn)一步演化為“物哀”的審美取向。簡(jiǎn)單來(lái)說(shuō),“物哀”指的就是一種以悲為美,以淡雅、凄婉、悲涼為重的審美取向。這種賞玩孤寂、賞玩殘缺的取向,深深影響了日本的傳統(tǒng)音樂(lè)、建筑、茶道、服飾,以至于文學(xué)。這種“人生不如意”的美學(xué)情趣自《源氏物語(yǔ)》開(kāi)始,像遺傳基因一樣在日本文學(xué)中代代相傳。從紫式部到清少納言,從川端康成到太宰治、芥川龍之介,再到村上春樹(shù),其作品中無(wú)奈、孤獨(dú)、寂寥和凄涼的情愫,都是和《源氏物語(yǔ)》體現(xiàn)的“物哀”美學(xué)傳統(tǒng)一脈相承的。
二、村上小說(shuō)主人公的特點(diǎn)
(一)被社會(huì)放逐的“邊緣人”
村上春樹(shù)的主人公往往是一個(gè)再普通不過(guò)的小人物,本身就是孤獨(dú)的象征。他已被徹底“簡(jiǎn)化”,無(wú)妻無(wú)子無(wú)父母無(wú)兄弟無(wú)親戚,與工作同事的交往也適可而止,是一個(gè)徹徹底底的“邊緣人”。相反,村上作品中春風(fēng)得意、八面玲瓏的角色往往是為襯托主人公而存在的反面形象。林少華曾在《挪威的森林》的序言中寫(xiě)道:“與其勉強(qiáng)通過(guò)與人交往來(lái)消滅孤獨(dú),化解無(wú)奈,莫如退回來(lái)把玩孤獨(dú),把玩無(wú)奈。······這種在一般世人眼里無(wú)價(jià)值的、負(fù)面的、因而需要擯除的東西,在村上筆下成了有價(jià)值的、正面的、因而不妨賞玩的對(duì)象。”[2]可以說(shuō),村上筆下彌漫著一種孤獨(dú)的美學(xué);這些平凡的小人物,寄托了他對(duì)現(xiàn)代都市繁雜人際關(guān)系的抵觸,轉(zhuǎn)而追求空寂寧?kù)o的生活,體現(xiàn)了如同日本園林“枯山水”般“少即是多”的價(jià)值取向。
(二)有過(guò)被集體或他人拋棄的經(jīng)歷
村上的主角大多在青春時(shí)期經(jīng)歷過(guò)某種不幸事件從而留下心理陰影,而故事情節(jié)往往也由這些往事而展開(kāi)。如《挪威的森林》里渡邊唯一的好友木月突然自殺,《沒(méi)有色彩的多崎作的巡禮之年》里多崎作被高中的好友團(tuán)體驅(qū)逐,《且聽(tīng)風(fēng)吟》中初戀女友的不辭而別。這些突如其來(lái)的事件也許呼應(yīng)了村上春樹(shù)對(duì)于孤獨(dú)的看法:“人,人生,在本質(zhì)上是孤獨(dú)的,無(wú)奈的。所以需要與人交往,以求相互理解。然而相互理解果真是可能的嗎?不,不可能,宿命式的不可能,尋求理解的努力是徒勞的。”但是,主人公把玩孤獨(dú)的態(tài)度又恰恰印證了“物哀”之美的另一個(gè)方面:“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發(fā)展趨勢(shì)值得悲傷的就悲傷,值得哀憐的就哀憐,值得高興的就高興,值得眷戀的就眷戀。”順其自然,無(wú)心無(wú)我,正是頗具禪意的一種體現(xiàn)。
(三)“平凡中有不凡”的性格
村上春樹(shù)之所以廣受年輕人歡迎,一大原因可能是由于他的作品中從來(lái)不見(jiàn)成功學(xué)那種鼓舞人心、奮發(fā)向上的“心靈雞湯”,反而終于給了“孤獨(dú)”一個(gè)名正言順的理由,甚至還大加贊賞。“村上作品的一個(gè)特點(diǎn),就是主人公從不強(qiáng)調(diào)自己與眾不同,總是說(shuō)自己如何‘普通’。當(dāng)然主人公都是不普通的,但其不普通是借別人之口說(shuō)出來(lái)的,是別人眼里的不普通。”村上春樹(shù)的小說(shuō)以獨(dú)特的風(fēng)格和青春的氣息打動(dòng)了眾多剛剛體驗(yàn)到人生苦澀,開(kāi)始思考人生的年輕讀者,為他們帶來(lái)了深切的心理共鳴。
(四)在現(xiàn)實(shí)和追憶之間徘徊的處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村上春樹(shù)的作品中往往喜歡設(shè)置兩位性格相對(duì)的女性角色,而主人公往往在這二人之間猶豫不決,則代表了沉湎于回憶還是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抉擇。如《挪威的森林》中的直子和綠子,《沒(méi)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中的白和黑,《國(guó)境以南,太陽(yáng)以西》中的島本和有紀(jì)子。這二人往往一個(gè)是圣女般出塵脫俗、多才多藝的美麗女子,但往往給人不食人間煙火之感,與悲傷的回憶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而另一個(gè)則是世俗、活潑的青春少女,渾身上下洋溢著生命的活力。主人公在被美麗嫻靜的前者吸引的同時(shí),也會(huì)被沉重的過(guò)去所纏繞;在被生機(jī)蓬勃的后者打動(dòng)的同時(shí),也會(huì)被現(xiàn)實(shí)的殘酷所阻撓。所幸,村上的主人公大多雖然溫柔,但并不脆弱;沉湎于過(guò)去的少女最后往往選擇自殺來(lái)自我了結(jié),留下悲傷的主人公帶著信念堅(jiān)強(qiáng)地繼續(xù)生活,這也是村上作品中一絲雖然微茫,但依舊耀眼的亮色:與過(guò)去揮別,與未來(lái)妥協(xié)。
三、村上春樹(shù)的人生觀轉(zhuǎn)變
縱觀村上春樹(shù)在日本文壇的前輩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以生命踐行“物哀”理論,給自己“櫻花般絢爛綻放之后凋落”的死亡的,實(shí)在不在少數(shù)。川端康成、三島由紀(jì)夫、太宰治、芥川龍之介······這些大名鼎鼎的作家不約而同地選擇在文學(xué)造詣的巔峰時(shí)刻退出了生命舞臺(tái)。村上春樹(shù)筆下的人物雖然也常常選擇自我了結(jié),但是在他的觀念里,選擇自殺是一種自由,選擇活下去是一種更高級(jí)的自由,與一了百了相比,村上春樹(shù)更為推崇他筆下的主人公“我”面對(duì)孤獨(dú)、荒誕的積極的態(tài)度。當(dāng)“冷雨中的小木屋”消失的時(shí)候,人們就會(huì)被卷入到殘酷的現(xiàn)實(shí)中, 此時(shí)主人公再也無(wú)法平靜,就必須積極地行動(dòng)起來(lái)。從《奇鳥(niǎo)行狀錄》開(kāi)始,村上春樹(shù)逐漸告別了淡漠和疏離,轉(zhuǎn)而擁抱現(xiàn)實(shí),尤其對(duì)社會(huì)漸漸懷有了責(zé)任感。在采訪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時(shí),談及村上春樹(shù),他曾說(shuō)“希望村上在其作品中能夠突破內(nèi)避式個(gè)體的失落、孤獨(dú)、空虛和悵惘等頹廢情緒的圖譜,賦予作品中的人物以更多的社會(huì)意義。”這種希望已經(jīng)變成了現(xiàn)實(shí)。《神的孩子全跳舞》、《地下》、《1Q84》等作品反映了神戶大地震、東京地鐵毒氣襲擊等重大事件,表明村上由“私人化寫(xiě)作”逐漸轉(zhuǎn)向?qū)w制和社會(huì)的叩問(wèn)。正如他在2009 年獲得耶路撒冷文學(xué)獎(jiǎng)時(shí)發(fā)表的感言那樣:“假如這里有堅(jiān)固的高墻和撞墻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村上的小說(shuō)中不再像之前那樣充滿無(wú)法擺脫的悲哀和宿命感,而多了一些由愛(ài)心構(gòu)建的亮色。在村上筆下孤獨(dú)的故事里,處處都隱藏了救贖,孤獨(dú)并沒(méi)有使他們走向絕望,反而讓他們?cè)诠陋?dú)的最深處看到了一點(diǎn)光亮,并由此走向新的生活。他曾說(shuō):“我寫(xiě)小說(shuō)的理由,歸根結(jié)底只有一個(gè),那就是為了讓個(gè)人靈魂的尊嚴(yán)浮現(xiàn)出來(lái),將光線投在上面。經(jīng)常投以光線,敲響警鐘,以免我們的靈魂被體制糾纏和貶損。”雖然村上作為一個(gè)純文學(xué)作家,這樣的“責(zé)任寫(xiě)作”不一定是他的長(zhǎng)項(xiàng),但是他對(duì)于“物哀”精神的繼承和超脫,仍然是值得期待的。
綜上所述,日本文學(xué)中的以悲為美的物哀理念,追求的是纖細(xì)而幽怨的情調(diào),著眼點(diǎn)不是濃烈如酒的醇厚,而是淡若止水的清雅。而村上春樹(shù)無(wú)意中對(duì)這一特點(diǎn)的繼承和對(duì)西方文學(xué)的借鑒,則使得他的文字更加融會(huì)貫通、精微動(dòng)人。“物哀美”是一種感覺(jué)式的美,它不是憑理智、理性來(lái)判斷,而是靠直覺(jué)、靠心來(lái)感受。讀村上的作品同樣是一種“以心不以腦”的直覺(jué)體驗(yàn),掌握村上作品中獨(dú)特的“物哀”情結(jié),對(duì)于我們更好地把握作品、了解日本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1]葉葒.以悲為美——論日本文學(xué)中的物哀[J].世界文學(xué)評(píng)論,2012(01).
[2]村上春樹(shù)著.林少華譯.挪威的森林[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