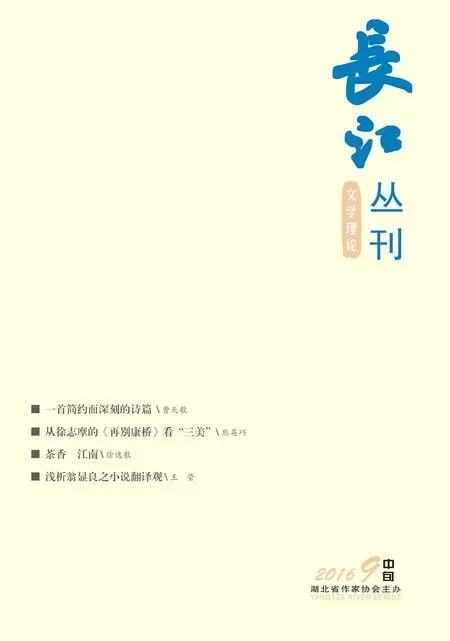《卡斯特橋市長》中的邊界空間對比分析
鄒德媛
《卡斯特橋市長》中的邊界空間對比分析
鄒德媛
本文從建筑空間、家庭空間及工作空間三個維度對《卡斯特橋市長》重新考察。從空間的對比變遷中挖掘其中的文化內涵,撥開各種矛盾力量的沖突,哈代在小說中力圖建立一個融合、平衡的共同體。這顛覆了哈代悲觀作家的傳統觀念,為哈代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邊界空間 對比 融合
批評者對哈代的定性評論是他是悲觀小說家,細讀哈代的小說,對此結論提出質疑。哈代的思想經歷了對田園的眷戀之情后,正視現實,隨對傳統農村的予以同情與理解,但思想更為深刻,更加關心城鄉變遷中人們何去何從,人們的生活方式、態度、信仰、習俗、思想如何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而改變,即城鄉相輔相成,融合平衡的共同體社會。
哈代的《卡斯特橋市長》創作于1884—1885年間,是哈代創作第二個階段的重要作品。小說講述了工業革命期間英國社會的城鄉變化,以及由次導致的一系列新舊文化沖突,雷蒙德·威廉斯將之歸類為“鄉村邊界小說”。本文將在空間理論的框架下結合雷蒙德·威廉斯的空間批評文化理論,從新的視角解析《卡斯特橋市長》。本文從建筑空間、家庭空間及工作空間三個維度探討主人公亨察德在與法爾弗雷的競爭中的空間轉換為切入點,三個特定的空間轉換折射出特定時期的文化觀念和情感結構。
一、雷蒙德空間理論
20世界西方學界出現的空間轉向,空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單一的,凝固的容器,而是立體的,飽含社會文化意義的有機體。各派理論批評家從不同的角度探析空間的意義。作為空間理論的重要貢獻者,雷蒙德的空間批評理論主張從文學文本入手,強調空間的物質性,文化性,注重文學中的地理空間,他的空間批評研究史將文學文本中的戲劇、小說作為文化和社會中的一部分來進行研究。文學作品雖不能像地理學那樣提供精準的數據,甚至還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但正如克朗所說,“文學作品中的‘主觀性’不是一種缺陷,事實上正是它的‘主觀性’言及了地點與空間的社會意義”①,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論保證。
雷蒙德的獨特貢獻在于他在文學作品中引入了空間概念。他在《鄉村與城市》這部著作中從“城市”、“鄉村”,“邊界”空間切入,給予邊界空間極大的關注。在雷蒙德看來,邊界空間不僅是地理位置上從鄉村到城市過渡的地理空間,更是人們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從傳統到現代過渡的文化空間。雷蒙德的邊界空間具有多維性,不是單一的、扁形的。它與時間敘述相輔相成,已經不是單一意義上的地理空間,而是富含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生活方式,及代表各種生活方式的異質力量沖突的文化空間。在三個
中,雷蒙德注重邊界空間,認為工業革命沖擊了英國傳統的鄉村社會結構,破壞了這個“共同體”。而邊界空間中,各種矛盾沖突,異種力量融合,變化,重新組合,成為新的“共同體”。
重新審視《卡斯特橋市長》這部小說,卡斯特橋市具有明顯的邊界空間的特點,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城市,也不是純粹意義上的鄉村,它是一個處于城鄉轉變過程中的獨特的地理空間。小說中各種建筑、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及思想方式的描寫可以更好的闡釋城市化進程中人們的思想、信仰及人們的身份轉變過程中的特點,有助于讀者全面理解城市化進程中的文化變遷。
二、建筑空間
空間包括物質景觀和非物質景觀,本文中的建筑空間即一種物質景觀,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釋是人們人為的為了滿足人們生產或生活的需要,運用各種建筑主要要素與形式所構成的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的統稱。威塞克斯是哈代以其家鄉多賽特為背景虛構出來的地理空間,并賦予其獨特的內涵和社會意義。哈代筆下的卡斯特橋市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只能算市鎮。卡斯特橋市“整個兒坐落在一大片小麥地上”……“沒有城市與周邊高低的交界區,”“農夫的孩子可以……將石頭扔進市政職員辦公室的窗子里;身著紅袍的法官,可以伴著陣陣咩咩的羊叫聲,審問偷羊賊,宣讀他的判決書”②小說對卡斯特橋式整體風格的描寫就呈現出一種城鄉邊界模糊,亦真亦幻的朦朧狀態。地理空間是文化空間的載體,即文化空間具有物質性,卡斯特橋市正是一個處于城鄉過渡狀態中的邊界。
小說中雖設置了很多地理場景及一些帶有傳統鄉村特色的元素符號。三水手客店有都鐸式拱門,門牌上的三個水手被陽光曬得褪了色,扭曲變形,畫像已經模糊不清,可是店老板卻不能在卡斯特橋“找到一個畫工,能夠擔當復制這樣富有傳統風格的人物形象的任務。”③“鐵器店里的長柄大鐮刀、普通鐮刀、羊毛剪、彎尖刀、鍬、鶴嘴鋤和鋤頭”④。還有墻皮脫落的教堂,破敗的圓場。這一切使卡斯特橋市成為維多利亞時期鄉村集鎮的典型。這些地理空間及其元素符號不但營造了一個傳統氛圍,它們的變化反過來又助推了情節向前發展。城市與鄉村是相輔相成的。“農村與城市幾乎談不到一線之隔,而是緊密相連”⑤。不但指地理空間上的不分你我,還體現在生活習慣、方式、思想、信仰等方面。
賣粥老嫗認為“世界可不是老樣子啦;正正派派做生意賺不了錢……只有耍滑頭,搞欺騙”⑥。極具諷刺意義的是,她本人就是一個不可靠的敘述者,是一個欺詐的小販。從反面看,這正是哈代對新興社會結構的肯定,對結構重組后的社會敞開胸懷。以技術和科學為代表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涌入,卡斯特橋市整個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而這種代表新興生產力結構的社會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喜愛法爾弗雷這個年輕人,接受他的新思想,這就使這個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融入了新興生產關系。
亨查得的性格極端化,他要么恨一個人,要么愛一個人,這樣的性格決定他在思想、信仰、行為及生活方式上不能適應這種過渡狀態的文化特點,生產關系決定人的身份,個人要在新的生產關系中重新構建自己的身份,才能生存,適者才能生存生存。卡斯特橋是哈代虛構的一個平衡點,新舊交替的中間地帶,一個新舊秩序的容器。亨察德之生活在過去的回憶中,不能選擇遺忘,只能走向滅亡。
三、家庭空間
家庭是人的避風港,是私密的空間。而家卻也是最能體現身份地位的空間。小說中的家庭空間主要指亨察德的家,無論家具,寥寥無幾的書本,還是整個房屋建筑,處處可見它的傳統性。
亨察德是這個家庭名副其實的一家之主,蘇珊在這個家庭中幾乎是悄無聲息。可正是他這個一家之主將法爾弗雷領進自己的家門,邀請他與自己一起供餐,且在家中將自己深藏十九年的秘密透漏給了這個不太熟悉的年輕人,而亨察德自己也承認,就是喜歡這個年輕人,有說不出的原因。他在家庭空間的地位在他破產后就讓給了他的對手法爾弗雷,一個新興階級的代表。亨察德破產后,法爾弗雷買下它的房產和家具。同一個空間,因其主人的思想、信仰、身份不同,所具有的社會屬性也發生了變化。正如亨察德自己所說“他還要照樣買下我的身體和靈魂吧!”⑦
從小說整體情節安排來看,法爾弗雷不但娶了亨察德的未婚妻露塞塔,在露塞塔去世后又取了他的女兒伊麗莎白。這個房間的三個女主人,除了蘇珊外,另外兩個都屬于法爾弗雷。而蘇珊在女兒伊麗莎白是否亨察德親生的問題上,又欺騙了亨察德。伊麗莎白本身就和亨察德形成鮮明的對比。伊麗莎白有理性,做事有條理,亨察德易沖動,性格善變。伊麗莎白熱愛知識,喜歡讀書,而亨察德沒有什么文化,讀書寥寥無幾。哈代借此對比,暗含伊麗莎白非亨察德親生女的身份。亨察德喪失了在這個家庭的生存空間。亨察德的在這個家庭里喪失了身份后,哈代又兩次安排他回來,一次是為露塞塔,這一安排,除了符合人物性格的需要,還隱喻了兩種新舊力量,思想的交融。這個空間既不是亨察德的家,也不是法爾弗雷的家,是一種結構發生了變化的全新的家。
影響亨察德大起大落的人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意失敗,二是情感受挫。經濟結構影響這情感結構,生意失敗后,亨察德的思想經歷了一系列復雜矛盾的變化。對繼女伊麗莎白由冷漠變得依賴,順從。對于他的記憶,他有選擇的進行遺忘,遺忘里伊麗莎白養女的身份,重新接納她,父女二人共同經營的種子生意,哈代在此勾畫出一副人人向往的和諧家庭的畫面,這與之前亨察德對待妻女的態度截然相反。亨察德人生轉折點就是賣妻,而伊麗莎白第一次給亨察德送信時,亨察德給妻子的信又附上的這五個畿尼,正是當初賣妻的錢。可見,妻子在他眼里仍舊是一件商品,他有義務照看她卻無情感。現在這個只有父女的家卻處處充滿純粹的親情,令人向往。
四、工作空間
工作空間是最直接體現生產關系的地理空間。小說中的工作空間主要指市政大廳、亨察德的倉庫和進行糧草交易的集市。小說運用大量的對比元素展示新舊關系,亨察德做事全憑記憶,賬目一團糟,人員管理上簡單粗暴;法爾弗雷有知識,懂得科學管理,愛讀書,還給伊麗莎白推薦了大量的書籍。
對待新技術的態度上看,法爾弗雷還引進了先進的機器收割機,大家非常好奇,引發熱議,而亨察德卻對此不屑一顧。知識、技術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這毋庸置疑,亨察德自身固有的傳統農業意識導致他不愿接受新事物。在糧食買賣生意上,法爾弗雷有一套科學的策略,掌握好買進賣出時間,逐漸積累起一定的財富。亨察德僅憑一個占卜者的占卜來制定買進糧食計劃,結果出人意料,糧價并未上漲,導致了他破產的結局。法爾弗雷在生意場上擊敗亨察德后,開始積極謀求市長這一職位。破產后的亨察德,緊接著被揭發但年賣妻丑聞,因此,在下一任的市長選舉中落選。亨察德在公共領域的生存空間亦不復存在。
生意的失敗使亨察德的內心情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對競爭對手法爾弗雷充滿敵意,由憤怒敵對,到復仇,再到和解。不愿意選擇遺忘,難以面對現實,酒后不但詛咒法爾弗雷,甚至跑到糧倉屋頂要與法爾弗雷決斗,勝利之后,卻不忍置之于死地,放過了法爾弗雷,而他們最終的和解是由于露塞塔的死去。
亨察德的失敗是哈代不愿愿意看到的結局,哈代自始至終都是積極的尋求出路,法爾弗雷在亨察德破產之后制定了幫助他的計劃,由他牽頭,重新做起種子生意。亨察德的接受,無論處于什么原因,亦體現他思想的改變。新舊兩種力量在這一空間沖突作為激烈,最終雖已亨察德孤獨死去為結局,但此時的亨察德亦不是之前的亨察德,他的思想、行為均發生了變化,而法爾弗雷的思想亦發生了變化,這種思想是融合了新舊兩種傳統的全新思想。
五、結論
工業革命對城鄉社會結構及人們的生活方式的沖擊,使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及行為均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反來又影響了人們的生存空間。卡斯特橋市是哈代筆下融合的邊界空間,是哈代積極人生態度的一種反映。這一嘗試對我國城鄉變遷中涉及的教育、思想、信仰、生活方式的變化有深遠意義。
注釋:
①[英]邁克·克朗,楊淑華,宋慧敏譯.文化地理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
②[英]托馬斯·哈代,張玲,張揚譯.卡斯特橋市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③[英]托馬斯·哈代.張玲,張揚譯.卡斯特橋市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④[英]托馬斯·哈代,張玲,張揚譯卡斯特橋市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⑤[英]托馬斯·哈代,張玲,張揚譯.卡斯特橋市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⑥[英]托馬斯·哈代.張玲,張揚譯.卡斯特橋市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⑦[英]托馬斯·哈代,張玲,張揚譯.卡斯特橋市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1]Williams,Raymond.Thecountryandthecity.New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1973.
[2]聶珍釗.悲戚而剛毅的藝術家[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
[3]陸揚.空間理論和文學空間[J].外國文學研究,2004(4):31~37.
(作者單位:赤峰學院大學外語教學部)
本文系全國高校外語教學科研項目:“空間理論視域下的哈代再研究“項目編號:NM-00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