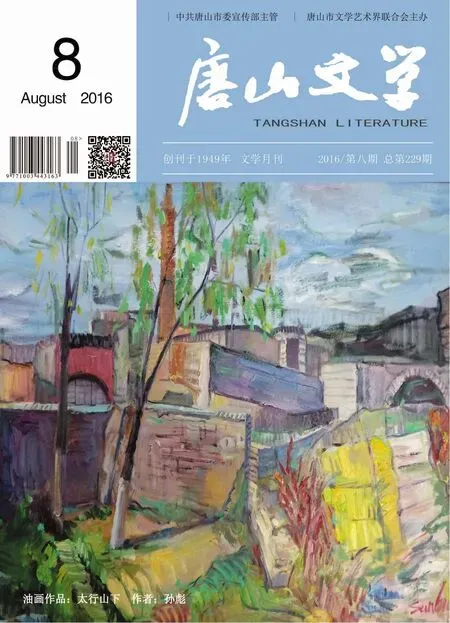《李娃傳》大團圓結局的民俗敘事
唐榮卉
《李娃傳》大團圓結局的民俗敘事
唐榮卉
《李娃傳》取材于市人小說《一枝花》,乃白居易之弟白行簡“應李公佐之命”而作。唐傳奇是中國小說發展的濫觴,含唐代文人“作意好奇”之蘊藉。王夢鷗稱之為“以史家筆法,傳奇聞異事。”魯迅有云:“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有意為小說。”白行簡為唐德宗年間進士,“行簡本善文筆,李娃事又近情而聳聽,故纏綿可觀。”《李娃傳》乃唐傳奇的中上之作,其寫的是狹斜娼妓的事跡,“完全擺脫了神怪之事,而以生動的筆墨、動人的情感來全力表現人世間男女之情,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虞初志》評其“此傳摹情甚酷”、“描畫細膩,有史遷之遺意”。
一、大團圓與民俗敘事的關系
大團圓結局是指通過“曲終奏雅”的形式在悲劇發展的最后加上一條“光明的尾巴”,此乃民族深層結構話語、一種“集體無意識”。王國維認為這種情節結構模式“代表吾國人之樂天精神者也”,魯迅也常常借助大團圓現象對中國國民性的缺失問題進行深度批判,所謂“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正如《李娃傳》中作為妓女的李娃與官宦書生滎陽生突破世俗禁忌的美好結局。事實上,唐代婚姻法對唐人愛情婚姻起重大作用的是良賤不婚和士庶不婚兩大原則,以及婚姻必須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三揖六禮的婚配程序。《戶婚律》(總一百九十一條)規定:“人各有偶,色類須同。良賤既疏,何宜配合”亦說明了此點。然白行簡創作的《李娃傳》卻突破了世俗禁忌,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按照鐘敬文對于民俗的分類,精神民俗是民俗中重要的一環,從民俗文化結構來看,其可分為表層的物質民俗文化、深層的精神民俗文化以及介乎兩者之間的制度民俗文化。就本質而論,它反映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人生哲學,充滿著人文關懷,滲透著人民群眾的愿望和期盼”,是他們的“宇宙觀與理想世界”的“書寫”。因此,民俗的敘事方式是以人生觀照為核心而形成的結構形態和邏輯關系。大團圓結局在中國古代敘述作品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隸屬于精神民俗范疇。
二、大團圓敘事文本分析
(一)全知之視角
男性第三人稱全知全能的敘述視角視野開闊,對時空延展度大、矛盾復雜、人物眾多的作品有天然優勢。《李娃傳》的主要情節就是從與李娃有戀愛關系的滎陽生的角度敘述出來的,而李娃的主要事跡及情感經歷則大半都是通過滎陽生的限知視點展示出來的,如初遇李娃:
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
少數由白行簡本人描繪,如結尾描述李娃封夫人前關于靈芝的敘事:
后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于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
敘述角度十分自由,不受限制,不受約束,作者處于一定的高度,無論是過去的還是未來的,無論是本地的還是異地的,作者都了如指掌,清清楚楚,敘述起來非常方便自由。這樣可喚醒讀者的再創造能力,拓寬想象空間。這是大多數傳奇采用此視角之緣由,同時也是李娃在結局處喪失話語權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跌宕之情節
當李娃被滎陽公“備六禮以迎”與滎陽生結成“秦晉之偶”后,白行簡似乎也自信不需要任何話語的點綴,僅通過自己冷靜客觀的敘述就足以使李娃這一形象成為真正的傳奇,促成大團圓敘事模式。滎陽生之父滎陽公阻止了滎陽生與李娃的分別,促成一段好姻緣。李娃與滎陽生的事跡被當時皇帝知曉,又是賞賜又是升職,李娃也被封為洴國夫人。此時再對比滎陽生落魄之時的慘狀:
被布裘,裘有百結,襤褸如懸鶉。持一破甌巡于閭里,以乞食為事。
真是“凄婉欲絕”,結局可謂曲終奏雅,敘事過程中情節的起伏變化一直在潛移默化地引導受眾,這種前后情節的突變得以構建一個完整的故事,作品先以公子金盡、 娼家絕情反轉了情節方向,繼而以李娃脫離娼門、孜孜勸學使敘事再度逆轉,于極盡跌宕之中兩度把個人從群體中區分出來,使離奇怪誕的情節想象在特定的語境中取得藝術的理性,使文本自足的事實斬斷與歷史的聯系,代之以藝術原則。正如明桃源居士所說:“唐人小說摘詞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白行簡在敘述的過程中加強了自身的控制力度,費盡心機,訴諸于虛構世界的愿望表達。
三、大團圓敘事探微
民俗之源上及原始遺風,在先民們創造的各類文化形態中,其深層無一不暗含他們對自身的思考。在民俗系統中,人生問題始終居于價值中心,成為凝聚民俗文化元素排列和組合的內驅力。
(一)文化心理結構
在中國民俗中,天人一體同構,天文與人文的相互交涉,猶如一股巨大的精神潛力推動著民俗運轉的軸心。這種調和意識與哲學思想“陰陽五行說”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庸之道”有著密切的聯系。“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張載《正蒙·太和》)中庸之道要求人們在處世行事時,允執其中,不偏不倚,凡事折衷調和大吉。(《論語·八佾》)對待不仁之人,也不能疾之太甚,否則就會產生禍亂。“圓”一詞大概是中國民俗文化里用意最廣泛也最美好的詞匯,代表一種圓滿意識,具有美好的意義生成。李漁在《閑情偶寄》中對“大團圓”結局作了如此描述:“(戲曲)全本收場,名為‘大收煞’,此折之難,在無包括之痕,而又團圓之趣。如一部之內,要緊腳色共有五人,其先東、西、南、北,各自分開,到此必須會合。”因此,對圓滿的迷戀是一種世俗之性,表現在戲劇中就是以苦開頭,以樂結束;以悲開頭,以喜結束;以逆境開頭,以順境結束。相互轉化的圓形結構在戲劇作品結尾洋溢著濃厚的樂和喜的大團圓色彩。
(二)創作意圖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和制約下,中國敘事文學注重信實,而信實之作又與儒家的道德思想存在一定不合之處,因此,中國古代作家常在敘事文學主體故事之外加上一個大團圓的尾巴,以實現懲惡揚善之目的,弘揚理想道德和理想人格,并使情感的發泄歸于中正平和,一定程度行沖破了灰色沉幕,給世俗青年男女以希望的火光及誘惑。《戶婚律》(總一百七十八條)規定:“妄以奴婢為良人,而與良人為夫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為妻、以婢女為妾者,徒一年半。”由此可窺見以妓女為妻實在不可想象。若李娃離開滎陽生回去重操舊業倒是非常符合邏輯,然而白行簡安排了滎陽公對于李娃身世的不介意,而是“命媒氏通二姓之好”,怕也是非常有遠見之舉。婚后李娃“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有四子,皆為大官,氣卑者猶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封建家庭嫡長為核心下這樣的局面似乎無從解釋。李澤厚稱此“是對有血有肉的人間現實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執著”,對門閥制度的戶婚律給予無情的嘲弄,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庶族欲打破森嚴門閥制度的愿望。
(三)審美接受
丹納有云:“如果一部文學作品內容豐富,并且人們知道如何解釋它,那么我們在作品中所找到的會是一種人的心理,時常也就是一個時代的心理,有時更是一種種族的心理。”因此大團圓的敘事不僅與創作意圖有關,更與期待視野有關,即所謂的審美接受。斯托洛維奇將藝術的功能分為娛樂、享樂、補償、凈化、勸導、評價、認識、預測、啟蒙、啟迪、教育、交際、社會化、社會組織等十四種。大團圓滿足了受眾某種補償心理,由于文學作品的情感特征和理想品性,使得文學閱讀成為滿足人們情感補償的最理想的方式之一,人的審美需要促使人通過審美鑒賞活動得到一種“想象的滿足”,心理和情感的補償就有了陶冶和凈化的作用。從而借文學之“圓”彌補生活之“缺”,使飽受苦痛的人們心理得到撫慰與平衡,從而達到對痛苦的“坐忘”與“心齋”,這也便是中國古代大團圓審美心理找到了適宜它衍生的溫床。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 410082
唐榮卉,女,漢族,湖南大學2014級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