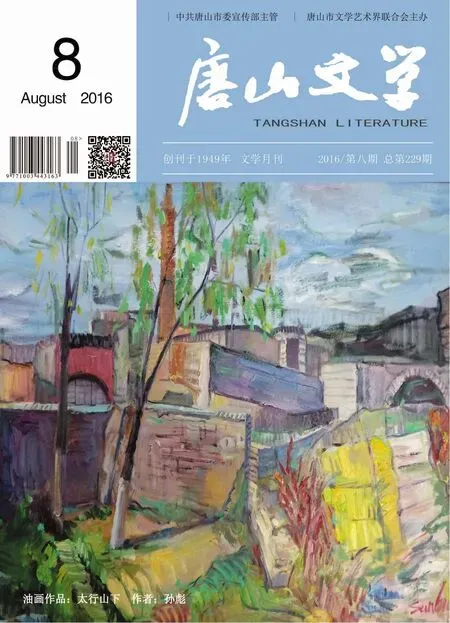淺析西方繪畫對當代工筆人物畫的影響
王 穎
淺析西方繪畫對當代工筆人物畫的影響
王 穎
人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豐富,思考的問題也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越來越復雜。藝術家們想要表達的情感、內容也豐富起來。以往的繪畫題材與主題已經不能滿足藝術家們對生活、生命的表達和探索。畫家們受到西方的啟示,開始關注生活本身,生活狀態,對人生的思考,生活中的小情節、小情趣。如畫家張見的作品描繪當下人們迷茫的心理,對藝術與人生的思考,情色,同性戀等。很多畫家會關注到農民,關注到社會上的少數人,如李傳真對勞苦農民工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的描繪。女孩梳妝,工人回家,鬧事買賣,拍攝現場等都成為畫家筆下的一幅幅作品。
工筆人物畫的發展,使傳統的構圖不能滿足當下多元的工筆人物畫的表現。西方藝術的沖擊,帶來新的啟發。在繼承傳統精髓的基礎上融入焦點透視的規律,平面構成意識、非完整性形象、滿構圖的運用使工筆畫滿足當代人的審美觀念。張見的繪畫就是很好的典型,他用植物或幕布或其他對畫面進行分割,使畫面達到某種審美規律,而極具現代感;畫面中的人物形象借鑒了很多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作品,將古典美與現代感協調在一個畫面中,同時又具有中國畫的神韻。《黑晝》以平面構成的方式對畫面進行空間切割,傳遞出多維空間。《失焦》用一個不完整的形象,描繪一個社會群體的矛盾、焦躁甚至迷失的生活狀態。徐華翎的大部分繪畫作品中運用到了不完整的人體,營造出女性的一種純凈,神秘,朦朧的美。羅寒蕾也曾畫過一段女人體,變現女人的柔美。鄧先仙的《霧茫》,蘇茹婭的《夏至》都是滿構圖的作品,畫面飽滿,給人很大的視覺沖擊力。
為了使畫面更加協調,畫面當中的用線也得到了一定的改變。有人看來工筆畫缺失了線就不再完整,而張見說:“線在我的認識里,首先是一種表現手段,其次它可以被人上升到一種文化的高度。線之于我的意義在于:它是手段,是目的,而最終它是手段和目的的統一。有什么樣的線,就有什么樣的畫面效果。一味強調“線”本身,它已經嬗變成一種功能性目的了!而我們,需要在“線”之外,看到更多豐富的東西,而它首先是作為主體精神承載物的語言方式而已!這種具有生命意識的線,是傳統中國畫的精髓。”在徐華翎的畫中,剛開始的畫面中線條弱化,后來不再用線,朦朧的,夢幻的,沒有界限的人體,就像是青澀少女的情竇初開般美好。羅寒蕾的繪畫作品注重用線,她用精悍的線條變現出人體結構和衣紋走向,并結合對線淡淡的渲染讓線條結合進人體當中,成為畫面中人體的一部分。魏恕壯女系列頭像作品為了使畫面更具寫意性,用線看似隨意實則用心,略粗拙的線更好地體現了活躍在各行各業外表時尚,內心淳樸的壯族女孩們。蔡曉滿的《戲》畫中圓滾滾的線條配上老人們一張張入戲的臉和有趣的神情,韻味十足。
“隨類賦彩”是傳統中國畫的設色思想,以物體的固有色為主。近代以來吸收了西方的設色思想,加入了環境內色和光源色,也注意到色彩的明度,純度,冷暖對比,光影,還有以作者的主觀意向為主進行設色的,使畫面更為豐富,也能更好地適用于多元化的工筆人物畫中。不管畫面中是以強烈的對比色求得裝飾性和沖擊力,還是在和諧的同色系色彩中尋找細微的變化,求以畫面中朦朧淡雅的詩意,都是以畫家敏感的美的感受和傳統繪畫思想為基礎的。羅寒蕾的繪畫作品大多以黑白灰色彩為主,在整個灰色調子里少許的色彩,使畫面靈動又富有生機。金瑞的《鐵馬冰河之戰圖》以絢爛的背景色,色彩雖亮麗卻降低了色彩的純度以反襯畫面中淡雅安靜的赤足少女,這樣的配合讓畫面色彩豐富,卻也清新雅致。劉金貴《節日的山村》整幅畫面統一在喜氣洋洋的紅色調子里,并在紅色中找細微的差別。穩重大氣的紅色,讓畫面穩定且有沖擊力,讓強烈的裝飾味和深厚國畫韻味并存,充滿活力。
光與我們每日相伴,但在西畫傳入之前幾乎沒有人將其運用的繪畫當中。維米爾《倒牛奶的女仆》中從窗中散入屋里的柔和日光。倫勃朗畫面中最典型的特征是運用一道明亮的光束將黑暗的場景顯示出來。西方油畫在畫面中對光線的運用比比皆是。近代以來通過對西畫中用光的學習,出現了很多對光線運用自如的當代畫家。田黎明繪畫中可看到西方印象派作品中光斑的效果,他的畫面中滿是柔和的光與影的變幻,能感受到純凈、清亮的生命力的跳躍。在鄭慶余的作品中對光影的運用尤為常見,他的人物的刻畫往往帶有明暗交界線,畫面中又放置了窗或門,光從中穿過照在人和物上,呈現出半透明的狀態,有時畫家會畫出人或物的影子。畫面中的光或月光,或晨光,或夕陽,或燈光,或頂光配上半透明的人物,動物,景物,有一種亦真亦幻,亦虛亦實的感受。又像流沙逝于掌心,越是美好越是想要抓住的,卻越是留不住。
工筆人物畫壇一片欣欣向榮,其中還有很多問題等著畫家們探索,怎樣才能讓工筆人物畫既有中國韻味,又越來越豐富多彩,是一個問題。
作者單位:廣西藝術學院 530022
王穎(1990—),女,漢族,河南平頂山人,廣西藝術學院2014級中國畫人物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