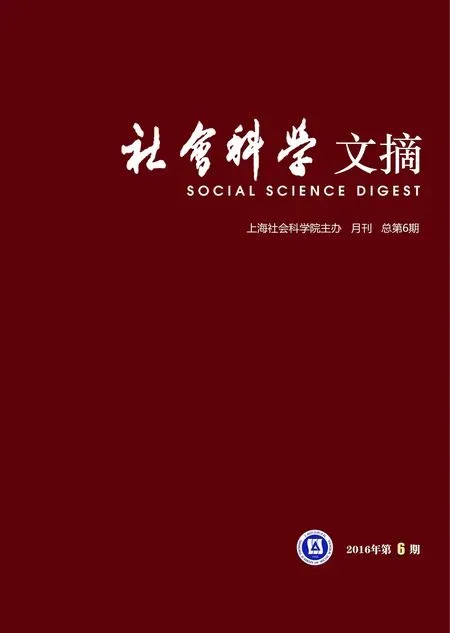《民法典》立法背景下商行為的立法定位
文/王建文
《民法典》立法背景下商行為的立法定位
文/王建文
因我國《民法典》客觀上不可能涵括基本商法規范,且因完全涵蓋總綱性商法規范將嚴重破壞民法總則及民法典整體上的邏輯性,故我國總綱性商法規范的最佳立法模式為制定獨立于《民法典》的形式商法(既可為《商法通則》,亦可為《商法典》)。但鑒于《民法典》立法工作已啟動,若能在《民法典》中制定關鍵性總綱性商法規范,亦可起到應急立法的作用,一方面可解決總綱性商法規范長期缺失的問題,另一方面可為我國形式商法的立法確定基本的法律依據。我國在《民法典》立法背景下總綱性商法規范的立法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其中商主體與商行為的立法定位尤為迫切。為此,筆者曾在《我國商法引入經營者概念的理論構造》(載《法學家》2014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我國商法應引入經營者概念,使其作為商主體概念的替代,算是筆者對商主體立法定位問題的回答,故本文僅針對商行為的立法定位展開研究。
商行為的特殊性:商行為特別調整的內在原因
基于商行為的商事法律關系的特殊性決定了商行為獨立存在的依據。依此,從法律概念的邏輯關系上講,法律行為固然可謂商行為的上位概念,但實際上這種理解并不完全準確。不僅法律行為不能取代傳統商法中的商行為概念,而且因現代市場經濟中各種新型商行為的特殊性更為明顯,甚至遠遠超出了法律行為理論的基本框架,故只能適用商法的特別規定,而不能直接適用民法中法律行為的一般規范。例如,商事實踐中廣泛存在的決議行為,就不能簡單地適用法律行為的一般規范,其與共同行為及合同行為均有實質性區別,關于決議行為的成立、生效、可撤銷、無效的判斷都不能簡單地套用法律行為的一般規范。因此,即使我國民法典總則中特別在“民事法律行為”制度中規定決議行為,也因其與法律行為的理論體系存在天然的區別,而難以在兩個概念之間形成邏輯自洽。
與民法上同類性質行為的規定相比較,商法關于商行為效力判斷的規范更為嚴格。契約法的一般規則的某些方面在商法領域得以改變。流質契約之禁止是民法的重要規則,但在商法中并不禁止。作為一項特殊的商法規則,商行為的短期時效制度值得一提。由于商事交易追求效率,往往要求迅速了結商事交易中的糾紛。因此,為滿足交易迅速、便捷的要求,立法多采取短期時效制度。
在我國,因《民法通則》《合同法》等基本民法規范都采取的是民商不分的立法模式,故不存在上述立法上的區分。但這種民商不分的混合立法模式,已出現了明顯的“商化不足”與“商化過度”的弊端,既無法適應商事法律關系的調整需要,又不當地將僅適用于商主體或商行為的規范泛化為統一適用于所有民事主體的一般規范。在我國民商事司法實踐中,諸如表見代理是否成立、公司非經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對外擔保的法律效力、民間借貸的舉證責任等法律糾紛往往存在同案不同判的問題,其原因就在于法官或仲裁員對這些法律關系中一方當事人是否為商主體及其行為是否為商行為有不同認識。若法官或仲裁員認識到商行為的實施主體應承擔嚴格的注意義務并對其舉證責任賦予更高要求,則在判斷相對人是否為善意時,就會形成不同的判斷標準,從而產生大相徑庭的裁判。
綜上所述,可以肯定地作出判斷:盡管法律行為乃商行為的制度基礎,但因商行為具有不能為一般法律行為制度所包涵的特殊性,故只有單獨確立商行為制度,才能妥善調整基于商行為而發生的商事法律關系。
商行為概念界定的域外立法經驗
客觀主義立法例(以法國為代表)根據法律行為的客觀內容來判斷其行為是否屬于商業性質。法國商法形式上以“任何人均有權從事商行為”為指導思想,實際上則以營利性為判斷商行為的實質性要素。就現行客觀主義立法例而言,西班牙商法是這一立法例真正意義上的代表。《西班牙商法典》第2條第3句規定:“符合本法典和其他商事法律規定的,均應推定為商事行為。”
在主觀主義立法例(以德國為代表)下,只有商人雙方或一方參加的法律行為才屬于商行為。“行為”“商人”“商事營業”是德國商法中商行為概念的基本要素。簡單地說,商行為包括兩個構成要件:商人身份和有關行為屬于經營商事營業。
折中主義立法例(以日本為代表)采取了主觀與客觀雙重標準來概括商行為概念。詳述之,商行為的概念既包括任何主體從事的營利性營業行為,即客觀商行為;也包括商人從事的任何營業活動,即主觀商行為。這一立法例為多數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所采行。
通過上述立法例與學理的考察可知,無論采行民商分立立法例還是民商合一立法例,大陸法系基本上都注重對商行為概念予以抽象概括;而采取經驗主義立法原則的英美法系則不注重對作為法律行為下位概念的商行為予以抽象,如《美國統一商法典》對各種商業交易行為作了詳細規定,但并未予以概括性描述。盡管有學者認為,根據該法規定可以推定,美國商法中商行為是指商人所實施的商業交易行為,但這種概括顯然與立法上的定義相去甚遠。
我國《民法典》中商行為概念界定的立法選擇:經營行為概念的采用
在我國《民法典》制定中考慮商行為的概念選擇及界定時,應充分考慮我國市場經濟實踐中需要對其法律性質予以認真思考的若干問題。為此,需要超越傳統商法典關于商行為界定的束縛,對我國商行為的法律界定作必要創新。
商行為法律界定的核心要素應為“以營利為主要目的”,以便適應現代商事交易日益泛化的時代背景。在具體概念的確定方面,筆者認為,與放棄傳統商法中的商人概念相適應,不妨放棄與商人概念相對應的商行為概念。那么,如何選擇替代概念是個問題。鑒于筆者提出可立足于我國現有立法資源將“經營者”作為我國商法中商人概念的替代性概念,故應考慮立法上相對應的概念能否成為我國商法中商行為的替代概念。就此而言,盡管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價格法》《產品質量法》《反壟斷法》《食品安全法》《侵權責任法》等法律已明確采用了經營者概念,且《反不正當競爭法》《價格法》《反壟斷法》等部分法律還對經營者概念作了明確界定,但有的未確定經營者對應行為的概念,有的雖確立特定概念(如經營活動、經營行為)卻未作明確界定。因此,我國現有立法資源無法為商行為的概念選擇提供有力支持。筆者認為,鑒于商行為乃法律行為的下位概念,故不宜將“經營活動”確立為我國商法中商行為的替代概念,而應引入“經營行為”概念。筆者認為,可將經營行為作如下界定:經營行為是指以營利為主要目的而實施的行為;企業所實施的行為視為經營行為,但明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除外。
至于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的解釋,無需也無法通過立法明確界定,由司法機關、仲裁機構及行政機關根據具體情形自由裁量即可。就具體形式而言,鑒于提高法律適用的統一性之考慮,建議通過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司法機關及行政機關的法律條文釋義等方式提供法律適用指引。
結語:我國《民法典》中經營行為的立法構想
在我國《民法典》立法中,若擬就總綱性商法規范作專門規定,則建議對經營行為作明確而簡單的規定。易言之,我國《民法典》不必對種類繁多的經營行為作具體規定,只須就不同類型的法律主體所能實施的經營行為范圍分別作出相應的明確規定,從而明確經營行為的實施主體類型及其所能從事經營行為的具體范圍,解決經營行為的法律適用問題。對于那些在體系上應納入經營行為范疇,但在立法上則又應當單獨立法的經營行為,如銀行行為、票據行為、證券投資行為、期貨交易行為、信托行為等則只需在商法中就其法律屬性與商法上的特殊法律適用予以規定即可。
在經營者與經營行為之間的關系方面,可作如下構想:因經營行為而發生的法律關系均受商法調整,經營行為的實施者即為經營者;企業作為從事營業性經營活動的特殊經營者,其所實施的行為一般可推定為經營行為,但明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行為除外。基于此,可對我國《民法典》中經營行為的一般規定作如下構想:
第X條 因經營行為而產生的商事關系,適用本法(章)規定。
本法所稱經營行為,是指以營利為主要目的的行為。
本法所稱經營者,是指經營行為的實施人。
依法設立的企業是法定經營者,其所實施的行為可推定為經營行為,但明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除外。
當然,我國《民法典》即使對經營行為作了上述規定,也僅能起到形式商法缺失背景下的應急立法作用,若要徹底解決我國總綱性商法規范的立法需要,仍應制定形式商法才能有效解決。至于該形式商法是《商法典》還是《商法通則》,筆者認為應對具體立法形式作深入、系統的研究,在法學界尤其是商法學界形成基本共識后再作抉擇。目前商法學界亟待解決的問題是,立足于我國市場經濟實踐及商事司法實踐,系統論證總綱性商法規范單獨立法或特別立法的必要性,確定關鍵性條款,并在條件成熟時提出體系化的商法規范立法建議稿,從而為我國總綱性商法規范及形式商法的立法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律與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摘自《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6年第1期;原題為《論我國〈民法典〉立法背景下商行為的立法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