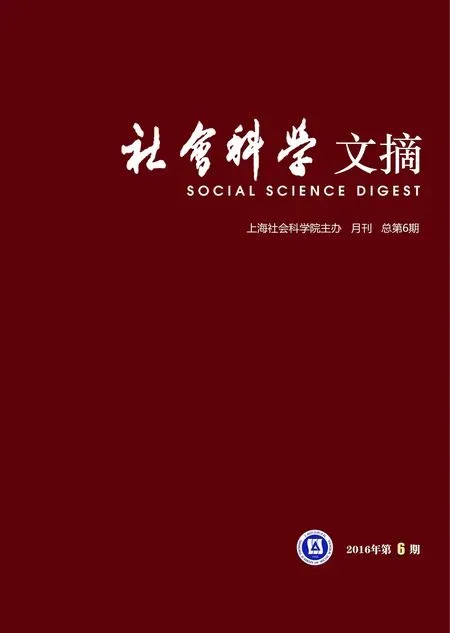自由的歷險
——從“德國觀念論”到《資本論》
文/白剛
自由的歷險
——從“德國觀念論”到《資本論》
文/白剛
追求人之為人的“自由”是自啟蒙時代以來西方哲學的主流,也特別成為從“德國觀念論”到馬克思《資本論》發展的主題。
自由的“虛化”:德國的“觀念論”
在根本而重要的意義上,可以說“自由”就是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建構其理性大廈的“拱心石”。對康德來說,自由一詞的最根本含義就是理性的自主。人們只有遵循理性法則而非啟示和自然傾向,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在此基礎上黑格爾認為,盧梭已經把自由提出來當作絕對的東西了,而康德也提出了同樣的原則,不過主要是從理論方面提出來的。康德主張和強調的主要是實踐理性領域的“意志自由”:意志的本質就是自己決定自己,當意志自己決定自己時,它便是自由的。正是在康德哲學那里,古老的超越和救贖思想被轉譯進了生活于現代世俗社會之市民的理性自由當中。在此意義上,對人類文明發展具有重大世界歷史意義的法國大革命,正是高舉康德理性自由大旗和高喊康德意志自由口號的偉大壯舉,因而康德的自由思想也就成了“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馬克思語)。但在馬克思看來,自由決不是空穴來風和單純的理性自覺,它的發展是與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階級利益追求密切相關的。雖然康德的理性自由具有重要的思想啟蒙的意義,但在康德這里,表達人之為人的主體性的作為人為道德立法的意志自由,雖然擺脫了上帝和靈魂的統治,但仍然缺少落到實處的堅實的物質基礎,自由在他這里仍然停留在精神和意志的道德實踐領域,依然飄浮在半空中,自由仍是“虛化”的。
作為德國觀念論的集大成者,黑格爾雖然對康德哲學有諸多批判,但在追求自由問題上,黑格爾卻是康德的繼承人。在康德的基礎上,黑格爾明確強調自己哲學的主題就是“精神自由”。在黑格爾這里,自由不再僅是道德實踐領域的“意志自由”,而是處于世界歷史的展開過程中。自由的最高表現就是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和自我發展:自由乃是不依賴他物,不受外力壓迫,不牽連在他物里面;只有在思想里,而不是在任何別的東西里,精神才能達到這種自由。在此基礎上,世界歷史也無非是“自由意識”的進展,而資產階級國家正是自由的實現。在黑格爾這里,自由作為理性的本質是最高的東西,是“精神的自覺”和“觀念的自足”。在此意義上,我們說黑格爾通過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實現了理性與現實的和解,達致了個體理性認同普遍理性的“精神自由”。黑格爾曾批評柏拉圖在理性確定性的祭壇上犧牲了自由,但不幸的是,黑格爾本人的絕對精神也犯了類似的錯誤。
在馬克思看來,德國觀念論對自由的理解固然博大精深,但根本上仍然是一種浪漫主義的精神幻想。它沉迷于其哲學浪漫史的國度里無法自拔,以至于德國觀念論將自由表述為自我意識的歷史顯現。也就是說,它的自由觀念“依然停留在一種更為精致的形而上學的或意識形態的層次上”。所以,德國觀念論雖然高揚了自由的大旗,但由于它忽視或貶低了自由的物質基礎,它只是達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伽達默爾語),只能給予人們一種關于“自由的幻象”,而不能獲得“真實的自由”。
自由的“物化”:斯密的《國富論》
在自由從天國到塵世的轉變過程中,與康德同時的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功不可沒的。可以說,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德國觀念論面臨著一個共同的任務,那就是爭取和實現人的自由。《國富論》的出版,使斯密既成為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也成為了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原則的首創者與主要闡述者。如果說,康德是第一位新興資本主義秩序重要的“哲學代言人”,那么斯密就是第一位新興資本主義秩序重要的“經濟代言人”。斯密的自由思想與霍布斯和洛克的個人自由主義的英國傳統相一致,是一種“自然自由”傳統。這一傳統認為,個人在自然自由制度中具有某種自然的權利,并可以尋求經濟上的自利目的。也就是說,斯密通過在其經濟學中確立的財產權的自由和貿易(交換)的自由,保障和實現了現實的自由,自由第一次在世俗世界的現實經濟事務中得到了經驗化和實證化的“感性顯現”。在斯密這里,主體的“物化”——商品化、貨幣化和資本化,也就是實在的自由。在此意義上,美國政治哲學家克羅波西認為:“正是由于把希望過得更好的欲求作為替代對暴力死亡的恐懼來作為人的主要激情,亞當·斯密完成了霍布斯體系的自由主義化和商業化。”所以說,正是通過古典經濟學的產業化和商業化,斯密才第一次創造了一種可能性,即從經濟領域突破一切觀念性和虛幻性的自由。這是因為只有在這種人為的經濟和商業活動中,人才獲得了一種世俗的自由空間。
但作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者和超越者的馬克思,還是在斯密所謂的“物化自由”這里,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競爭的形式自由背后掩蓋的實質不自由。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明確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商品交換過程中所體現的自由和平等的形式性和虛假性:“在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總體上,商品表現為價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的背后,在深處,進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個人之間這種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這實際上就是盧卡奇所指出的,在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中,個人的自由仍受他自己所創造的、包圍自己的作為商品世界的“第二自然”制約。因此,在資本主義商品交換體系的控制下,那些看似是拓展和實現自由、平等和所有權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的東西,最后卻都以作為對自由之選擇范圍和實現形式的總體限制而告終。也就是說,正是資本主義的“第二自然”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爭得的自由。所以在《國富論》這里,雖然自由從“虛化”的“精神自由”走向了“物化”的“經濟自由”,但物化的“經濟自由”也仍然是不自由的。
自由的“現實化”:馬克思的《資本論》
作為馬克思自由思想來源的,不僅有德國觀念論的精神和意志自由,更有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生產和交換自由。特別是馬克思在現代自由主義思想中半隱蔽的“孕育”階段,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和斯密的《國富論》,就包含在其起源歷史的兩個最重要方面當中。在馬克思這里,古典哲學和古典經濟學的自由并沒有完全遭到否定,而是被揚棄和超越了,轉變和提升為了一種更高層次的人之現實性的自由。在馬克思自由思想的形成過程中,他把古典哲學的“精神自由”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自由”作為一種“啟示”接受并汲取了其主要思想。正是通過《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將取自古典經濟學對自由的物質化論證與古典哲學的觀念化想象結合了起來,實現了對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哲學分別表征的資本主義社會“自由”之“經濟發展”和“理論架構”的雙重批判,意識到了“人之自由”還處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物化結構”和“意識形態”的雙重束縛當中,這實際上就是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因此,人類解放所要求的自由是從自我意識中解放出來的自由,而不是“自我意識的自由”;是從資本中解放出來的自由,而不是“資本的自由”。
從《論猶太人問題》到《資本論》,馬克思所追求的決不是“復制貧困”和“復制剩余價值”,而是在擺脫貧困和消滅剩余價值的基礎上,復制和創建“現實的自由”。所以馬克思才在《資本論》中強調:自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因此,“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只有在此基礎上,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由此可見,馬克思主張的是在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通過“聯合起來的個人”共同占有生產資料而“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來徹底揚棄和超越德國觀念論飄浮在半空的“虛化自由”和古典經濟學剛剛落地的“物化自由”,實現“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真實自由”。唯此,方能以現實的個人自由取代抽象的觀念自由和資本自由,使本來存在于“必然王國”彼岸的“自由王國”此岸化。所以說,馬克思自由之偉業的核心,就是將來自古典哲學和古典經濟學共同的“理性自由”當作其絕對進路,在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所有權”的三位一體的基礎上,追求和建構“個性-自由-解放”新的三位一體的“自由王國”。但這一“自由王國”,決不是古典哲學和古典經濟學自由的“拷貝版”,而是它們的“升級版”。在此基礎上,我們確實可以說: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的《資本論》已經由關于“物”(商品、貨幣、資本)的科學,轉變為了關于“人”的自由解放的學說。從德國的“觀念論”到斯密的《國富論》再到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邏輯進程,實際上也是自由從“虛化”到“物化”再到“現實化”的推進過程。正是在這一推進過程中,自由才真正獲得了新生。
(作者系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摘自《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