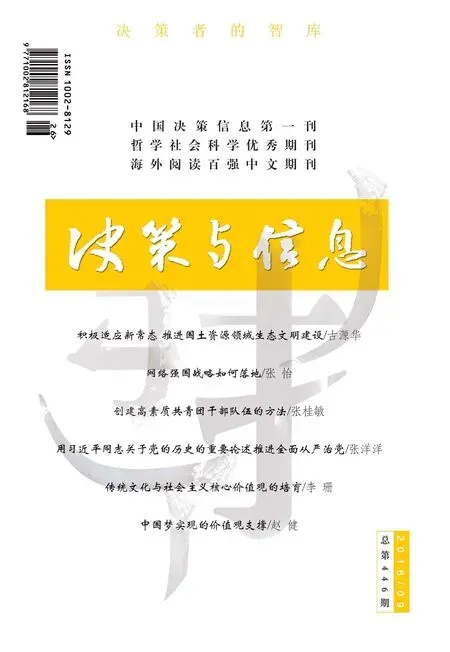探討文化對國際政治學者的積極影響
劉廣宇
國際關系學院 公共外交與文化傳播 100091
探討文化對國際政治學者的積極影響
劉廣宇
國際關系學院 公共外交與文化傳播 100091
文化對國際政治無疑具有積極的影響,不論是在克服“哈耶克陷阱”方面還是在避免國際政治淪為“經(jīng)濟現(xiàn)象”方面都發(fā)揮著其重要作用。對于政治學者而言,文化更是提升個人情懷、擴展學術視野的橋梁。
文化;國際政治;借鑒
每當一提起國際政治,人們往往會想起縱橫捭闔、嚴肅冷峻的政治人物或者以國家為單位吹胡子瞪眼式的權力爭奪。而一說到文化,則常常會浮現(xiàn)出溫文爾雅的君子形象。那么,正如世界上有不同膚色的人種一樣,國際政治和文化之間真的是兩種不同的“人”嗎?還是由于在不同領域框架下相互隔閡的“幻覺”?本文就試著探討一下國際政治學者能從文化中獲取哪些積極效果。
首先要說明的是“文化”的定義。說這個詞的解釋有千百種那都不為過,然而如果大而化之的認為“文化即人化”,那么這種作為全人類的總和的概念,就是只可意會不的存在了。但是除了最廣義的文化定義,相對于國際政治的實踐性而言,文化就是包括文學、藝術、哲學、意識形態(tài)等的側重于精神層面的人類思想結晶。雖然這樣的分類,從理論上將把政治和文化相互區(qū)分,但是實際上作為二者主體和統(tǒng)一體的人,兩者的相互借鑒是在一個環(huán)境中產生的,這取決于有沒有相互聯(lián)通的意識和橋梁。而要構建起這樣的聯(lián)通,首先就要明確文化和國際政治間的一些區(qū)別。
一、從國家層面對比文化與國際政治
兩者的對比角度可謂多種多樣,但是作為實踐或精神的活動,則必須要有環(huán)境、主體、客體(目的)以及實踐方式等基礎性因素。基于此,二者的對比關系也將分這幾部分進行說明。
目前關于國際關系環(huán)境的一個關鍵詞就是“沖突”。不論是把國際關系看作是國家間的“游戲”還是權力爭奪,無時無刻不伴隨著沖突。不論是霍布斯還是荀子都對“沖突”問題給予極大關切。假如國際社會是像老子設想的那種“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tài),那么就不會有關系發(fā)生。而一旦主體間相互接觸那么由于資源的分配不均、各國家需求多元,沖突在所難免。所以政治人物始終要面對的就是這種復雜的局面。國際政治常常將國家看作是有機體,不發(fā)展、不去爭奪生存的權利,國家就會衰亡,這種觀念和地緣政治學密不可分。德國地理學家弗里德里希·拉策爾作為地緣政治學的鼻祖,創(chuàng)立了國家有機體和生存空間學說。他將一個國家看作是一個人,都需要生長和自由進取,這種生長、斗爭、演變和衰亡的過程,深深印上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痕跡。政治人物作為本國的守夜人,時時刻刻要盯著國家的生存狀況,警惕國家的安全環(huán)境。而文化則無須這種精神緊繃,其所面臨的基本上是自由寬松的國際環(huán)境,“交流”是這個領域的關鍵詞。任何一種文化都不能獨立存在而發(fā)展,自我更新都需要新鮮的空氣,所以文化是最容易跨越國界的領域,劍拔弩張的情況在文化中很少見。
從主體性來看,文化的長處在于多樣性,而國際政治長于統(tǒng)一。之所以人類發(fā)展到如今如此高度的精神文明,多樣性扮演了極大作用,這種多樣性為文化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多維的可能,其張力是全方面的。反觀國際政治,國際上某項國際事件的參與主體越多,其中的紛爭就越難解開,多樣性也是模糊性,而這也恰恰限制了政治人物的眼光。馬克思·韋伯說政治人物應該具備三種基本素質:熱情、責任感、判斷力。然而任何一個杰出的政治家必然要有前瞻性,這種眼光不要求有文化特性那樣的探求人類發(fā)展的終極奧秘的長度,而是能在一定時期的局限內作出超越本階段的舉措。所以政治家的頭腦必須是開放多樣而又明晰的,才能在眾多可能中合理的選擇。而為國際政治所驕傲的——理性,往往又容易落入怪圈——“哈耶克陷阱”。哈耶克陷阱就是“理性”的異化,即人類對自身擁有完全理性能力的“幻覺”和盲從。理性實際上只能有限的解決可控因素,但是不可控因素在整個人類過程中占比要遠遠大于可控因素。例如對“民族利益”的理解,它雖然是衡量政策的必然標準,但是實際上政治家很難在某一時刻決定它到底意味著什么。政治家的眼光不是單靠理性就能解決的,必然要有文化的影響,加入感性的因素,從文化中把握歷史的脈絡,從而獲得超越現(xiàn)階段的效果。
從目的性來看文化和國際政治就會發(fā)現(xiàn)二者相互對應關系:人文情懷與現(xiàn)實主義的碰撞、理想和實踐的交織。一個是散射式的尋求社會真理,一個是直線式的直達目標。然而兩者的矛盾焦點并不在于散射和直線的不同方向,而在于國際政治中的“經(jīng)濟現(xiàn)象”,即在零和游戲規(guī)則中對利益的錙銖必較、成本的精確計算以及討價還價。但是政治實踐必須現(xiàn)實,國際政治必然牽動國內政治,國民不會因為國家提出的某項萬年計劃而動容,必須在短時期或較短時期內見效,這樣國家才會有持續(xù)的權威。文化就不必如此,文化的綿延不用為眼前所困,基本上只要有人就有文化的傳承,就像猶太人千年文化流傳至今那樣,而當一國的文化感到危機時,實際上往往是政治危機,正如五四運動始于拯救傳統(tǒng)文化危機而終于政治革命一樣。文化縱然也是現(xiàn)實的存在,也想發(fā)揮實際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實踐性不強、縹緲,只能慢慢發(fā)酵,不能像疾風驟雨的政治執(zhí)行力相抗。也正是過程的緩慢致使文化能充分地不斷變化,最終沉淀為適應人類生活的模塊。
然而,經(jīng)濟并不是政治的唯一度量或是根本存在標準,在《爭論中的國際關系》一書中,作者就明確表示不能將政治現(xiàn)象和經(jīng)濟現(xiàn)象互換,政治決定和個人以及商業(yè)公司的決定方式有著天壤之別。如果單單從利益的角度來看待或從事國際政治,未免太過于簡單,國家畢竟不同于公司,國家的存在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tǒng),所以誰能全面審慎地看出問題的癥結誰就能誰就能做出不小的成就。從這點來講,文化無意間給了國際政治非功利性的思考問題的態(tài)度。
二、從個人層面來看文化對政治人物的積極作用
文化不僅在國家層面能給予國際政治以“另類”思考,同時也在幫助政治人物開辟學術或實踐的新天地。有人說,政治是門藝術,的確幾乎所有的人類活動都有藝術形式。但是藝術并不代表國際政治承認了文化的地位,一般大家都會寫從文化來看國際政治諸如此類的文章,而很少寫從國際政治來看文化的,這就間接反映了人們依然習慣于文化從屬政治的思維方式。所以,所謂的藝術也只是在技巧方面而非在文化性方面。中國古代《大學》中有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道路,其中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就是說明知識和文化修養(yǎng)對政治的重要性。毛主席作為一個杰出的政治領袖,文化修養(yǎng)發(fā)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對中國文化都有著很深的體會。在他身上兼具詩人的浪漫氣質和政治家的機敏,深知中國文化中農民、工人的想法,在幾次圍剿之后最困難的時期仍然保持詩人般的積極革命情懷,最終推動革命一步步向前。
文化除了對政治家個人的情懷注入積極的精神力量,同時也推動政治領域學術的發(fā)展。作為一流外交政策專家,美國對外關系文員會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沃爾特·拉塞爾·米德,運用文化的角度來解析美國的外交傳統(tǒng),成功的樹立了美國外交政策傳統(tǒng)的自信,反擊了俾斯麥所說的:“上帝對傻瓜、醉漢和美國給予特別的保佑”。他在《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一書中總結出美國外交政策四個學派:漢密爾頓主義、杰斐遜主義、杰克遜主義和威爾遜主義,讓美國人在審視自身的外交政策時有了更深的認識。同樣注重文化因素而成就自己學術地位的還有小約瑟夫·奈,他的“軟實力”理論,將文化這種軟實力提升到了和軍事、經(jīng)濟等硬實力相當?shù)牡匚唬岢隽诵率兰o美國如何維護自身地位的解決路徑,從而影響希拉里進行“巧實力”外交。可見不論是在研究方法還是理論建構方面,文化越來越受到國際政治的重視。
三、總結
文化不僅對宏觀的國際關系產生新思路,同時也提供給政治學者、政治人物以積極的個人情懷和廣闊的學識空間,文化的作用越來越為人所認識。然而,這對以權力和利益為核心的現(xiàn)實主義國際政治分析方法并不構成挑戰(zhàn),國際博弈仍在持續(xù)。作為社會精英,每個政治學者幾乎都不缺乏文化的熏陶,關鍵是如何將這種人文情懷以多大比例融入到政治中去。或許美國威爾遜總統(tǒng)在處理一戰(zhàn)后事務中提供了不成功的實踐,他提出的十四點計劃在國際上并不被克里蒙梭、勞合·喬治所重視,美國國內也沒有通過加入國聯(lián)的議案。但他之后卻被評為與林肯比肩的總統(tǒng),其執(zhí)政思想中所蘊含的理想主義的文化因素現(xiàn)已成為美國外交的寶貴精神財富,文化在政治領域的張力的確值得深入研究。
[1]劉雪蓮.地緣政治學[M].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2]郭小聰.守夜人與夜鶯[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5月版.
[3]趙汀陽.每個人的政治[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1月版.
[4][美]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M].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1月版.
[5][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