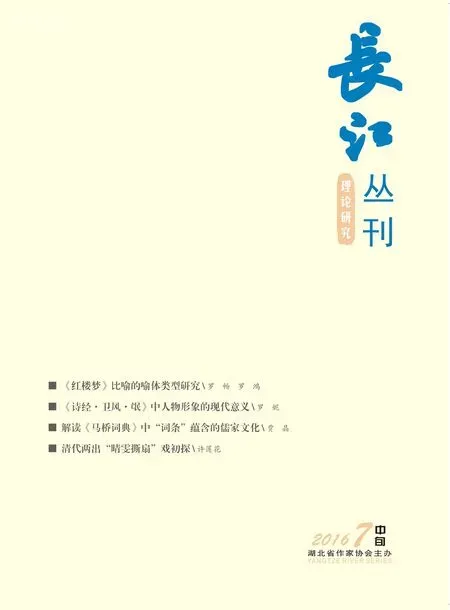淺淡關于《橘頌》篇的一些問題
武國強
淺淡關于《橘頌》篇的一些問題
武國強
《橘頌》作為中國古代文人所作的第一首詠物詩,在我國詩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屈原《九章》中的名篇,也是其代表作品之一,它突出而生動地表現了屈原高潔、堅貞的人格和志趣,千百年來詩人借橘樹所表達的熱愛故土、正直孤傲、樂觀向上的精神一直為后人稱道;但是關于它的誕生時間、創作主旨、象征意義,至今學者們的觀點仍有分歧。本文通過梳理相關文獻研究,旨在進一步明晰有關《橘頌》的一些問題。
橘頌 九章 屈原
一、再論《橘頌》的產生時間
關于《橘頌》產生的時間問題,學術界存有早、中、晚三說,目前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是屈原早年的作品。如明代著名學者汪瑗在《楚辭集解》里說:“但此篇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后所作者也。”汪瑗雖未明言是屈原早期作品,但已開始質疑《橘頌》非其放逐后之作。清人陳本禮言:“原之頌橘……余細玩其詞,蓋早年童冠時作也。”(陳本禮在《屈辭精義》)陳本禮直接肯定說此詩是屈原早期作品,并推測是“童冠時作”。這些觀點都為后人提供了有力的借鑒。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橘頌》是屈原放逐江南后所作。自王逸以降,洪興祖、朱熹、林云銘等人均主此說,如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橘頌》作為《九章》中的名篇,在王逸看來無疑也是其放逐后所作。洪興祖繼承了王逸的觀點,朱熹對此雖稍有異議,但他也認為《九章》出于屈原放逐之后,只是非“一時之作”而已。清代林云銘《楚辭燈》中說:“在原當日,見國事不可為,而又有宗國無可去之義,故把橘之不能逾淮做個題目。”清代蔣驥《山帶閣注楚辭》里談到:“作文之時不可靠,然玩卒章之語,揪然有不終永年之意焉。殆亦近死之音矣。”林云銘、蔣驥也都主《橘頌》出于屈原放逐之后。更有甚者,如曹大中先生認為這是屈原的絕名辭。
《橘頌》一詩產生的年限問題,無論是主早期說,還是晚期說,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存在,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然筆者通過聯系屈原的生平經歷,并結合其作品的實際內容與有關史料來分析,認為主《橘頌》是屈原早期作品的論點似乎更有道理。
當代著名楚辭學家趙逵夫先生認為“《橘頌》是屈原行冠禮時有意仿效士冠辭所寫成。”他將《橘頌》與《儀禮·士冠禮》所收冠辭進行比較后,得出了《橘頌》是詩人“舉行冠禮之后抒寫懷抱之作”的結論。由于《橘頌》在內容和形式上與《儀禮·士冠辭》有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所以他認為《橘頌》是仿士冠辭而作,其產生時間當為屈原二十歲行冠禮時,即公元前334年。他的主要論據是:(1)《橘頌》是四言體,士冠禮祝辭亦保持著四言形式;(2)《橘頌》中講到“德”,士冠辭也講到“德”;(3)冠辭可以稱為“頌”,《橘頌》亦稱為頌,故《橘頌》是仿士冠辭而作;(4)認為《屈詁》對“受命不遷,得之天也”的解釋,與士冠辭“受天之慶”等意思大體一致;(5)《橘頌》中言及“幼志”,士冠辭也有“幼志”;(6)從“嘉”、“服”等文字運用上看,兩文中均見,故亦為仿士冠辭而成文。我們從《橘頌》文本并結合現存文獻來看,趙逵夫先生找出的論證材料,是相當具有說服力的,并不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橘頌》與《士冠辭》只是在某些方面恰巧偶然有相似之處。固然有巧合之處,但在六個方面都極相近,這恐怕是不可能的,若非有意為之,絕然不會出現如此多的偶然。
由于《橘頌》的風格較為獨特,故聞一多說:“《橘頌》內容形式獨異,當自為一類。”姜亮夫也說:“……最突出的莫過于《橘頌》。在這篇詩里,詞面上一點也沒有直接講屈原的事跡,但仔細體會就會知道,屈原是以橘樹自比,并且這種比喻是有其深厚的現實基礎的。”《橘頌》整篇的感情基調,都是朝氣蓬勃、積極向上、堅定自信的。“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不僅寫出了橘樹受命生存的美好環境,還寫出了其“受命不遷”的堅毅品格,橘樹之高雅隱隱欲出。“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的外貌色彩絢麗、明艷動人,字里行間流露著詩人對橘樹的贊美之情。橘樹從外貌到內質都如此之美好高潔,不禁使人感慨它“獨立不遷”的節操。橘樹的美好,不僅在于外貌更表現在它內在的精神。如“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詩人一方面歌詠橘樹“橫而不流”、“淑離不淫”的高風亮節,一方面談到“愿歲并謝,與長友兮”,將橘與我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作為自己內心的獨白。《橘頌》運用擬人化的手法,一方面是對橘樹斑斕多姿的外表、“蘇世獨立”、“秉德無私”的美質進行歌頌,一方面是詩人對自己偉岸人格和崇高理想的熱情謳歌。有些學者誤認為詩人在詩中“自我賣弄和夸耀”,其實不然,詩人因為在青年時代就樹立了遠大的志向,養成了堅毅的品格,所以他才能有日后“吾將上下而求索”、“雖九死而猶未悔”的執著探索和追求精神,才能有“哀民生之多艱”的廣闊胸襟和悲天憫人的情懷。《橘頌》開朗明快的格調,不同于屈原其他作品深沉滄桑的風格。正如金開誠所言,就《橘頌》文本本身所表現的情感來說,“不大可能是老年人的作品。”
二、重釋《橘頌》的創作主旨
有關《橘頌》的主旨問題,歷代注家解讀不盡相同。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注曰“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由于宋洪興祖《楚辭補注》的體例是每句下先錄王逸注,“補曰”以下是洪氏對王注的補充或糾正,所以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二人觀點的繼承性,他們一致認為《橘頌》乃“美橘樹之有德”、“自喻才德如橘樹”、“自比志節如橘”“言己愿與橘同心并志,……長為朋友,不相遠離也”。二人基本認為《橘頌》是詩人用于自比其德的,他們的觀點得到了宋代大儒朱熹的認同。王逸、洪興祖、朱熹三家,在對《橘頌》文字用辭釋義上雖有所分歧,但就其整體旨意而言,三者觀點還是相近的。清人林云銘《楚辭燈》中說“看來兩段中句句是頌橘,句句不是頌橘,但見(屈)原與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鏡花水月之妙”。林云銘進一步繼承了前人的觀點,還贊其有“鏡花水月之妙”。
著名學者聞一多先生解詁《橘頌》時,在題解中引用了杜甫《四松》、白居易《玩松竹》等詩篇,他雖未直接指出其創作意圖,但我們通過相關材料可推知他對《橘頌》是屈原借物詠懷、托物言志之作的觀點也是基本認可的。今人姜亮夫在《屈原賦校注》直接明言:“作者因頌橘而牽及自身,完全用自己來比擬佳橘。”可見,姜先生是肯定了《橘頌》一詩為屈原托物言志之作觀點的。但當他在《屈原賦今譯·橘頌》中再次談到《橘頌》的旨意問題時,又說《橘頌》是《九章》中的“別調”,是“體物”之賦,是當時新興的一種文體,意義似乎很難解釋。姜先生觀點的模糊性,不免讓人有種如墜深淵之感,不知該如何取舍之意。當代學者游國恩、張中一等辭賦大家針對《橘頌》篇的主旨問題,也各自提出了自己不同的學術觀點,以致對《橘頌》主旨的解讀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莫衷一是。
就以上所列舉各家觀點而言,筆者更傾向于傳統觀點,同多數學者一樣,堅持認為《橘頌》是屈原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詩篇。《橘頌》一詩,不僅謳歌贊頌了橘樹的美好,還寄托了屈原遠大抱負和崇高理想,是屈原自身品格的真實寫照。屈原將自己的性格、志向、品德和愛國情感通過對橘樹的熱烈贊美傳達出來,讓讀者能夠在字里行間去品味詩人獨立不遷、積極樂觀的豁達精神,其真不愧為當時乃至今日詠物詩的扛鼎之作。
三、管窺《橘頌》的象征意義
《橘頌》作為屈原《九章》作品中最短的一篇詩作,無論是在題材、體裁,還是在情趣方面,都與其他八章迥然不同,而獨具特色,下文將進行淺要分析。談及《橘頌》的象征意義,就一定會牽涉出其文本所表達的思想主旨,這一問題勢必與前一問題重復,因此,本節將不再贅述其內容方面的問題,而僅從其藝術手法角度簡單闡釋其意象的象征意義。
在藝術手法方面,《橘頌》借鑒運用了《詩》三百篇里的比興手法,即象征的手法,卻能更進一步。《橘頌》用比興發端,由一物比興到整篇,說物則物中有人在,說人則人中有物在。詩人巧妙地描繪了橘樹的生態和習性,用類比聯想的方式,將大自然中橘樹的特點與社會現實中人的品格結合起來,既溝通物我,又融通古今。林云銘說:“一篇小小物贊,說出許多大道理,且以為有志有象,可友可師。”可見,物我一體、物我交融的創作境界在《橘頌》中已達到一定高度。
林庚在《釋橘頌》中說:“《橘頌》所寫的是一種性格,這也正是屈原的性格,戰國時期正是國家觀念將要形成還未形成的時期。……他是一個鄉土觀點極重的人……屈原一生的悲劇,也因為他對于楚國過分的愛戀。然而這種愛戀是可寶貴的,屈原因此成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由此可看出,林先生認為《橘頌》是屈原早期的作品,是詩人借橘自況、言志明理的作品,詩人將橘樹比作人,從而形成整體的象征系統。讀《橘頌》一詩,貌似詠橘,卻是處處喻人,它是我國傳統文化中古人追求“天人合一”精神內質的生動體現,也是古人“情景交融”美學理想的有力實踐。詩歌將“橘”與“人”巧妙地合二為一,表面上看是頌橘,而實質上是緊扣屈原的精神,是在頌人。南宋劉辰翁稱贊這首詩歌是“詠物之祖”,此言非虛,它不僅開啟了我國詠物詩擬人化的先河,還為文壇留下了光輝的藝術典型,其獨特的藝術價值,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綜上所言,《橘頌》作為屈原早年言志的一篇賦作,其以宏闊明朗的深刻寓意,炫麗柔美的文辭樣式,物我一體、情景交融的藝術手法,不僅在《楚辭》中,乃至在中國文學史上都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筆。屈原在《橘頌》篇中,將詩歌中常見的象征手法運用地恰到好處,其物我相忘、物我交融的藝術實踐,為后人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從后人創作的一些詠橘詩來看,其無論是在體物還是在寄托方面,無不受到屈原《橘頌》一詩的影響,如沈約的《園橘》、李嶠的《橘》、李紳的《橘園》等。盡管學術界關于這部作品在創作時間、文本主旨等方面存在諸多分歧,但這絲毫不影響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橘頌》就像一件偉大的藝術珍品,價值無可估量;就像一壇塵封的老酒,歷久而彌香。
[1]姜亮夫.屈原賦校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2]陸侃如,龔克昌.楚辭選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毛慶.詩祖涅槃[M].武漢:生活.讀書.知識三聯書店,1996.
[4]趙逵夫.屈原與他的時代[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5]姜亮夫,姜昆武.屈原與楚辭[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6]宋·洪興祖.楚辭補注·橘頌[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3.
[7]宋·朱熹.楚辭集注·橘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清·王夫之.楚辭通釋·橘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單位:云南大學旅游文化學院)
武國強(1986-),漢族,助教,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