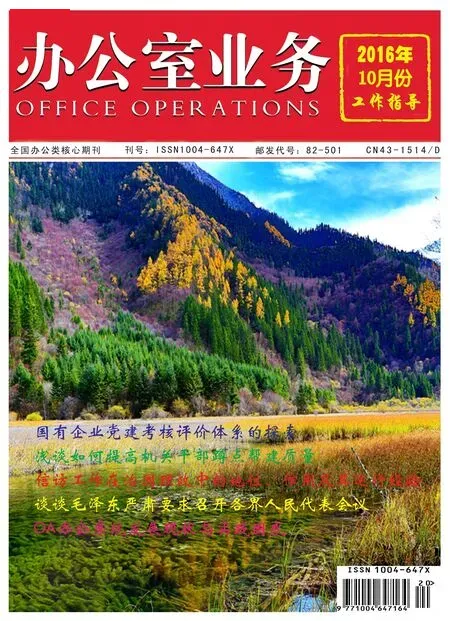新常態下人事檔案管理的新思路探索
文/鄄城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張華
新常態下人事檔案管理的新思路探索
文/鄄城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張華
無論是企業單位還是事業單位,在日新月異的發展中,都逐漸展現出對于人事管理的重視程度,因為人事管理不僅是對單位員工檔案管理,還是對人員綜合素質水平的記錄,在員工考核評價中起到重要影響。基于此,本文將主要以事業單位為主,探索分析常態下人事檔案管理新思路。
新常態;人事管理;新思路
新常態是一種新環境、新趨勢,其概念既強調了新時代下新思路,又體現了要不斷改善、以穩為綱的常態管理。在新常態條件下,各單位要不斷更新管理理念,改革管理方法,提升企業自身環境適應能力。掌握新趨勢下經濟市場需求,改善舊常態管理制度下出現問題。
一、新常態下人事管理新要求
(一)加大重視程度。新常態主要特點之一為速度,從高速轉為中高速,這是一種放緩增長模式,要求各單位速度與質量齊抓。因此,應用在人事管理中,需要單位領導提升重視程度,通過對于人事檔案的合理管理,保障員工檔案質量,使其在員工競職、調職中發揮重要作用。
(二)更新管理理念。新常態主要特點之二為結構,要不斷升級優化結構模式。事業單位人事檔案管理部門也該革新管理理念,建設新型管理制度。提升管理人員工作責任感,將檔案進行規范化管理,及時更新檔案資料;對于獲獎及處分資料一定要嚴查,確保檔案的準確性。并且對于老舊檔案進行科學保護,以免出現蟲蛀、發霉等現象,降低檔案完整度。
(三)創新管理手段。新常態主要特點之三為動力,找尋新驅動方式。事業單位也要不斷提升創新能力,通過引入數字化管理模式,提升人事檔案管理質量,建立單位內部電子檔案庫,提升轉檔、入檔、提檔效率,運用現代化手段,提升單位服務質量。
二、舊常態下人事檔案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管理人員方面。事業單位與企業單位不同,其目的是為社會帶來教育、醫療、科學等方面服務,以提升國家服務質量宗旨,因此在福利、保險方面,都有國家實行扶助政策。由于一些事業單位員工屬于繼承制,故人事檔案管理部門管理人員并不具備專業素養。可能只是因為服從分配,被調到檔案管理部門,因此對于檔案管理沒有科學合理規劃,難免會出現大量工作問題。
還有些單位領導并不重視檔案管理工作,其單位管理人員往往身兼數職,不能及時提供檔案信息,也影響了企業單位的辦事效率。
(二)檔案管理方面。我國很多單位在檔案管理方面存在以下兩方面問題:第一,檔案內容不準確。檔案單位對于一些檔案材料內容不會進行審查,因此單位人員在填寫過程中會虛報情況,尤其是對于賞罰記錄填寫上。很多員工都會夸大一些優秀事件或是捏造一些不便查證的獲獎記錄,而對于懲罰記錄也抱著單位不會查的僥幸心理,少量填寫。第二,檔案管理不及時。這是單位人事檔案管理重難點也是主要職能。但一些單位在此方面做得不好,由于管理人員日常疏忽,或是對于檔案管理手法不科學,因此導致檔案出現張冠李戴現象,或是調檔不及時為人員遷移造成不便。還表現為檔案不能及時更新,不能符合新型人事審核標準為人才考評造成不便。
三、針對人事檔案管理提出建議
(一)提升管理人員管理素質。在新時代背景下,只有具備專業素養才能提升辦公效率。事業單位應按照2014年推行的《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公開招聘、競聘上崗,為檔案管理部門提供專業人才。或是將招聘人員與競聘員工同時進行在崗實習,在實習期考察其檔案規劃能力、突發情況處理能力及對于人事檔案的管理能力,最后進行擇優錄取,杜絕企業內部裙帶關系。
對于在崗人員,也要進行定期培訓,提供深造機會。通過外出學習、在職培訓提升其專業素養,也加深了對于檔案管理的科學認識,加強工作責任感與積極性。
(二)建立合理檔案管理平臺。檔案管理水平與管理者責任感與管理手段有莫大關系。在信息化時代很多單位都對檔案實行數字化管理。通過實施管理在以下三方面提升管理質量。1.方便更改,通過電子備檔,每位員工都可以通過工作號登陸系統進行信息查看與管理,如家庭住址、聯系方式可以自行更改,改正后標注提醒管理員即可。2.方便檔案調取,電子檔案不似傳統紙質檔案,在檔案管理中很可能因為管理員疏忽或是自然災害而遭到損毀。而電子檔案不僅保證了檔案本身安全,還易于調取。其他單位需要員工檔案時,可以先進行電子轉檔,如有需要再轉紙質文檔。3.方便管理人員管理。通過員工自行更改通知管理員,可以節省管理員登記改正時間,將這部分時間用于檔案資料查實與老舊檔案整理,不僅提高了檔案準確性,還能提高人才競爭能力,方便單位考核。
四、結語
人事檔案管理在單位運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好的檔案管理機制不僅能幫助員工快速辦理入檔、轉檔手續,還能幫助單位提升服務質量與服務效率。事業單位也該積極適應新常態下工作標準,加深對檔案管理重要性的認識程度,改善管理手段,從而更好地為社會服務。
[1]練漢雄. 新常態下縣級人事檔案管理的舉措[J]. 辦公室業務,2016(09):153.
[2]張麗.新常態下人事檔案管理探究[J].現代商貿工業,2015(13):98-99.
[3]馬卓.新常態下高校干部人事檔案管理的問題與對策[J].邊疆經濟與文化,2015(06):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