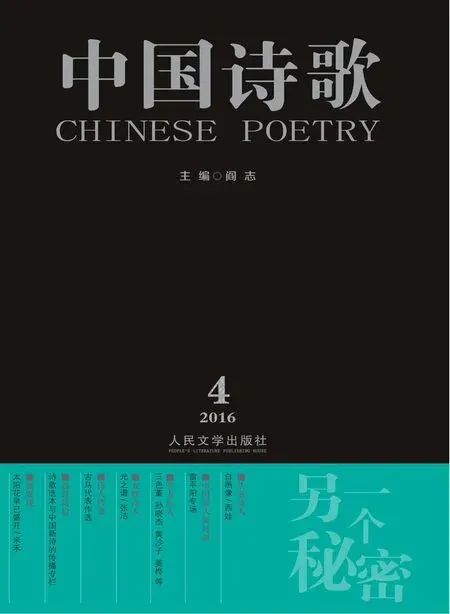李定新的詩
李定新的詩
離去的詞語都穿著時代的衣裳
總是想站在那片荒蕪的稻田
對著 噴吐綠焰的稗草
大鬧一場 叫醒
一代人的饑餓
青黃不接的憂傷
青黃不接 著一件蒼白的外衣
早已無力地離去
和離去的親人躺進黃土一樣
它靜靜地 躺在一本詞典里
記憶的螢火 搖曳
破舊的門窗
歲月安好 江山無恙
村子的候鳥 自由飛翔
寂寞的光陰里 銹蝕的鐮刀
一籌莫展 只有這時
青黃不接才會咳出內心的驚顫
如同從老屋走出的父親
穿的還是那個時代熟悉的衣裳
向日葵
這是幾年前回鄉時見到的一幕
遲至今天我都無法準確地描述當時的心情
只記得當我爬上那個熟悉的山坡
一抬頭便看見對面山腰間
正噴射著一大片金黃的火焰
火苗哧哧地沖向天空
仿佛要追跑著攥住剛剛離去的春天
那里曾是一棟斑駁冷清的泥磚房
主人是一個被婆家遺棄多年
楓葉一樣被吹回村子的瘋婦
她的雜亂無章的生活讓村民
也包括回鄉的我早已熟視無睹
她的生老病疼像一片片雪花
落在麻木的冰面上
讓我費解的是每個人見到我時
好像我還不曾看見似的
都驚詫地指著那一大片金黃的火焰
“看呀,那是李小青的向日葵!”
很多年了 那片金黃的火焰
一直燃燒在我的心里
越燒越旺 仿佛要燒掉我心里所有的積蓄
要燒毀我那整個炊煙繚繞的村莊
回鄉
像一枚被強行掐斷的樟葉
在城市的油沙路面旋轉了幾圈
一陣風就將你吹回了村莊
漆黑的夜 你用一臉慘白的月光
照亮回家的路
當刺耳的爆竹次第點燃滿村燈火
你面帶塵世愧疚的微笑 輕輕地
走向一個開著白花的鏡框
年初離家時的承諾
還只是一個空空的屋架
兒子的婚事在風中搖搖晃晃
長長的雞鳴 牛在清晨的露水中啃著青草
這一切你不再關心
前面帶路的小黃狗
離開村口時咬著褲角不松的小黃狗
退退轉轉 轉轉退退
能否準確嗅到樂沖后山上
父親汗水浸漬的氣息
這些 你也不再關心
夕陽中的造船廠
身體早被掏空
生銹的招牌也被摘走
江面上千帆過盡
像一件1950年代的風衣
在廢墟中飄搖
推土機步步緊逼
金色的陽光打在江面上
歲月無助的影子
瑟瑟發抖
江的對岸 一座緘默的老城
被越來越密集的人群挾持
眼看著一只無形的手
一鍬鍬掀著黃土將它掩蓋
大半個世紀的依伴支撐
已然力不從心
夜幕徐徐鋪展
時間的口越張越大
江面上撒滿碎金的往事
一點一點 吞沒在黑暗中
手藝
這些民間的花朵
正一支一支被時間摘走
嗡嗡轉悠的蜜蜂 蝴蝶
不知何時也離開了村莊
父親走后
竹床 木屣 福桶 蓑衣
這些與他相伴一生的伙計
帶著一身絕技 煙消云散
犁鏵 牛軛 水碾房 油榨屋
在一陣機械的轟鳴聲中
退縮在一個個蕭瑟的角落
來龍去脈 無人問起
灶口余生的竹木
不再迷戀鄉下破繭成蝶的夢想
紛紛外出鍍金 然后
擺出種種優雅姿勢 衣錦還鄉
父親走時 靈屋富麗堂皇
祖輩從沒享受過的家電應有盡有
只有母親自個納的青面白底的壽鞋
和奶奶給爺爺納的沒有兩樣
致父親
你越走越遠
每走一段
隨手關上一扇漆黑厚重的門
怕驚醒你急促的咳嗽
穿過每道門前來看你
我都是小心地拎著沉重的心情
腳步輕輕
只有這次 穿過第二十三道門
參加你的期頤之慶
也許是多喝了一杯
抑或時光過于荒蕪
一個趔趄撞響往事冰硬的門欞
霎時雨水如注
煙霧繚繞中 傳來電閃雷鳴
渾濁的眼光里 一枝蕨從您的窗口斜逸而出
像一只緊握命運的拳頭
又像一個秘而不宣的問號
插在歲月的褶痕
對一些往事的回憶
風雨在前
往事總在身后
回首便是光風霽月的晴天
一座普通而破舊的四合院
輕煙裊裊
氤氳 一把明清的鎖
暮色中 那個返鄉的女人
滾燙的腳
行走在冰面上
一個赤膊慣了的人
吹著風
生生套上一件過冬的衣
我滿懷興致 推門入院
本想伏案寫一首充滿張力的詩
卻最終只寫了個標題
永不言敗的村莊
村口的小河綠水長流
裊裊炊煙沖破層層封鎖
如同旗幟 以固有的姿勢
從屋頂升起
眼看稻田被踐踏成荒丘
一把把鋒利的鐮刀
依舊執拗地守護著季節
最后一只老水牛牽走了
繩子還牢系在記憶的犁軛上
一顆顆年輕的心被虜走
一顆顆更年輕的心在呵護中
沿著鄉情的臍帶茁壯成長
南瓜粥沒了 一聲聲呼喚還在
知青屋沒了 一張張臉孔還在
草鞋沒了 一點點足跡還在
油碾沒了 一片片油茶林還在
年味沒了 一塊塊臘肉還在
節日沒了 節氣還在
農事踩著豐收的大鼓
還在支撐一個民族的脊梁
如果你相信
村莊在城里安置了它的內線
只要有一片雪花
一個個熟悉或不熟悉的身影
就會接到旨意一樣回到村莊
時間揮舞著利器席卷而來
終將只能打敗
一個村莊虛妄的光芒
總是想起那條叫董木溪的河流
總是想起那條叫董木溪的河流
水質清澈 一些小鳥從水底輕輕滑過
河面不寬不窄 剛好沉住一口氣的距離
即便落雪下雨 兩岸牛羊的叫聲無慮無憂
順著水流方向出去的青年
日子長了 又回到了這里
水中不再有汗漬的異味
縷縷炊煙 依舊從暖暖夕陽中冉冉升起
董木溪 一個永遠不厭的姿勢
環抱著樂沖根深蒂固的子民
一個失去聽力的老人
也能憑借風的冷暖強弱聞到它的呼吸
常常想起那些在水中奔波的石頭
它們逆流而上 永不停息的身影
一度讓我想找到董木溪的源頭
我要把世間所有的希望和幸福撒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