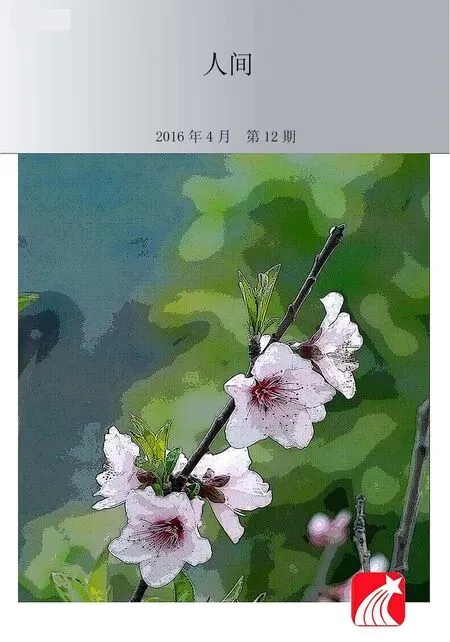遼代張世卿墓室壁畫《出行圖》再探
張娜
(四川大學,四川 成都 610000)
?
遼代張世卿墓室壁畫《出行圖》再探
張娜
(四川大學,四川 成都610000)
摘要:早在漢代,“車馬出行”就已經成為墓室壁畫或畫像石中的一種流行裝飾題材,尤其在東漢時期的畫像石墓中,更是十分常見。宣化遼代家族墓的發現,尤其是在對于宋代風俗民情有了較為豐富的認識之后,為了解宋遼邊界地區,處于遼界之內的漢人的文化藝術提供了相對豐富的資料。學界認為,遼代壁畫為“中國壁畫史上最后的閃光”,可見地位之重。
關鍵詞:張世卿;墓室壁畫;墓主人;出行圖
關于近年來出土的遼代墓室壁畫主要集中于河北、內蒙、山西北部和北京市一帶,對此,學界給出了許多頗有見解的說法和解讀。如李清泉老師的《繪畫題材中意義和內涵的演變—以宣化遼墓壁畫中的車馬出行圖為例》、《粉本—從宣化遼墓壁畫看古代畫工的工作模式》從圖像學的角度來闡釋認為宣化遼墓壁畫中普遍發現有運用粉本的現象,分析墓壁畫中粉本的運用的幾種方式,認為這體現了民間畫工的基本工作模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最新編纂的《宣化遼墓》發掘報告中,系統地討論了宣化遼墓群的年代、葬制、墓志以及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的情況。先賢鄭紹宗等人的研究,是對壁畫內容的意義和墓主人所處文化年代的解讀。他們對宣化遼墓壁畫墓群研究有指導性的意義。鄭紹宗曾經提出宣化遼墓中的散樂圖,表現的應是大曲演奏。[1]對遼墓壁畫的研究還有很多,成果豐碩,在此就不一一贅述
被譽為1993年全國考古十大發現之一的遼代壁畫墓群,位于宣化區下八里村北一里許的坡崗上,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壁畫墓營建于遼天祚帝天慶六年(1116年),墓主人為張世卿。[2]筆者主要從該墓壁畫中的出行圖入手。從整體上看,它的畫面不再出現車騎導從綿延不斷、護衛侍者前護后擁的復雜場面。畫面正中央于前方位置繪一匹白馬,馬額頂鬃毛以紅帶結成發辮,馬尾亦以紅帶綁扎,黃鞍飾、黃蹬、白韉,表現了貴族使用的金韉銀著(障泥)、絡、鞍、轡齊全,并有一云龍紋白色搭背。畫面上出現侍者5人,4人皆幞頭官服,表明了張世卿的官宦地位。第一人著朱砂色圓領團錦花長衫,左手牽馬、右手執藤鞭;第二人著白色圓領團錦花長衫,肩抗一長柄藍色大傘,是出行時遮蔽日曬雨淋不可缺少之物,此二人皆戴短腳蹼頭。第三人身穿朱砂色圓領團錦花長衫,頭戴筒狀東坡巾,雙手捧一頂荷葉形大白帽,立于馬鞍的正后方;第四人為持衣人,身穿藍色圓領團錦花長衫,頭戴蹼頭,其左臂搭一件紫色長袍,右手指向后方,似作交談狀;最后一人頭頂一大盤,盤中盛有黃色瓜棱形注子、盞托、扣碗、小碟等以備飲用。五人皆穿白色褲子,系帶布鞋,一副漢官仆吏的模樣。表明了墓主人準備出行的隆重場 面。
根據墓志記載,墓主人張世卿死于遼天慶六年(公元1 1 16年)正月四日葬 同年四月甲子朔十日。他在遼為官,曾特授右班殿直累軍(遷)至銀青祟祿大夫檢 校國子祭酒兼監御史云騎尉。這就為我們提供了墓葬的具體年代和當時的社會背景。遼初為游牧民族。太祖耶律阿保機建國后很長一個時期,仍是帶有很嚴 重的奴隸制殘余的封建軍事政權。特別是契丹奴隸主貴族統治集團在對宋和西夏等的掠奪戰爭中,給當時各族勞動人民帶來了很大的災難。特別是道宗大安年間五京屬地皆饑,墓志中 “大安中民谷不登,餓死者眾”所反映的正是這種情況。這在《遼史》 中也有所透露。“貧民大批流散逃亡”。在這種形勢下,契丹上層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反動統治,公布了“除安泊逃戶征償法”、“入粟補官法”等(《遼史·道宗本紀五 》),妄圖以此緩和矛盾,挽救危機。張世 卿正是由“進粟二千五百解”而得到所謂“天柞皇帝嘉其忠赤 ”,[3]特授右班殿直,官至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云騎尉。進入了契丹上層階級的行列。因此,張世卿墓無論形制、繪飾和隨葬器物俱遠高于其他張姓墓。制定了“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和“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的總政策,在這一政策下,這一地區原有的生產方式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原生活方式沒太大的改變,因而社會也就沒有發生大的動亂。總體而言,燕云地區在契丹統轄的100多年中,無論生產和文化都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成為契丹國家的首富之區。《 王澤墓志》“:念析津之壤,邇在浚之郊。戎冠天下之雄,與賦當域中之半”。[4]雖然他的官銜并非實有其職,但在漢人當中,可以說張世卿墓的出行圖基本代表了燕云十六州地區遼國中上層漢官階層的出行情況。
位于壁畫正中的鞍馬,皆是配有鞍鞘的,卻無人乘騎,李清泉先生認為這是留給靈魂的一個“位”,暗示著死者在另一個世界的旅行。畫中的馬有了生命,開始在陰間各司其職,供死者的靈魂使役支配。筆者對此也表示認同,但是在遼墓壁畫中皆不見墓主人,從藝術作品的角度來看.這一圖式所包含的如持傘、引馬、持衣等基本服務色,很大程度是主人優越生活和社會地位的象征。所以即使墓主人沒有出現在儀仗隊伍中也宣誓了他的存在。宣化遼墓出行圖多以鞍馬為中心,在唐代的繪畫作品有很多以鞍馬為中心,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在論到“衣冠異制”時說:“至如閻立本圖昭君妃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慎畫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如唐代韓幹的《牧馬圖》,南宋的《神駿圖卷》說明宣化遼墓的圖繪風格是上接傳統的。同時,“契丹故俗,便于鞍馬”,[5]鞍馬便于出行,契丹本就屬于游牧民族,善于騎射,作為宋遼邊境的宣化地區漢人,墓主人可能也擅長騎馬之術。因此,在該出行圖中以鞍馬作為中心。
張世卿墓志中提到他有“孫男二人,長日伸,妻耶律氏。”這說明:遼末在上層封建統治集團中,契丹和漢族通婚大概已較普遍,甚至可能已擴展到中下 層。墓志還說到張世卿“男一人,恭謙,曾肄北樞密院勒留承應”,進一步提供了在北樞密院中有漢人為官的實物資料。這都說明在遼的晚期漢和契丹等少 數族的密切關系。[6]宋遼邊界漢人與宋地漢人生活沒有太大的差異,雖然身處遼代契丹族的統治下,一方面受遼代統治政策“以漢制漢”的影響,南北分治,另一方面又漢民族的文化傳統與習俗根深蒂固,在遼境中的漢人墓葬,表現出了漢人在長期的民族文化融合中汲取契丹文化的情況,宣化遼墓反映著這方面的一些信息。宣化遼墓壁畫應該可以作為遼代晚期漢人繪畫成就的代表。也表現了漢族官宦的生活,它雖沒有漠北契丹貴族墓表現出的 車馬喧囂的場面,卻表現出更多的生活小景與生活場面。
在此,筆者從圖像和文獻的結合分析認為墓葬壁畫作為一種作為為了來世的藝術,雖然與傳世繪畫描繪的那種現實存在有所不同。車馬出行壁畫很有可能與死者的身份和地位發生聯系,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一種象征。以張世卿的地位,圖繪的可能就是他在當世身份、地位或者某種生活狀態。它的意義在于宣示自己生前的所有,并且把這種生前所有帶向另一個世界。
參考文獻:
[1]鄭紹宗.宣化遼墓壁畫[J].(臺灣)故宮文物月刊.1997 年第 12 期
[2]張家口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張家口文史 第2輯2004年09月
[3]鄭紹宗,河北宣化遼壁畫墓發掘簡報,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博物館
[4]陳述輯校《全遼文》,中華書局,1982 年。
[5]許嘉璐主編《遼史.儀衛志》,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1
[6]鄭紹宗,河北宣化遼壁畫墓發掘簡報,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博物館
中圖分類號:K24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4-0254-01
作者簡介:張娜,女,漢族,四川省巴中市,研究生,四川大學,美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