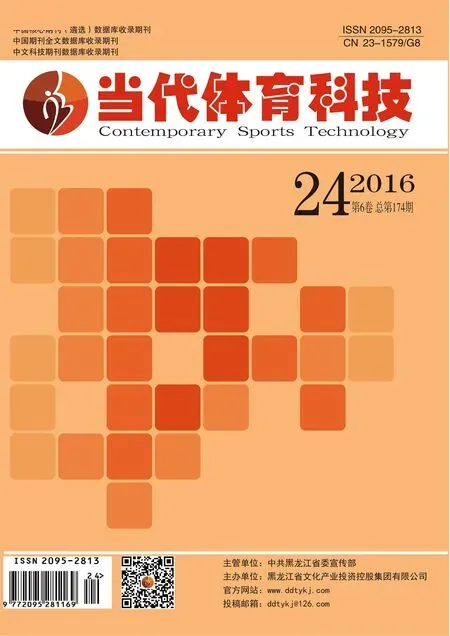“馬太效應”現象對競技體育的影響研究
吳風瞵(鄭州大學體育學院 河南鄭州 450044)
“馬太效應”現象對競技體育的影響研究
吳風瞵
(鄭州大學體育學院 河南鄭州 450044)
“馬太效應”現象影響競技體育中的許多方面,通過對競技體育中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分析總結,認為合理利用“馬太效應”的規律,可以更好地為競技體育服務。在選材方面各省隊強化優勢項目的同時,補充自身劣勢項目,增強區域間競技體育的交流,促進人才的流動;在運動訓練方面,教練員與運動員強化運動訓練理論的學習,在發展優勢的同時注意劣勢的提升,全面、動態地利用“馬太效應”為運動訓練服務;在比賽方面,完善賽制的管理系統,保證競技體育的公平、公正性。
馬太效應 競技體育 運動員
1 “馬太效應”現象的由來以及演變
“馬太效應”是從《新約·馬太福音》中的一個故事演變而來的,故事總結的大意是:越富裕的越是容易得到,越貧困的越是容易失去。最初是描述一種社會心理現象[1]:對那些在社會上已經非常有名聲的科學家所做出的貢獻給予的榮譽越多,但是對于那些名聲不大或者還沒有出名的科學家則不肯定他們的科學成績。經過社會的發展演變,在當今經濟社會表現出的是以快吃慢、以大吃小的社會現象;同樣的,在運動訓練和競技體育的過程中也顯明的存在著“馬太效應”現象。
2 “馬太效應”現象對競技體育的影響
2.1“馬太效應”現象對運動員選材的影響
運動員選材是競技體育的第一個階段,運動員的選材關系到競技體育的各個階段、整體實力與運動隊的可持續發展[2]。我國運動員后備人才選拔一直是在舉國體制的引導下把職業體育后備人才培育模式作為主導,采用“三級訓練”的體制[3]。由于我國各地地理位置、氣候、文化傳統的不同,整體來說呈現出區域性特征的“馬太效應”現象,例如:東北三省的冰上運動項目、湖北省的體操項目、廣東省的賽艇項目等,這些優勢項目省份在比賽中更容易取得優異成績。
對于選材來說,運動員的競技能力分先天遺傳與后天訓練兩方面組成,所以,這些優勢項目地區因為當地的自然地理條件與氣候條件,人們的身體形態、身體各部分機能、心理素質、遺傳等因素要優于其他省份,更容易選拔出大批體育競技人才;首先,優勢項目地區有豐富的經驗,以及社會各方面的支持更容易選拔人才。弊端則是優勢項目地區由于選材的基礎數量大,對于運動員自身來說運動成績不易突出,對訓練以及心理造成壓力,不利于“后起之秀”的展示;其次,相對于優勢項目省份,其他省份在這些項目的人才選拔與培養工作環節中需要克服的困難較多,不利于運動員的運動能力提升。長此以往,從國家整體的競技體育水平來說,有利于保持這些項目在世界級比賽的運動成績,穩固整體排名;但對于各個省份來說,使得優勢項目的地區成績越來越好,加劇了區域競技體育的失衡,影響部分省份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
2.2“馬太效應”現象對運動訓練的影響
在運動訓練中“木桶理論”強調的是運動員的運動成績受競技能力中最薄弱的一項的影響,而“馬太效應”強調的是發揮運動員的優勢競技能力。根據田麥久教授的項群訓練理論,運動員的身體形態、身體機能、技術、戰術、心理、智能等各個影響運動能力的因素在相互關聯中又各自獨立,并且有著自己的重要性等級,而各種等級在不同運動項目中作用各不相同。不同運動項目所需競技能力主導要素各不相同[4],運動員和教練必須在清楚從事運動項目要求競技能力影響因素的不同等級的情況下,以提高運動成績為目的,使優勢能力得到合理地發展和提高,在各個運動項目的整體體系中選擇最能影響整體、權重最大的能力進行完善和提高,以此使運動員的運動水平達到最高狀態。由此可以得出,“馬太效應”的基本思想是按照各個項目要求,教練員努力提升運動員的競技能力中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并對各因素及系統整體進行合理配置以達到最佳的竟技效果。所以,決定運動員的競技能力的各個因素并不僅僅受制于“短板”劣勢,“長板”的優勢同樣可以影響運動員的競技能力。
2.3“馬太效應”現象對運動比賽的影響
比賽是在統一規則中參賽者在體能、智能、機能、技術、戰術等方面進行的較量,既是運動員對前一階段運動訓練的總結與測試,也為今后運動訓練指出不足與方向。
在比賽運動員身上“馬太效應”尤為明顯,曾經取得優異的運動成績或在重要比賽中有突出表現的運動員,不但領隊和教練對其寄予厚望,觀眾也會在比賽的中對其增加關注度。以中國110m跨欄運動員劉翔為例[5],自劉翔在雅典奧運會打破紀錄以來,每逢國內外110m跨欄比賽劉翔的社會關注度都要遠遠超過這個項目的其他運動員。對此有益的一方面,社會的關注提升了運動員的榮譽感,并且為運動員增加了社會收益;弊端則是一方面給比賽的運
[8]Kontos, A. P.,Breland-Noble, A. M. Racial/ethnic diversity in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 A multicultural introduction to working with athletes of color[J]. The Sport Psychologist,2002(16):296-315.
[9]Oberg, K.Culture shock: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J].Practical Anthropology,1960(7):170-179.
G8
A
2095-2813(2016)08(c)-0158-02
10.16655/j.cnki.2095-2813.2016.24.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