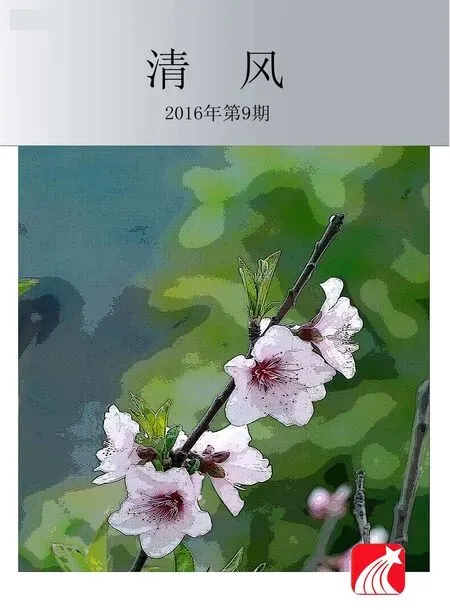制度反腐專家解讀“問責條例”
采訪_本刊記者(發自北京海淀)
制度反腐專家解讀“問責條例”
采訪_本刊記者(發自北京海淀)
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之際,黨中央在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上又發布重大舉措,7月8日,《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正式實施。該條例將對我國的反腐敗、全面從嚴治黨產生怎樣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呢?為此,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專訪了著名制度反腐專家、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以下簡稱“李”),請他就“問責條例”作了全面解讀。
反腐敗由動員階段進入問責階段
記:“問責條例”在此時出臺有何深意?它與以往頒布的黨內法規有何不同?
李:十八大以來,開始了強高壓反腐敗,而隨著“問責條例”的正式施行,表明我們的反腐敗已由動員階段進入問責階段。三年多的高壓反腐,作為中央紀委書記的王岐山,概括了一句很深刻的話,那就是“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像過去頒布的幾個條例,例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去年10月份頒發,今年1月1日施行,有兩個多月的緩沖期。而本次“問責條例”,于7月17日才由新華社授權全文發布,但是從7月8日起就開始施行,中間沒有緩沖期,這說明問責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十八大也已經過去三年多了,三年多來,對相關文件的動員、教育、學習已經成千上萬遍了,到了該問責的時候了。
也有人已經注意到,在2009年7月12日,新中國成立6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但是這個“暫行規定”層級不高,頒發機關級別也不高。此次中央出臺“問責條例”,從“暫行規定”升級到“條例”,也體現了我黨對全面從嚴治黨工作的重視。
另外,較之以往,這次頒布的“問責條例”有三個突出亮點:第一,過去問責主要是針對個人,沒有針對組織的;這次是既重個人責任,更重組織責任。第二,過去針對的是工作責任、業務任務上的責任;這次既重工作責任,更重政治責任,凡損害了黨的執政基礎的,就要問責。第三,過去重執行責任;現在既重執行責任,更重決策責任,追黨委的責任、黨委書記的責任,就是追決策責任。過去問責問的都是諸如副縣長、副市長以及分管行政領導的責任,對黨委特別是黨委書記基本上問不了責;現在不一樣了,“問責條例”提出,問責對象重點是黨委(黨組)主要負責人。這也是該問責條例最突出的一個亮點。
記:為什么要重點對主要負責人問責,是否體現了權責對等原則?
李:20多年的反腐敗理論研究和講課中,我反復講四個概念,權、責、利、罰,有權就有責,權與責必須對等;同時,有責就有利,責與利必須相當。但是,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前恥于談利,現在又羞于談利,這就導致責與利不相當。責與利不相當以后,有些該盡責的人就開始不那么負責了。有利就有罰,利與罰必須平衡。利重而罰輕,人們必然趨利而忘罰,導致罰難責眾,最后法不責眾。
目前,“問責條例”的頒發和施行,我認為是在權、責、利、罰中,采用的是抓中間帶兩頭的做法。從抓問責入手,既促進權力的履職盡職,又解決不履行職守的罰的問題,不盡責就要受罰,不作為、慢作為、緩作為、亂作為、胡作為都是不盡責的問題。所以要通過抓問責,既帶動黨員干部正確行權,又通過懲罰讓那些不盡職盡責的干部受到震懾。
“問責條例”具備很強的可行性
記:問責重在可行,“問責條例”是如何將問責落到實處的?
李:“問責條例”的出臺既必要又可行。過去問責的面窄,而且大都是碎片化的問責,是只見樹木、難見森林的問責,現在是系統化的問責,首先從戰略上問責,先問你的政治之責,再問你的工作之責;先問你的組織之責,再問你的個人之責;先問你的決策之責,再問你的執行之責。這樣就抓綱帶目,綱舉目張了。所以,“問責條例”的出臺既必要又可行。習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引用過清代人陳澹然的名言:“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而這次得“問責條例”就是從“萬世”、從“全局”出發的一個問責,因此,頗具可行性。
另外,“問責條例”還做到了紀法分開,2009年出臺的“暫行規定”有涉及“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條款,這一次就沒有了,因為這是法紀問題,不需要再拿黨紀來說事。如果不管黨紀國法,眉毛胡子一把抓,那樣反而不容易把問責落到實處。同時,“問責條例”還把處分條例和問責條例分開了,也和2009年的“暫行規定”不一樣,因為涉及具體處分時我們有《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這里就不需要再細化分開了。
還有媒體采訪我時提到,2009年印發的“暫行規定”中既有程序性規定,又有實體性規定?為什么這次沒有程序方面的規定,我的回答是,中央強調的是全黨的問責,實施辦法授權給了下面,“問責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可以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我以為,言下之意,就是說,問責作為從嚴治黨的利器,是新常態下的新事物,需要以創新的精神、改革的辦法去推進。中央把問責條例的大格局、大原則、大方針確定,具體的實施辦法,包括程序性的規定、救濟的渠道等,由各省、各部委結合自身的具體情況去做。
別看過去“暫行規定”有26條,這次“問責條例”減少一半,只有13條,但是這次卻是長遠結合,粗細結合,戰略與戰術結合。立高遠站宏觀,做到了該細的細,該粗的粗,該深的深,該淺的淺。這樣的問責,才能既有利于當前的到位,又有利于以后的拓展。
問責的目的是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
記:“問責條例”提出了終身問責,是出于什么考慮?
李:第一,《黨章》第二條規定,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你既然宣誓入黨,就表明你要為黨的事業奮斗終身,“問責條例”是遵循《黨章》制定的,那么,終身問責也是成立的。
第二,從掌權者的現狀來看,各級領導干部的權力基本上是只能上不能下,或者說很難下,這個狀況就迫使我們必須實行終身問責。
第三,從干部選拔的方式來說,我們總是在少數人中選少數人,上位權力的影響力極大。從表面上看,官員的權力會隨著他的退休、調離而自動解除,但是他在位的時候,他是少數人選少數人,選出來的這些人可能是他的親信、同伙,甚至死黨!因此,領導身邊的人,如辦公室主任、秘書、警衛、司機等,常常被破格提拔、超速提拔!這在現有干部隊伍,特別是重要崗位所占比例越來越大!所以也要終身問責。例如周永康,他在位時破格提拔了很多人,他退休后,影響力還是很大。所以必須終身問責,促使干部不搞不利于黨內團結的事情,不搞團團伙伙,不搞人身依附關系。
記:官員被問責,對今后的仕途影響有多大,是不是今后再努力都不能再上升了?
李:完全不能這么認識。有人說2003年是中國首開問責之年。其實,早在改革開放之初,1979年11月,因發生了渤海二號沉船事故,很快,國務院于1980年8月25日作出《關于處理渤海二號事故的決定》:一、接受宋振明同志的請求,解除他石油部部長的職務,提請人大常委會批準。二、國務院主管石油工業的副總理康世恩同志,對這一事故沒有認真對待和及時處理,在國務院領導工作中負有重要責任,決定給予記大過的處分。康世恩雖然被問責了,但他通過努力工作又得到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后來又重新出來工作,而且擔任更重要的職務。這就證明,問責不是整人,問責也不僅僅是追究某個人某級組織的責任。如果僅僅滿足于問了多少人的責,查了多少人,處分了多少人,撤了多少人,那么這種問責只是做了一個很淺的工作,深層次的問題沒有解決,這種問責既不能達到目的,也難以長時間地維系。
有權就有責,誰敢說自己百分百之盡到責了?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如果工作出現一些過失、錯誤乃至嚴重錯誤,被問責是很正常的情況,不問才不正常。應該讓問責成為一種常態,而不能把問責當成一種非常態。同時,問責也不能只停留在對問題的問責,而應該去發現問題產生的根源,這樣的問責才能事半而功倍,才能夠有利于政治體制的改革。
記:那么,問責的最終目的應該是什么呢?
李:通過問責有利于推動制度治黨,但是問責條例并不等于制度治黨。制度治黨包括兩個層面:一是修改完善黨規黨法,這是淺層次的;二是深層次的,即習總書記說的,“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
問責是通過嚴肅黨紀、嚴肅責任來發現我們制度設計、權力結構、用人體制、權力運行機制當中的弊端和問題,通過問責,不僅應發現人的責任,而且更應發現我們用人體制和權力結構的問題。然后,我們再根據發現的問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進行黨內民主制度的改革、黨內監督制度的改革、黨代會常任制的改革,最終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問責的主要目的在這里;而不是為了拿下多少人。重構政治生態,制度治黨,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這才是問責要達到的目的,也是反腐、監督以及巡視要達到的目的。
而我們深層次的弊端其實就是蘇聯模式,在十八大之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我的新著《蘇共亡黨之謎》,里面就主要論述了蘇聯模式的兩大根本性弊端。蘇共亡黨,表面上存在一系列問題,但是這一系列問題的背后,其實是兩個根本性的弊端發揮了關鍵作用:一個是權力結構,另一個是選人用人體制。把這兩個根本性的弊端解決了,我們問責的目的就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