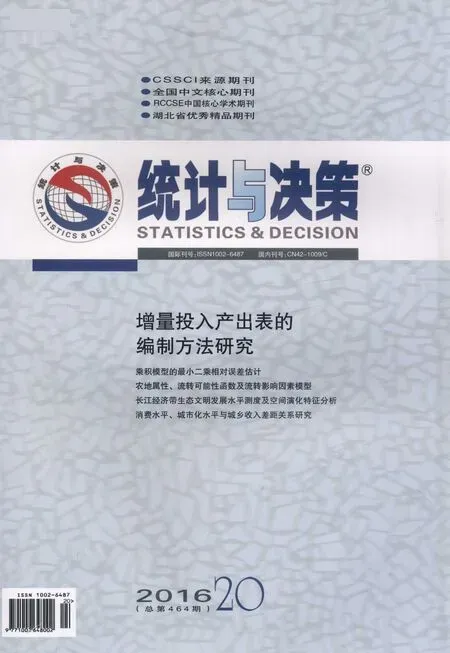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資源配置效率測算與分析
鄭家喜,楊東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武漢430073)
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資源配置效率測算與分析
鄭家喜,楊東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武漢430073)
為探究中國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文章應用DEA中的BCC模型,基于截面數據測算了2013年我國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的綜合效率、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基于1999—2013年面板數據運用DEA一Malmquist方法,測算了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中的技術效率、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研究成果對農業科技管理部門制訂合理的農業科技資源配置政策具有參考價值。
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資源;配置效率;DEA
0 引言
農業科技運行效率評價是進行農業科技資源配置決策機制制定的前提,評價結果可以指導有關部門對農業科技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充分發揮農業科技資源的作用,最終提升農業發展的質量。文獻[1]選擇并合成了農業科研機構產出績效的指標,采用多元回歸模型分析得出科研投入規模及結構影響農業科研機構的產出,發現農業生產還脫節于科研產出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科研產出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文獻[2]應用曼奎斯特指數方法測度了30個省(市、區)級農業科學院的科技資源配置效率。文獻[3]利用向量誤差修正(VEC)模型對我國農業科技創新資源投入與農業現代化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文獻[4]構建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剖析農業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因素。本文是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中的BCC模型、DEA-Malmquist方法,分別運用截面數據和面板數據對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資源配置效率進行測算,并進行差異性的比較。
1 數據來源和指標選取
本文共選取18個省、直轄市及自治區作為研究的決策單元,中部地區分別為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江西、山西6省;西部地區分別為四川、云南、貴州、甘肅、青海、陜西6省,廣西、西藏、內蒙古、新疆、寧夏5個自治區以及重慶直轄市。農業科技資源的擁有主體包括農業科研機構、農業高等院校、農業科學院和農業科技企業等,而農業科技企業從事農業科技活動相對較少,農業高等院校以教學為目的,僅部分科研工作涉及農業科技領域的研究[5]。因此本文運用農業科研機構和省級農業科學院的整合數據來反映各自省份的農業科技資源情況,其數據是經過對1999—2013年《全國農業科技統計資料匯編》等資料整理所得,該資料對中國農業科技人力資源、農業科技財力資源、農業科技物力資源及農業科技產出等進行了詳盡的統計匯編,是研究中國農業科技方面的權威數據資料。
本文借鑒楊傳喜(2011)的研究成果,選取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含在國外期刊發表的論文)、科技著作的出版數量、專利授權數量作為農業科技產出的衡量指標。單位在職科技活動人員數量、科技活動經費支出數額作為農業科技投入的衡量指標。
2 基于截面數據的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效率測評
本文采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中的BCC模型,基于2013年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投入與科技產出的截面數據,應用Deap2.1軟件測算了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的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和規模報酬,結果如表1(見下頁)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綜合效率平均值分別為0.843、0.836、0.847。由此可見,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相對于綜合有效率1而言,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綜合效率分解后的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別為0.902和0.939、0.849和0.985、0.928和0.916,純技術效率西部地區優于中部地區,而規模效率則是中部地區強于西部地區。
從中西部地區18個省份的農業科技運行綜合效率值分析,綜合效率為1(即綜合有效)的有湖北、貴州、甘肅、寧夏4個省(區),占22.22%。換句話說,湖北、貴州、甘肅、寧夏4個省(區)的農業科技投入產出規模在中西部地區中是相對最優的,也就是位于“生產前沿面”上;綜合效率非有效(即綜合效率值小于1)的省份是余下的14個省(區),即中部地區的山西(0.772)、安徽(0.929)、江西(0.877)、河南(0.775)、湖南(0.660)5個省份,西部地區的重慶(0.651)、四川(0.790)、云南(0.837)、廣西(0.924)、陜西(0.689)、青海(0.939)、西藏(0.738)、新疆(0.968)、內蒙古(0.628)9個省(市、區)。根據以上數據可以得知,中西部地區的農業科技運行效率相對較低,因此有必要進行農業科技資源配置的適度整合以便提升農業科技創新效率。數據包絡分析方法所測算出來的是相對效率,也就是說運用內部的標桿所衡量出來的效率[6]。針對導致各自省份農業科技運行效率高低的深層次原因則需要結合科技環境、科技體制等多種因素進行綜合分析。

表1 2013年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效率
純技術效率值為1的有湖北、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等8個省份,占中西部地區省份數量的44.44%;規模效率值為1的湖北、貴州、甘肅、寧夏。因此要在純技術性率提升的同時,切實改變農業科技機構或科學院的適度規模,實現規模效率的持續改進。純技術有效率而只是由于規模非效率導致整體技術非效率的地區有云南、陜西、青海、西藏,這4個省份農業科技運行效率的提高需要重視科研的規模與布局情況,而不是注重投入的技術性方面的利用效率。農業科研機構所處的規模報酬階段決定了是擴大規模還是縮減規模以便提高科研的規模效率。由于內蒙古、云南、廣西和四川4個省是處于規模報酬遞減的階段,所以要實現規模經濟就應該減小科研投入的規模;與此相對,山西、安徽、江西、河南等10個省份則可以通過投入規模的適度擴張來實現規模經濟。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新疆等省份的農業科技運行綜合技術效率小于1是純技術效率值與規模效率值都小于1所引起的,因此必須從科技人員、科技資金冗余的調整以及科技管理政策調整等方面著手,同時根據所處的規模階段進行合理調節,以便有所選擇地有效配置既定的農業科技資源,達到高效利用的目的。
2.1 規模報酬不變情況下的技術效率
2009—2013年區域規模報酬不變的技術性率(Crste)平均值如表2所示。從區域規模報酬不變的技術性率平均值來看,2009—2013年,東部地區(0.96)>全國(0.84)>中部地區(0.83)>西部地區(0.79)>東北地區(0.73)。因此,中西部地區規模報酬不變的技術性率平均值都低于全國和東部的平均值,但是高于東北地區。
從全國31個省(市、區)Crste年度平均值來看,不同年份差異比較明顯,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五年的Crste平均值分別為0.835、0.866、0.78、0.877、0.849,總體上呈上升趨勢,一定程度反映了農業科研機構的科技運行效率隨著改革的推進而不斷得以提升。具體省(市、區)Crste的年度變化情況詳見表2。
甘肅、青海的技術效率平均值均為1,是經濟相對發達的北京(1)、上海(1)、江蘇(1)、浙江(1)、福建(1)、山東(1)之外的少有的中西地區省份。Crste平均值在(0.9,1)的有河南、湖北、貴州、陜西和寧夏。山西的Crste平均值在(0.8,0.9),Crste平均值在(0.7,0.8)的有安徽、江西、湖南、廣西、四川、云南、新疆等省(市、區),內蒙古自治區的Crste平均值最低只有0.388,西藏和重慶的技術效率平均值也相對較低,分別是0.667和0.594。
2.2 規模報酬可變情況下的技術效率
區域規模報酬可變的技術性率(Vrste)平均值如表2所示。從區域規模報酬可變的技術性率平均值來看,2009—2013年,東部地區(0.96)>全國(0.87)>中部地區(0.85)=西部地區(0.85)>東北地區(0.76)。因此,中部與西部地區規模報酬可變的技術性率平均值相同,它們低于東部和全國的平均值,但高于東北地區。

表2 農業科研機構科技運行效率(2009一2013年)
全國31個省(市、區)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五年的Vrste平均值分別為0.874、0.906、0.817、0.89、0.869,雖然不同年度有小幅度的波動但總體趨勢仍呈增長態勢,具體省(市、區)規模報酬可變情況下的農業科研機構的技術效率(Vrste)的年度變化情況如表2所示。
2009—2013年,甘肅、青海、西藏、寧夏共10個省(市、區)的技術效率平均值均為1,是除了經濟相對發達的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之外的農業科研機構運行效率比較理想的民族地區。Crste平均值在(0.9,1)的有河南、湖北、貴州、陜西。山西的Vrste平均值是0.892,Crste平均值在(0.7,0.8)的有安徽、江西、湖南、廣西、四川、云南、新疆等省(市、區),內蒙古的Vrste平均值最低只有0.472,重慶(0.665)的技術效率平均值也相對較低。
2.3 規模效率
2009—2013年,農業科研機構的規模效率(scale)平均值如表2所示。從區域規模效率平均值來看,東部地區(0.994)>中部地區(0.975)>全國(0.962)>東北地區(0.958)>西部地區(0.932)。因此,中部地區規模效率平均值高于全國的平均值,而西部地區則低于全國的平均值。
2009—2013年,甘肅、青海的規模效率平均值均為1。Scale平均值在(0.9,1)的有安徽、江西、山西等13個省份,由此可見農業科研機構的規模效率在0.9以上的高達83.33%。說明經過科技管理領域的改革,農業科研機構的規模達到相對適度的水平,規模效益得以顯現。西藏的規模效率平均值最低,只有0.667。內蒙古的Scale平均值(0.812)也相對較低。
從全國31個省(市、區)Scale年度平均值來看,規模效率提高的趨勢非常明顯,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五年的Scale平均值分別為0.947、0.952、0.956、0.981、0.978,作為農業科技創新重要主體的農業科研機構更應該有效地配置農業科技人力、財力、物力、信息等資源切實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從而促進現代農業的持續、協調、綠色發展。
3 基于面板數據的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效率測評
本節采用Malmquist方法,基于1999—2013年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投入與科技產出的面板數據,得到了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的Malmquist指數及其分解,如表3所示。累乘結果顯示,技術效率提高了24.1%,而技術進步指數出現大幅度下滑30.1%,最終致使全要素生產率指數下降了13.1%。全要素生產率平均下降了1%,導致全要素生產率指數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指數的下降(2.5%),技術效率指數平均提升1.5%。
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效率的年度變化波動較大, 2001—2002年、2003—2004年、2005—2006年、2008—2009年、2010—2011年、2011—2012年度間,Malmquist指數提升的幅度分別為31.2%、46.1%、0.6%、13.7%、7.9%、2.2%; 1999—2000年、2000—2001年、2002—2003年、2004—2005年、2006—2007年、2007—2008年、2009—2010年、2012—2013年度間,Malmquist指數出現不同程度下滑,下降的幅度分別為14.6%、22%、13.4%、21.9%、2%、7.3%、10.7%、1.7%,如表3所示。1999年科技體制改革、科研機構轉制一定程度影響了農業科技運行效率,政策影響到農業科技人員減少了用于農業科學研究的時間,進而影響科研成果的產出。2002年以后,國家科研體制改革的思路逐漸明晰,《農業科技發展綱要(2000-2010)》提出建立國家農業科技創新體系,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專門闡述了農業科技方面的問題及解決路徑,中國農業科學院也實施了農業科技創新工程,使得農業科技的特色更加鮮明、競爭性經費與穩定性經費支持的比例趨于合理,對農業科技運行效率的提升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表3 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效率(1999一2013年)
表4(見下頁)中給出了中西部地區18個省份的農業科技運行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情況,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區不同省份間農業科技運行效率差異明顯。Malmquist指數大于1的有安徽、廣西、重慶、湖北、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市、區),其全要素生產率平均提升的百分比分別為5.2%、6.9%、5.6%、4.6%、4.3%、7.7%、0.1%、5.9%,增長類型屬于低增長型[7]。安徽、湖北、重慶、云南四省Malmquist指數的提升是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綜合提高作用的結果,廣西、四川、新疆三省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得意于技術進步指數的提升,而青海Malmquist指數的提高主要是技術效率的增加。
技術效率的變化可以解釋為處于前沿面下的省份學習位于前沿面上省份的管理方式、組織形式、要素利用效率、新技術運用能力、規模經濟性等,這表明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管理水平等方面還有較大的提升機會。技術效率值大于或等于1的有山西、安徽、湖北、重慶、貴州、云南、西藏、甘肅、青海和寧夏,其中青海提升幅度最大(9.6%)。
技術進步對農業科技運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促進作用不大明顯,除安徽、湖北、廣西、重慶、四川、云南、新疆等7個省份(占38.89%)的技術進步指數大于1,另外的11個省份(占61.11%)的技術進步指數都小于1,體現了科技體制改革等政策性方面的外部因素對農業科技資運行效率的影響力還有待加強。中西部地區技術進步指數年均下降2.5%。
規模效率指數大于或等于1的有山西、內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重慶、貴州、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3個省份,這一定程度說明農業科技的規模達到相對適度的水平,因此,在保持合理規模的同時切實提升質量。

表4 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1999一2013年)
4 結論
(1)利用2013年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投入與科技產出的截面數據,使用Deap2.1軟件運算得到中部地區、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綜合效率平均值分別為0.836、0.847,西部地區的農業科技運行效率整體優于中部地區;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綜合效率平均值僅為0.843,農業科技運行效率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2)2009—2013年,農業科研機構規模報酬不變的技術效率平均值為0.84、規模效率平均值為0.962、模報酬可變的技術效率平均值為0.87。因此,可以通過深化農業科技體制改革,優化農業科技創新力量布局,開展農業科技計劃績效評價,注重農業科技協同創新,組建農業科技創新聯盟等手段,切實提高農業科技資源的使用效率。
(3)1999—2013年,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的Malmquist指數及其分解累乘結果顯示,技術效率提高了24.1%,而技術進步指數出現大幅度下滑30.1%,最終致使全要素生產率指數下降了13.1%。全要素生產率平均下降了1%,導致全要素生產率指數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指數的下降(2.5%),技術效率指數平均提升1.5%。中西部地區農業科技運行效率的年度變化波動較大。
[1]申紅芳,廖西元,胡慧英.農業科研機構科技產出績效評價及影響因素分析[J].科研管理,2010,(6).
[2]楊傳喜,徐頑強,孔令孜,李小紅,張俊飚.農業科學院科技資源配置效率研究——基于30個省級農業科學院的面板數據分析[J].南方農業學報,2015,(1).
[3]邢曉柳.我國農業科技創新資源投入與農業現代化的關系——基于v EC模型的實證研究[J].資源開發與市場,2015,(6).
[4]董明濤.我國農業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及影響因素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4,(2).
[5]陳祺琪,張俊飚,程琳琳,李兆亮.農業科技資源配置能力區域差異分析及驅動因子分解[J].科研管理,2016,37(3).
[6]楊傳喜,黃珊,徐頑強.中國農業科研機構科技運行效率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3,33(4).
[7]楊傳喜.農業科技資源配置效率問題研究[D].華中農業大學,2011.
(責任編輯/易永生)
G311
A
1002-6487(2016)20-0102-04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146301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13BJy110)
鄭家喜(1969—),男,湖北松滋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農業經濟。楊東(1992—),男,湖北武漢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村區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