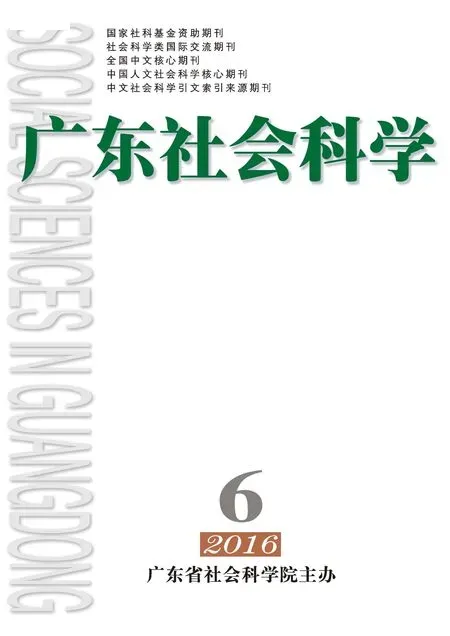抗戰時期國家紀念日與“抗戰精神”話語的建構
郭 輝
?
抗戰時期國家紀念日與“抗戰精神”話語的建構
郭 輝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面臨生死存亡的危局,國家紀念日作為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可資利用的重要政治文化手段,紀念話語中開始出現大量的“國難”描述,成為滋生“抗戰精神”的具體現實語境。國家紀念日紀念話語建構的“抗戰精神”以革命精神作為歷史來源、民族精神作為核心內容、國民精神作為現實表達。“抗戰精神”為中國人民抗戰提供了精神動力和支持,并增強了中華民族凝聚力,加強了社會對國家的認同感,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
國家紀念日 抗戰精神 抗戰時期 紀念話語
九一八事變后國難日趨嚴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試圖利用自身掌控的國家紀念日這一重要政治文化資源為現實抗戰服務。“國難”的產生促使國家紀念日中“抗戰精神”話語逐漸生成,并具有一定的內涵意旨,產生一定的社會功效。筆者闡述的國家紀念日紀念話語包含相當豐富的政治文化內涵,既有革命理念,也有領袖崇拜,還有民族主義,①而“抗戰精神”話語具有典型的現實意義和指向,本身即應“國難”而生,為抗日戰爭服務。在現實“國難”語境下,國家紀念日中的“抗戰精神”話語表現為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國民精神,為抗戰提供精神動力和支持,并能夠增強民族凝聚力,加強社會對國家的認同感,豐富社會的歷史記憶。本文即試圖觀察國家紀念日中的“抗戰精神”話語,分析其生成的現實語境、具體內涵,以及社會功能,以此揭示民族危機下國家紀念日紀念話語的現實面相。
一、“抗戰精神”的現實語境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家紀念日紀念話語中有不少關于“國難”的描述,“國難”的產生直接促使“抗戰精神”的生成,“國難”成為國家紀念日中“抗戰精神”話語建構的具體語境。國難滋生出抗戰精神,抗戰精神是應對國難之方。
國家紀念日中使用“國難”一詞應是在九一八事變后1931年10月10日國慶紀念,當時《中央日報》社論將“國慶”冠以“國難中之國慶”,但所言“國難”除“九一八”后日本的侵略外,還有國家的內部紛亂。社論指出:“今年二十周年國慶紀念,吾民族正遇重大之國難。環顧國中,無一處不破碎,無一事能差強人意,二十年來繼續不已之兵爭及政治上之紛爭,已消耗無限光陰,無限國力。建設不必談,即極幼稚之生產事業亦受戰禍及災害之影響摧毀殆盡。”一是“黨內仍迭有糾紛,致中央預定之訓政步驟,多所掣肘”;二是“本年復罹空前未有之水災,哀鴻遍野,饑溺載道,災情之重,及被災面積之遼闊,亙古罕見。即集全國之力量以救災籌賑,亦將不足以登斯民于袵席”;三是“暴日更乘我之敝,肆意尋釁。九月十八日之事件,竟破國際間事變之記錄。吾民族立國以來,有史以來,從未遭過如此野蠻之民族,從未被外力侵略凌逼至于如此其亟者”。②因為內憂外患、天災人禍肆虐,這一年的國慶閱兵喊出了“速起共赴國難”的口號。③國慶紀念標語中也不乏“在國難中紀念國慶務須下必死的決心共赴國難”、“在國難中紀念國慶必須作最大的努力光大國慶”之類的標語,④并被布置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會場。⑤1931國慶紀念,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告同志同胞書中也指出:“本黨正從事于肅清封建余孽,……以鞏固國家的基礎;不幸忽有亙古未有之水災,人民流離逃竄,慘不忍睹;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復乘我天災人禍交相逼迫之日,不宣而戰,忽于九月十八晚,侵占我沈陽,屠殺我同胞,遼吉兩省,相繼失陷,亡國慘禍,迫在眉睫!我們今日紀念國慶,不幸遇著這樣嚴重的國難,實在覺得十分悲痛與憤慨。”⑥同樣將“國難”指稱內憂外患、天災人禍。該年國慶紀念中國難話語勃興。



全面抗戰爆發后,全國上下更多地關注并致力于實際抗戰行動。況且,隨著日寇侵略的不斷深入,國人更多的需要心理安慰,而不宜過多談論屈辱的“國難”事實,以避免造成“氣餒”氣氛。在相關國家紀念日的紀念活動中,“國難”一詞出現的頻率雖然沒有之前那么高,但“國難”內涵已發生比較明顯的變化。

“國難”的宣揚成為“抗戰精神”話語建構的現實語境,正因國難才需要人們發揚傳統革命精神,弘揚民族精神,塑造國民精神,為抗戰這一當時最大的政治現實服務。
二、“抗戰精神”的具體內涵





歷史與現實、政治與文化的激蕩交融產生出抗戰精神。抗戰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同樣也有不少漢奸和賣國行為,精神信仰則顯得格外重要。中國與日本力量懸殊,物力、財力、武器裝備等皆不及日本,則特別需要精神的力量鼓舞人心,激勵抗戰。
三、“抗戰精神”的社會功能
國家紀念日紀念話語中的“抗戰精神”是抗日戰爭時期重要的精神資源,同時在抗戰精神的鼓蕩下,也提升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地位。當然,抗戰精神本身也可以作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記憶而存在。

其次,“抗戰精神”提高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地位和聲譽,增強了社會對國家的認同感。抗日戰爭時期國家紀念日紀念不僅是人們紀念特殊事件,也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表達現實政治訴求的途徑,尤其是為了贏得抗戰勝利,而有精神方面的要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通過國家紀念日塑造出的“抗戰精神”,是自身形象的形塑。反之,也有利于社會認識國家,增強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了解,從而有助于塑造國家認同感。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通過相關國家紀念日紀念不斷宣傳抗戰精神,將之通過相關活動影響及社會,增強人們責任感和使命感,讓社會各界都深切感覺到抗戰不僅是國事,也是個人的事情,在凝聚人心的同時也增強人們的集體認同感。尤其是當時充斥于報端的“民族精神”口號,使中國保持了一個民族國家的美好形象,增強了普通百姓對國家和政府的認同感。如此特殊環境下,歷史資源被國家廣泛運用,如“九一八事變”作為新發生的“恥辱性”事件,卻被當做“新的傳統”予以紀念。既是國家政策使然,也是國家在尋求可資利用的資源以增強統治權威。社會對國家認同感的增強正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意圖追求的目的所在。
最后,“抗戰精神”保存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豐富了人類的歷史文化資源。此乃就超越性的歷史價值和功能而言,并非在當時起到的作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于國家紀念日都會召開不少紀念大會,舉行紀念活動。紀念與記憶之間的關系殊為復雜,但傳遞和保存“記憶”之一面卻不容置疑,國家紀念日宣揚“抗戰精神”,包括國難的書寫,革命精神的刻畫,民族精神的弘揚,國民精神的塑造等,都是值得保存的社會記憶。當然,于一個民族而言,不僅快樂的記憶要珍存,痛苦的記憶也應保存,如此才能豐富民族的歷史記憶,提供更多歷史經驗資源。日本對東北的侵占,對東北同胞的殘害屬于國難、國恥記憶,應受到人們重視。“九一八”“國難”敘事作為一個民族痛苦的記憶,在抗日戰爭記憶中的地位相當重要,為中國空前國難的開始,其后不斷的痛苦的民族記憶皆源于此。“九一八”、“七七”等事變形成的記憶資源不同于個人記憶,而是一個民族共同的災難和體驗,是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但更多的是民族振奮的記憶,人們抗爭的記憶,無數英雄拋頭顱灑熱血的記憶,通過紀念活動中各種話語不斷重現和再造。如此關于“抗戰精神”的記憶應受到重視,是“國難”下中華民族的抗爭,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抗戰精神”不僅是中華民族歷史記憶的一部分,也是人類的重要歷史文化資源。
國家紀念日是抗日戰爭時期一項重要的國家政治文化政策,“國難”依靠國家紀念日被宣揚,由此而產生出對“抗戰精神”的需求。抗戰精神作為精神資源在當時危難局勢下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能夠增強民族凝聚力,為抗戰提供精神動力和支持。
①郭輝:《國家紀念日與抗戰時期“革命”話語之建構》,南京:《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郭輝:《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國家紀念日增設與民族主義的彰顯》,鄭州:《中州學刊》,2015年第6期;郭輝:《抗戰時期民族掃墓節與民族精神的建構》,開封:《史學月刊》,2012年第4期;郭輝:《傳統的發明:抗戰時期孔子誕辰紀念日研究》,廣州:《學術研究》2014年第7期;郭輝:《抗戰時期國家紀念日與國家觀念的傳播》,《近代思想史研究》第10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89~304頁。
②《國難中之國慶》,南京:《中央日報》,1931年10月10日,第1張第2版。
③《國慶閱兵禮今晨在飛機場舉行》,南京:《中央日報》,1931年10月10日,第1張第2版。
④《國慶紀念標語》,南京:《中央日報》,1931年10月10日,第1張第2版。
⑤《中央舉行國慶紀念》,南京:《中央日報》,1931年10月11日,第1張第3版。
⑥《國慶二十周年紀念市黨部告同志同胞》,南京:《中央日報》,1931年10月10日,第1張第2版。
⑦《國難中紀念總理逝世》,南京:《中央日報》,1932年3月12日,第1張第3版。
⑧社評:《國難中之國慶》,南京:《中央日報》,1932年10月10日,第1張第2版。
⑨《國難中之國慶日市黨部召各界開紀念會》,南京:《中央日報》,1932年10月11日,第2張第3版。
⑩《總理逝世八周年 各界昨開紀念會》,南京:《中央日報》,1933年3月13日,第2張第3版。



































[責任編輯 李振武]
*本文系中共中央組織部“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資助、湖南省教育廳優秀青年項目“國慶紀念日與民國政治文化研究”(項目號14B123)、湖南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學術骨干培養計劃資助項目“民國時期國家紀念日研究”(項目號13XGG03)的階段性成果。
K265.2
A
1000-114X(2016)06-0112-08
郭 輝,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長沙 410081
廣東社會科學 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