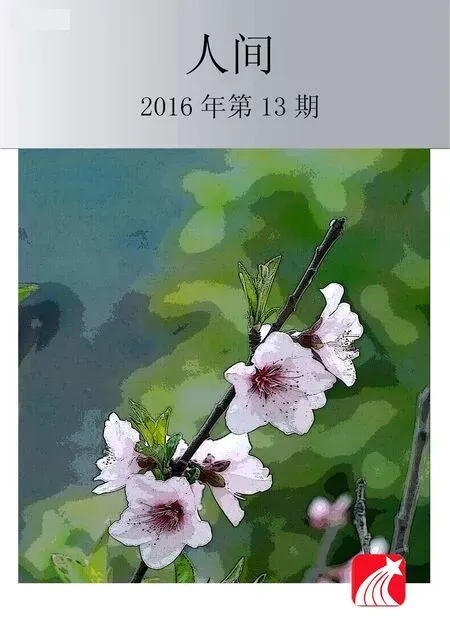論池莉的《托爾斯泰圍巾》中小人物的生存哲學
楊慶冬(哈爾濱師范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
論池莉的《托爾斯泰圍巾》中小人物的生存哲學
楊慶冬
(哈爾濱師范大學,黑龍江哈爾濱 150025)
摘要:池莉作為新寫實主義作家的代表,其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小人物形象,她的中篇小說《托爾斯泰圍巾》通過寡婦張華、裝修工、老扁擔三組人物,以花橋苑一場裝修房子的風波將人物聯系在一起,分別闡述這三組小人物或積極健康的、或彪悍的、或高尚的生存哲學。通過對他們擁有不同生存哲學的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分析,不僅使讀者走進了這三組小人物的內心世界,而且使讀者更加了解,這三組小人物所代表的三類生存哲學。池莉的《托爾斯泰圍巾》中的小人物的生存哲學,擴大了文學史上對小人物生存哲學的表現。
關鍵詞:小人物;生存哲學;艱難;卑微
一、“小人物”、“生存哲學”的界定
(一)“小人物”的提出與發展。
中晚唐時期,傳奇的出現塑造了大量的小人物形象。在此之前,文學長廊中的人物大多數為士大夫以及一些英雄形象。比如《左傳》中形形色色的軍事政治家,司馬遷《史記》中永載史冊的人物等。隨著文學越來越向市民階層靠近,中下層平民漸漸走進了文學作品,到了中晚唐,文言小說發展的成熟直接推動了小人物在文學作品中大量出現,如唐傳奇《李娃傳》中的李娃、《鶯鶯傳》中的崔鶯鶯等。第一次明確塑造了小人物,并正式將它提出、發展的是19世紀末俄國作家普希金,《驛站長》中的維林是俄國文學長廊中第一個小人物形象。
經過前人的發展與創新,在文學中出現了一條“小人物”的長廊,作為小人物典型的他們都有些共同的特點:首先是生存地位的卑微,居于社會底層的他們要忍受比普通人更多的苦難,不僅是經濟的拮據、生存的威脅,還有來自外界的欺壓;其次,作為弱者的小人物們是無力對生活進行反抗的,他們無法讓自己擺脫貧困,更無力與欺壓者進行斗爭,獲得平等的待遇。最后,飽受磨難的他們并沒有引起世界的關注。雖然“小人物”在不斷地發展,但大體上,這些共同點成了“小人物”的“商標”。
(二)生存哲學概述。
卡爾·雅斯在他的《生存哲學》中首次提出“生存哲學”,他對“生存哲學”做了如下界定:“從本原上去觀察現實,并且通過我在思維中對待我自己的辦法,亦即通過內心行動去把握現實。”[3]另一位哲學大家尼采也對生存哲學進行研究,他認為,潘多拉之盒給人類帶來災難卻還保留一個,人類把留下的災禍當作最了不起的財富——這就是希望[4],宙斯要求人類盡管從來沒有受到其災禍的如此磨難,卻不放棄生命,而是繼續讓自己再重新受磨難。
國外哲學家對“生存哲學”的論述準確精煉,而“生存哲學”在中國的發展更加具體化。魯迅、余華等作家以具體的人物形象向世界展現了不同的生存哲學。但是,無論是余華《活著》中福貴“牛”一樣的生存哲學[18],還是魯迅筆下阿Q的“精神勝利法”,都各自代表了一類小人物的生存哲學,代表了他們在面對生存困境時對永恒和絕對的理解以及對信仰的鑄就。
二、池莉《托爾斯泰圍巾》中小人物的生存哲學
池莉作為當代新寫實主義作家,重在真誠直面現實和人生,注重對凡俗的生活的表現,瑣碎的生活與操勞庸碌的小人物成了作品的中心。自從1978年池莉轉向了對生存意義的探討后,生存哲學作為她探討內容的一部分在她的作品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在池莉的中篇小說《托爾斯泰圍巾》中,小人物主要是寡婦張華、裝修工、老扁擔,池莉通過對這幾個小人物在面對生存危機時的態度,以及信仰的鑄就過程的描寫,向讀者展現了不同的生存哲學,對不同的生存哲學雖無褒貶,但努力地去闡釋和表現。
(一)城市邊緣人物張華的生存哲學。
張華的丈夫為救建材倉庫的火犧牲,全靠張華的“跑”才得了“烈士稱號”,張華也因此得到烈士遺孀的待遇,但生活依然艱難,與女兒胖丫——一個因病而肥胖癡傻的女孩相依為命。不完整的家、不健康的女兒、困難的經濟構成了張華“殘疾”的生活。但是,生活的殘疾并沒有使張華抑郁或是瘋狂,她的積極向上、熱心、樂觀構成了她“健康”的靈魂。張華在花橋苑看守自行車棚,可憐、邋遢但熱心。面對有缺陷的女兒和艱難的生活,她以“自然、敞亮、花哨”[5]來對待不幸的命運。同時,張華在別人遇到困難時還熱心幫助,當公寓的八層十六家住戶被大雨泡壞了房子急需要裝修的時候,張華熱情地為他們尋找裝修公司,為他們談價錢省錢。當裝修公司欺騙耍賴,使她被所有的住戶責怪時,她毫不掩飾地動情大哭,卻依然不失本心,愿意無償地幫助鄰居。
由此,我們要換一種角度去看前面我們所提及到的邋遢,她的邋遢,似乎也是對生活的一種態度,一種不計較的、健康的態度。張華是樂觀的城市邊緣人物的代表,也代表了那一類人的生存哲學。這是一類以積極回應和熱情善良的健康心態來應對生活中所有的艱難與不公平的小人物,反過來看,也正是這種健康的哲學,使他們能夠在困境中快樂地活著。
(二)農民工的生存哲學。
大批農民工涌向城市,成為了城市最底層的人物,他們在城市里求生存,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與欺辱。大多數農民工從事建筑、挑運等苦力勞動,可卻收益甚微,不得不在城里艱難地生活。因此,在池莉的《托爾斯泰圍巾》中,無論是裝修工還是“老扁擔”,都以農民工的身份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生存哲學
1.裝修工人“彪悍”的生存哲學。
池莉在小說中這樣形容這些裝修工:“這樣一些農民工,來的時候,是陌生靦腆的面孔;走的時候,卻千人一面,個個都是要錢的鐵面孔。”[7]池莉還在小說中大力渲染武漢夏天炎熱的天氣,并借用裝修經理的口說:“不找農民工找誰?現在城市里的人,誰還吃得這種苦?”[8]解放后的中國,甚至是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農民工大量進城,在陌生的城市尋求生存是件艱難的事。經濟的拮據使得他們只能住最簡陋的工棚或者是簡易房。地位的卑微使得他們在城里備受欺凌,他們是廉價的勞動力,需要干著最累的活拿著最少的錢。尼采說:“生命是應該被熱愛的。”[9]那么,這些裝修工的“彪悍”,應該也是熱愛生命的表現,因為生活不容易,因為社會太過于為難他們,而他們渴望活著、熱愛生命,所以他們必須彪悍起來。就像羚羊為了活著和保護自己的孩子所做的兇猛的反抗一樣,為了生存為了愛,兇猛不再是兇猛,彪悍也不算是彪悍。這是這一類農民工的生存哲學,是那類在混亂的社會中艱難爬行的小人物在面對外界的欺凌與威脅時所采取的自我保護。
一方面,大部分來到城里求生存的農民工,都背負著家里老小所有人的生存重擔,他們不得不使自己“彪悍”起來,繼續在城市邊緣摸滾爬拿。另一方面,這些來自農村的裝修工人內心深處有一種自卑,寡言少語以及不愿與人交流是潛在自卑的外在表現的一種,而外部環境、自身條件與自我意識都是造成自卑的重要原因。
2.“老扁擔”“高尚”的生存哲學。
“托爾斯泰圍巾”是小說的關鍵,也是池莉真正想表現的一種生存哲學的象征,它象征著知識和文化、生活的理想和尊嚴。在筆者看來,池莉在小說中的一段獨白是“托爾斯泰圍巾”最好的解讀,“我認識到,人的外在形狀,是命運安排的,沒有地位,沒有錢財,沒有事業成就,那都是由不得自己的;唯有人本身的內容,主要是志與氣;有志可以帥氣,有氣可以帥本。”[11]
老扁擔在城里主要靠為城里人挑東西掙錢,他攬下為“我”和教授聶文彥家挑裝修材料上八樓的活。面對著那些城里人的指責,他選擇沉默,當老板拖欠工資時,他就像石頭一樣固執地毫不退讓,這點與前文提及的裝修工很相似,都在用彪悍來反抗欺凌。但是,讀者在心中都會把老扁擔與裝修工人區別開,老扁擔不只有彪悍,還有一種內心深處的柔軟,是老扁擔存放尊嚴的心靈世界。接著,在“我”與老扁擔進一步接觸后,卻發現老扁擔不為人知的一面。池莉賦予老扁擔卑微的身份,艱難的生活,卻偏偏給他圍上取名為“托爾斯泰”的圍巾,托爾斯泰是文學與精神追求的象征,因此將“托爾斯泰”圍巾與“老扁擔”作對比,揭示出在城市中艱難生存的老扁擔的高尚的生存哲學
老扁擔的生存哲學中所包含的“高尚”已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所包含的內容,作為這個小人物的生存哲學,它有了更豐富的內容與含義。老扁擔善良、有信仰,雖然地位卑微雖然地位卑微但竭力守護尊嚴、渴求知識,用高尚的靈魂來面對生存的困境。無論生活如何艱難,他都守著心靈那塊圣地,用知識裝飾生命,用信仰來抵抗命運,這便是老扁擔“高尚”的生存哲學的詮釋。老扁擔成功地完成了對永恒和絕對的理解以及對信仰的鑄就。
三、《托爾斯泰圍巾》中小人物生存哲學的意義
在中國文學史上,繼魯迅小說中阿Q的“精神勝利法”和余華“牛”的生存哲學之后,[13]池莉的《托爾斯泰圍巾》擴大了小人物生存哲學的表現領域。一方面,池莉塑造的寡婦張華的形象展現了城市邊緣人物的心靈世界,表現了部分處于城市邊緣的小人物樂觀積極的生存哲學。另一方面,九十年代文學與世界聯系,導致文學表現娛樂化傾向而農民工的表現缺失[14],進入二十一世紀,池莉不僅僅是為小市民立言[15],而且將農民工作為小人物的一部分,深入他們的內心,為更廣大的小人物立言。
與同是新寫實主義的女作家方方在中篇小說《風景》里呈現出來的小人物的生存哲學相比,池莉擺脫了那種“干那些能夠改變你的命運的事情,不要選擇手段和方式[16]”的生存哲學觀,呈現了一些嶄新的小人物的生存哲學。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先生認為,新寫實小說的革新意義在于“關注于人的生存處境和生存方式,及生存中感性和生理層次上更為基本的人性內容,其中強烈體現出一種中國文學過去少有的生存意識”[17]。從這個意義層面來說,池莉的《托爾斯泰圍巾》中對于小人物生存哲學的表現,也為新寫實小說的革新做出了貢獻。
參考文獻:
[1]張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人物”及其現代性[N].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10-11-20(6).
[2]惠繼東.宗教文化語境下的小人物--以《驛站長》、《外套》、《罪與罰》中的小人物為例[N].寧夏師范學院學報,2011-10-29(5).
[3](德)卡爾·雅斯貝斯.生存哲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73.
[4][9]尼采.生存哲學[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55,41.
[5][6][7][8][11][12]池莉.看麥娘[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240,239,255,256,316,325.
[10]張賢亮.文人的另種活法[M].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2013:189.
[13]林喜敬.從《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看余華的生存哲學[M].山東:青島大學出版社,2009.
[14]牛學智.文學的農民敘述:一個單調而尖銳的線索--從陳奐生、散落民間的“父親”到賈平凹的清風街[J].小說評論,2008(5).
[15]吳曉紅.為小市民立言--論池莉小說的創作精神[N].江漢大學學報,1995-8-12(4).
[16][17]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312,313.
[18]在余華的《活著》中最后以福貴與牛相依為命寓意著福貴“牛”一樣的生存哲學——堅忍,并保持著生命的韌性。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5-0005-02
作者簡介:楊慶冬,性別:女,出生年月:1991.10,籍貫:安徽淮南,學歷:在讀碩士,任職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職務:學生,研究方向:漢語國際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