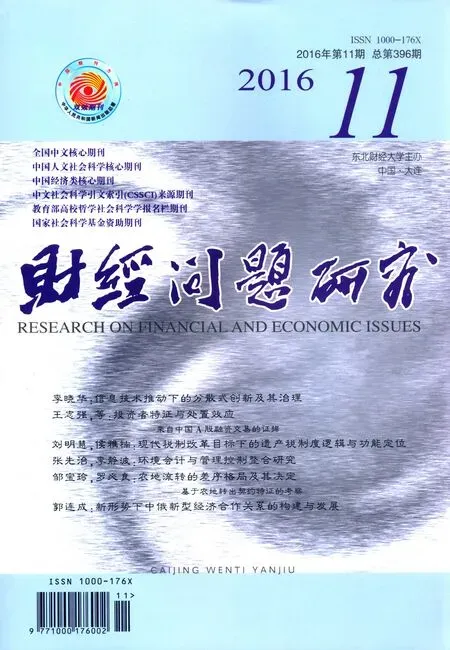自由貿易協定深度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及成因分析
文 洋
(中共中央黨校 國際戰略研究院,北京 100091)
?
自由貿易協定深度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及成因分析
文 洋
(中共中央黨校 國際戰略研究院,北京 100091)
深度一體化是當前自由貿易協定發展的主要特征。本文通過對430個自由貿易協定樣本進行比較分析和經驗研究,認為深度一體化不僅是全球貨物貿易、生產網絡、跨國投資和服務貿易不斷發展與融合所推動的結果,更是國家之間出于自身利益進行的規則重塑。基于此,筆者提出中國應加快融入深度一體化,加強探索新議題在自由貿易協定中的實踐。
自由貿易協定;深度一體化;生產網絡;跨國投資
一、引 言
各國生產力的發展、國際分工的深化和世界經濟相互依賴的加劇,客觀上要求打破國家邊界的地理限制,實現資源的跨國配置和市場規則的統一協調,因此,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紛紛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尤其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層出不窮。根據WTO網站統計,截至2016年2月,全球共有625個區域貿易協定向WTO通報,其中執行的有419個。可見,隨著貿易協定數量的增加,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也在不斷加深。
深度一體化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新特征。深度一體化(Deep Integration)類似于積極一體化(Positive Integration),積極一體化出現在WTO協定的承諾方式中,是指積極建立國內法規,使國內貿易體制與WTO義務規定更趨于一致。Lawrence[1]將深度一體化的本質定義為邊界后的一體化。與深度一體化相反的是消極一體化(Negative Integration)或淺度一體化(Shallow Integration)。國內學者東艷[2]和東艷等[3]將深度一體化定義為在降低關稅和配額的基礎上,采取更廣泛的政策來促進區內市場的進一步整合。總體來看,FTA議題范圍的擴大、合作程度的加深是深度一體化的主要特征。深度一體化的出現體現了貿易、投資和生產網絡等不斷發展的客觀要求,其功能主要體現在:第一,消除國家間邊界內的貿易和投資壁壘。第二,保護外國投資者在東道國的資產及權益。第三,通過統一協調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投資規則和政策來增強國際生產效率。
關注深度一體化的發展對中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近年來,巨型FTA(如TPP、TTIP)的出現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一方面,是因為其經濟規模巨大;另一方面,是因為其包含了諸多深層次的合作內容,被認為是國際經貿規則重塑的平臺。實際上,TPP、TTIP都是深度一體化的典型,我們在對其進行研究時既需考慮其參與成員國經濟、政治的利益訴求,同時也需考慮其形成的全球生產、消費發展的客觀背景。深度一體化是當前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形式,中國不可避免地身處其中,成為接受者、參與者乃至推動者。因此,對FTA深度合作要有清晰的認識,對其發展形成的動因進行客觀研判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深度一體化影響因子分析
Krishna等[4]對FTA進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總體來看,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分析FTA可能產生的經濟效應;另一類是探討FTA談判與簽署的原因。就后者而言,經濟學理論對各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提供了各種解釋。而近些年來,各國建立FTA合作程度加深,學者們又開始探討推動深度一體化的動因。與之前對自由貿易協定締結的經濟學解釋不同,現有學者對深度一體化的成因并沒有形成系統的研究成果。
1.貿易關系與深度一體化
通常情況下,貿易聯系越緊密的國家之間越有可能建立深層次FTA。參與深度一體化能夠維系或增強已有的貿易關系。在傳統的經濟學分析中,自由貿易協定將增加成員間的貨物貿易,使出口方從關稅減讓中獲益。隨著越來越多FTA的建立,非成員國面臨喪失市場份額的威脅,為了避免貨物貿易的轉移效應,只能要么建立新的自由貿易協定,要么加入到已經建立的自由貿易協定中,這就出現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同時,服務貿易的規模不斷擴大,對國民經濟和世界市場的貢獻不斷增強。服務貿易在全球貿易中所占比重從20世紀70到80年代的10%左右提高到2012年的20%左右。發達國家服務貿易在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更高。2012年美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服務貿易占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27.7%。服務貿易在全球價值鏈中起到總部功能、協調生產和聯系紐帶的作用,全球價值鏈依賴于服務市場的績效,因此,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將顯著增強制造業的競爭力,同時促進各國融入全球生產網絡。因此,一些國家對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要求十分強烈。
深度一體化的趨勢給各國帶來的競爭壓力不僅在于是否簽訂貿易協定,還在于簽訂怎樣的貿易協定。而深度一體化帶來的好處并不局限于像關稅一類的邊境措施,更進一步延伸到邊境內措施,如通過海關程序、政府采購、競爭政策和規則協調等進一步減少貿易成本。特別是,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面臨市場監管、勞動力流動乃至互聯網等諸多非傳統議題,更需要通過深度一體化進行協調。但要達成更多領域的協定,談判和協調成本是比較大的,如果成員之間的貿易往來原本就比較密切,那么談判收益與成本相比是可觀的,將更容易開展FTA的深度合作。此外,深度一體化對貿易流量的正向作用也被一些研究所證實[5]。
2.國際生產網絡與深度一體化
21世紀的貿易要比19世紀90年代以前的貿易復雜得多,這種復雜性是國際生產網絡不斷發展的結果,特點是將不同生產階段分布至不同國家。對于這種國際分工形式而言,在國外設置生產基地所減少的邊際生產成本能抵消離岸生產相關的非生產成本。這些非生產成本包括關稅、技術壁壘、產品標準、清關、運輸及處理海外法律程序等[6]。深度一體化協定涵蓋廣泛的規則,將有效減少非生產成本,推動國際生產網絡的興盛。因此,國際生產網絡的增加與深度一體化之間有密切聯系。對離岸外包的研究表明,盡管跨國生產者可以通過要素價格差異和新技術發展而獲益,但是國際生產分割有額外的成本。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環境、法律制度等方面差距較大,這些成本對于南北生產網絡來說更高。因此,國際生產網絡的擴大,要求實現減少國家間管理差距的深度一體化。制度框架、競爭政策和勞動市場規則等條款包括在協定中,會使得生產分工活動更加穩定,更不容易受到破壞和限制。
3.跨國投資與深度一體化
跨國投資的規模增長與結構演變對全球經濟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客觀上也要求新的投資規則對現階段跨國投資的便利性和自由化提供支持,對投資權益進行維護。從更實際的角度來看,不少自由貿易協定更應視為投資協定,因為成員間在投資領域的收益很可能超過貿易領域的收益。在深度一體化中,投資協定是核心議題,其主要目標是保護投資與實現投資的自由化。如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時,美國就要求加入減少投資風險、增加保護投資收益以及開放投資領域等條款。目前,對國家間投資協定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三個層面:第一,承諾機制視角。發展中國家簽訂國際投資協定是為了解決投資者對東道國政府的不信任問題。Stasavage[7]從這一視角出發,提出國際投資協定可以作為承諾,保證東道國政府不會發生政策逆轉,從而吸引投資流入。第二,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簽訂國際投資協定來克服政治障礙,從而有助于其推動市場改革。第三,競爭性擴散視角。由于越來越多的國家簽署國際投資協定,發展中國家擔心外商直接投資轉移,出于競爭目的簽署投資協定,一些研究為這一觀點提供了經驗證據。還有不少研究著眼于FTA對吸引外資的影響。Hufbauer和Schott[8]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東盟、歐盟和歐洲自由貿易聯盟成立及生效后,增加了成員之間的雙邊投資存量。Adams[9]利用引力模型證明投資條款對FDI有正向作用。Lesher 和Miroudot[10]分析南北型FTA的經濟影響,發現投資條款覆蓋面越廣,貿易量和外商直接投資增加越多。但是,FTA是否會增加投資流量至今尚無確切的研究結論。
三、深度一體化影響因素的經驗研究
1.FTA深化的統計與比較
大多數相關研究將自由貿易協定當作虛擬變量來進行實證分析,只考慮貿易協定是否存在,但不考慮其內容細節,將其視為“黑盒子”(Black Box)進行研究。但是,不同貿易協定的內容和范圍是有較大差異的,僅用二元方式對貿易協定進行描述和研究顯然是不夠的。因此,一些研究開始打開這個“黑盒子”,考慮特定貿易協定的設計差異,如爭端解決機制、投資、服務或貿易救濟條款等。這些研究表明,對貿易協定的設計是可以進行明確描述的。
Dür等[11]建立了DESTA數據庫,收集從1945—2009年的733個貿易協定,根據協議是否完整,是否涵蓋知識產權、政府采購、貨物標準、服務貿易、投資及競爭政策議題對FTA進行評價,滿足一個條件賦值1分,然后進行加總,最后的分數被用于反映該FTA的一體化深度,每個FTA的深度區間為0—7分。對DESTA數據庫中FTA的特征進行分析。從時間跨度來看,這些FTA的平均深度隨著時間推移并沒有呈現系統性的演變,在20世紀50年代期間的深度比較高,達到1.100,但是此后的深度卻比20世紀50年代更低,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FTA的深度才有較大提升。2000—2009年建立的FTA呈現出較強的深度一體化態勢,平均深度為3.151,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此外,表1還顯示了包含知識產權、政府采購、貨物標準、服務貿易、投資及競爭政策的FTA在樣本中所占的百分比,可見這些議題在FTA中的覆蓋率有明顯上升的趨勢。知識產權議題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都沒有涉及FTA,在2000—2009年的覆蓋率為19.3%。政府采購議題經歷較大的變化,在20世紀50年代一度達到10%的覆蓋率,可能是由于二戰剛結束,各國較快地推進貿易自由化以復蘇經濟,但在其后的一段時期中,政府采購在FTA中出現的頻率并不高,但在2000—2010年該議題的覆蓋率又上升到22.6%。貨物標準的覆蓋率最高,在2000—2009年已經達到89.2%。服務貿易和投資議題是目前FTA締結的關鍵議題,2000—2009年的覆蓋率分別為40.6%和35.9%,而受到發達國家推崇的競爭政策覆蓋率并不算高,為26.9%。

表1 1950—2009年全球貿易協定的深度及議題覆蓋率
數據來源:作者根據DESTA數據庫整理而得。
表2對比了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FTA深度及覆蓋議題。從合作程度來看,發達國家普遍比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深度高,各議題的覆蓋率也很高。其中,韓國、美國的FTA深度較高,均在6以上,而阿根廷、巴西的FTA深度最低,僅不到1。從具體議題來看,美國的所有FTA均包含知識產權、服務貿易和投資議題,表明在這些議題上推行的規則符合美國的利益要求。日本在服務貿易、投資議題的覆蓋率達到100%,意味著服務貿易與投資同樣是日本重點關注的自由化領域。韓國在競爭政策議題上表現出很大的積極性,所有FTA均覆蓋競爭政策。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的FTA深度較低,對新議題的覆蓋率不高。中國與印度等其他發展中大國相比,FTA深度明顯較高,議題覆蓋率也更廣,但在政府采購和貨物標準方面低于土耳其。阿根廷和巴西的FTA程度較淺,在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等議題上均沒有涉及。

表2 1990年以來各主要國家FTA的深度及覆蓋議題比較
注:總樣本包含DESTA數據庫中從1990—2009年所有的430個自由貿易協定。
2.模型與變量
本文對影響各國FTA深度的因素進行實證研究。根據前文的分析,將貨物貿易、零部件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作為FTA深度的影響因子進行檢驗。本文利用引力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具體設定如下 :
lndepthijt=β1+β2lnXijt+β3lnsgijt+β4lndgijt+β5lndcpijt+β6lndisij+εij
(1)
模型(1)中,被解釋變量部分,depthijt表示i國與j國之間締結的FTA深度,數據來源于DESTA數據庫。核心解釋變量部分,Xijt表示影響FTA深度的重要因素,包括tradeijt、pntradeijt、setradeijt、fdiijt,它們分別代表i與j國之間的貨物貿易總額,零部件貿易總額、服務貿易總額以及i國在j國的FDI存量。本文按照Orefice和Rocha[12]的方法,用零部件貿易來衡量兩國之間生產網絡的發展程度,其中,貨物貿易、零部件貿易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易數據庫(UN comtrade),零部件貿易定義為BEC編碼42、53及SITC編碼65的產品。服務貿易數據來源于OECD數據庫,FDI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庫(UNCTADstat)。控制變量部分,sgijt表示兩國間的GDP之和,反映兩國的市場規模和生產規模的大小;dgijt表示兩國間GDP之差的絕對值,反映兩國國內市場規模和生產能力的差距; dcpijt表示人均GDP之差,反映兩國間的要素稟賦及發展程度的差距;disij表示兩國之間的距離。各國GDP和人均GDP的數據均來源于IMF數據庫。各國之間的距離來源于CEPII的DIST數據庫。由于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FTA才呈現出深化的趨勢,因此,本文研究樣本選取1990—2009年的430個自由貿易協定。
3.結果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樣本為混合截面數據,可能會出現異方差現象。當模型中存在異方差時,在同方差假設下得到的估計量雖然仍舊是無偏且一致的,但不具有效性。因此,對可能存在的異方差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存在異方差。本文采取了克服異方差的最小二乘方法進行回歸。表3顯示了根據核心解釋變量進行的多次回歸,實證結果使用Stata14得到,具體如表3所示。

表3 實證回歸結果
注:***、**和*分別表示在1 %、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
表3的檢驗結果顯示:第一,貨物貿易額對FTA深度的影響為5%的顯著水平,且符號為正,說明貨物貿易的規模越大,兩國之間越有可能締結深度更高的FTA。第二,零部件貿易額對FTA深度的影響更為顯著,達到了1%的顯著水平,進一步驗證了前文的論述,即國際生產網絡的發達對深度一體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作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FTA將服務于國際生產網絡發展的客觀需要。第三,FDI對FTA深度的影響在10%的水平上正向顯著,說明母國在東道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存量越大,就越有可能與東道國簽署更高層次的FTA,以保護本國在東道國的投資。第四,服務貿易的回歸結果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服務貿易數據缺失較多,需要擴大樣本后進一步研究。第五,對于其他控制變量,兩國GDP之和、人均GDP之差對于FTA深度有反向影響,前者意味著兩國的市場規模、生產規模越大,越有可能進行消費、投資與分工的自我運轉,因而更少地需要通過締結深度較高的FTA來擴大市場規模,而小型經濟體常常通過推進貿易自由化來擴大市場范圍(如新加坡、中國香港);后者意味著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越大的國家間越不容易建立更深層次的FTA。這一點也比較容易理解,經濟發展程度差距越大,規則的接受程度和發展理念的差距越大,因此,不容易實現深度一體化。雙方的地理距離對FTA深度的影響也是反向的,說明經濟合作更容易在相鄰的國家之間進行,而且這種影響較為顯著。綜上,檢驗結果與本文關于深度一體化的闡述與論證基本一致。
4.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保證實證結果的準確性,本文用Kohl等[13]測算的FTA深度代替前文的depth重新估計方程,選擇樣本為1990—2011年間的235個貿易協定,以驗證實證結果的穩健性。其中,depth(C)用所涵蓋的條款數量來代表深度;depth(E)用協定中具有法律有效性的條款數量來代表深度,具體測算方法參見Kohl等[13],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注:***、**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
為簡要起見,表4中僅呈現了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用Kohl等[13]的FTA深度數據進行檢驗后,各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依然較為顯著且方向一致。因此,本文對深度一體化影響因素的分析得到了驗證。
四、結論及啟示
本文通過研究發現:一方面,不同國家參與深度一體化的程度有較大差別,發達國家比發展中國家的參與程度更高,而且各國對具體條款的接受程度也有所不同,反映了各國在一體化實踐中具有不同的政策需求;另一方面,深度一體化的形成也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客觀趨勢,是由貨物貿易、分工、投資和服務貿易不斷發展與融合所推動的。
通過以上的研究分析,有以下三點啟示:第一,深度一體化所帶來的規則變化需辯證看待。深度一體化的新規則由兩種力量推動,一種是全球化深入發展對規則變化提出新的需求;另一種是世界各經濟體出于自身利益而進行的規則重塑。因此,需要分辨哪些深層條款在全球層次治理既有效率又符合絕大多數國家的意愿與利益,這要求經濟學家、國際法學家對深度一體化的條款進行詳盡地分類與解析。第二,深度一體化的發展削弱了WTO全球貿易治理中心的地位。許多國家通過深度一體化,不僅實現了貿易自由,更推進了投資和生產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因此,以WTO為核心的傳統多邊貿易治理正面臨歷史性的轉折點。如果WTO不進行改革,只單純服務于傳統貿易的便利化,就無法幫助各國真正參與全球價值鏈,提升在國際分工中的競爭力。第三,中國應加快融入深度一體化。從2000年中國與東盟商談第一個FTA至今已經16年,中國的FTA建設取得了一定進展,截至2016年5月共簽署了14個自由貿易協定。但中國的FTA建設面臨兩個問題:一是FTA伙伴質量不夠高。中國的自貿協定伙伴經濟體量較小,與其他強勢締結FTA的經濟體相比,仍然滯后。二是中國參與的FTA深度一體化程度不夠高,很多新的經貿規則沒有進行實踐。因此,中國應該積極同重要的貿易伙伴國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做好頂層設計,在與他國商談建立FTA時,進行大量的前期研究準備工作。與此同時,妥善應對一體化新規則對中國的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競爭與博弈并不僅僅是對于貿易伙伴的爭取,更是對于規則主導權的爭奪,面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規則優勢,中國必須加快探索新的貿易議題在FTA中的應用。
[1] Lawrence, R. Z.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M].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2] 東艷. 深度一體化、外國直接投資與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區戰略[J]. 經濟學(季刊), 2009,(2):397-426.
[3] 東艷,馮維江,邱薇.深度一體化:中國自由貿易區戰略的新趨勢[J].當代亞太,2009,(4):111-173.
[4] Krishna, P.,Mansfield, E.D.,Mathis, J.H. The WTO and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From Co-Existence to Coherence[J]. World Trade Review, 2012,11(2):327-339.
[5] Ahcar, J. R., Ahcar, J. R., Siroen, J. Deep Integration: Free Trade Agreements Heterogeneity and Its Impact on Bilateral Trade[R]. DIAL, 2014.
[6] Ando, M. ,Kimura,F. Fragmentation in East Asia: Further Evidence[R]. ER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09.
[7] Stasavage, D. Private Investment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J]. Economics & Politics, 2002,14(1):41-63.
[8] Hufbauer,G.C.,Schott,J.J.Fitting Asia-Pacific Agreements Into the WTO System[R].NCCR Conference,2007.
[9] Adams,R.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Effects of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Old and New Evidence[M].Canberra:Media and Publications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2003.
[10] Lesher, M., Miroudot, S.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Investment Provision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 OECD Publishing, 2006.
[11] Dür, A.,Baccini, L.,Elsig, M. The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troducing a New Dataset[J].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14,9(3):353-375.
[12] Orefice, G. , Rocha, N. Deep Integration and Production Networks: An Empirical Analysis[J]. The World Economy, 2014,37(1):106-136.
[13] Kohl, T.,Brakman, S.,Garretsen, H. Do Trade Agreements Stimulate International Trade Differently? Evidence From 296 Trade Agreements[J].The World Economy, 2016,39(1):97-131.
(責任編輯:徐雅雯)
2016-09-21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 “國際投資規則的演變態勢、影響及應對研究”(16CGJ005)
文 洋(1985-),女,貴州遵義人,助理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研究。E-mail:wenyang@ccps.gov.cn
F745.5
A
1000-176X(2016)11-01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