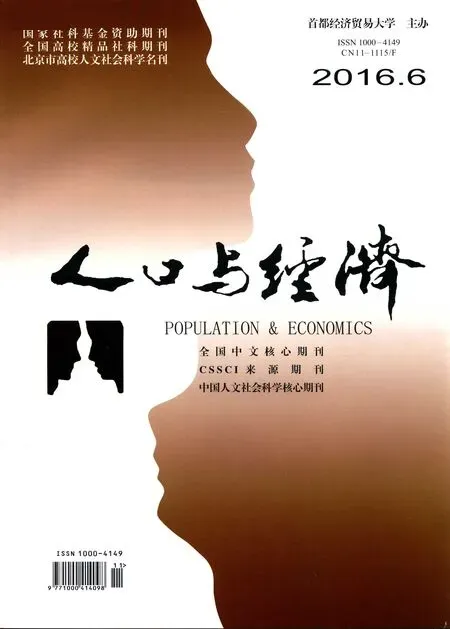中國城鎮居民家庭儲蓄水平隊列效應分析
杜本峰,劉文心
(1.中國人民大學 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2.中國人民大學 社會與人口學院,北京 100872)
?
中國城鎮居民家庭儲蓄水平隊列效應分析
杜本峰1,劉文心2
(1.中國人民大學 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2.中國人民大學 社會與人口學院,北京 100872)
利用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數據對城鎮居民家庭的儲蓄率進行了隊列效應的實證研究。分析結果表明,屬于不同隊列的城鎮家庭在儲蓄水平上都呈現出相似的“U”型年齡分布,即中年家庭(40-50歲)儲蓄率低,年輕家庭(20-40歲)和退休家庭儲蓄率較高,這一現象與其他國家的實證研究結果有顯著不同。本文認為,中國城鎮居民儲蓄率的“U”型年齡分布主要是由人口與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的:人口高速增長帶來的隊列規模效應使得面對更大競爭壓力的年輕人口儲蓄率較高,而經濟水平持續增長帶來的消費水平增長預期使得接近退休家庭儲蓄水平重新上升。
城鎮居民家庭;儲蓄率;隊列效應;生命周期
一、引言
拓展發展動力新空間,堅持需求引領,適應消費加快升級,以消費環境改善來釋放消費潛力,不斷增強消費拉動經濟的基礎作用,可以增強消費能力,改善大眾消費預期,挖掘農村消費潛力,從而最終擴大居民消費。在此,我們需要研究的問題之一是,我國居民的儲蓄消費模式在未來相比于過去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目前關于中國儲蓄率變動的研究由使用的數據可分為宏觀和微觀兩類。在使用微觀儲蓄數據的研究中,查蒙(Chamon)和普拉薩德(Prasad)研究中國居民儲蓄率隨收入上升總體逐年增加的原因,該研究使用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家庭調查數據對幾種整體儲蓄率上升的假說進行了測試,發現幾種假說都無法很好地解釋中國儲蓄率的上升[1],他們的研究使用了迪頓(Deaton)和帕克森(Paxson)的方法[2]以估算居民儲蓄率變動的年齡、隊列、時期效應,結果認為居民儲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住房、教育和醫療成本上升進而預防性儲蓄需求上升[1]。劉凱、查蒙和普拉薩德使用中國健康營養調查(CHNS)數據研究收入不確定性對年輕家庭儲蓄率的影響,認為年輕家庭的儲蓄率上升是由收入不確定性的增加帶來的,而老年家庭的儲蓄率上升與養老金改革有關[3]。張俊森等使用城鎮家庭調查數據分析了居民儲蓄的年齡結構及老年與兒童對家庭儲蓄強度的影響,在1988-1990年的數據中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年齡分布呈駝峰型,與其他經濟體中的情況類似,而2007年的數據中顯示所有的家庭儲蓄率都有了顯著的上升,儲蓄率的年齡分布由駝峰型(hump-shaped)變為“U”型[4]。
與儲蓄相關的傳統消費理論主要關注的是儲蓄水平的年齡效應,以消費者平滑跨期消費的動機為起點對居民的消費儲蓄行為進行分析。以生命周期假說為例,個體在年輕時儲蓄水平較低,隨著年齡增加,收入水平提高,儲蓄水平逐漸提高,中年時期儲蓄水平達到頂點,中年過后隨著收入降低儲蓄水平逐漸降低,個人的儲蓄隨年齡增長呈駝峰型分布[5]。截面數據的實證研究通常假設不同隊列之間的人口不存在異質性,即將年齡視作影響消費的主要因素。在這類實證研究中,消費水平往往與收入水平保持同步的增減,也呈駝峰型的生命周期分布[6]。在截面數據中,年齡和出生年份信息只能選擇一個作為變量進行分析。在進行儲蓄水平分析時,往往假設不同年份出生的個體儲蓄行為體現的是同質個體在不同年齡/生命周期下的決策傾向,這忽略了截面中不同年齡段的樣本由于出生年代不同而帶來的異質性。在社會、經濟環境長時間內變化幅度始終較小的條件下,由于不同隊列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環境較為相似,年齡成為影響家戶儲蓄決策的主要因素,故使用截面數據替代面板數據研究生命周期內的個體經濟行為即可得到較為準確的實證結果。而在經濟、社會處于快速變遷的環境中,個體決策除了受到所處年齡的影響之外,還受不同出生、成長環境的影響,即體現為隊列間的異質性。在這樣的環境下,隊列效應帶來的異質性可能大于生命周期(年齡效應)帶來的異質性,進而影響實證研究中的結論。比如,樂觀者認為,年輕隊列的消費和儲蓄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與上一代人不同,年輕群體對最低生活水平有更高的要求,進而產生更高的消費水平,同時,由于收入的持續增長,年輕群體的平均儲蓄水平也會低于上一代人。
本文希望研究的是戶主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家庭是否在消費和儲蓄行為上存在明顯的異質性,即著重分析的是隊列之間儲蓄水平的異質性。具體來說,我們想要比較和分析對于那些成長在經濟水平較高環境中的隊列群體,其儲蓄傾向是否會顯著低于上一代出生和成長于經濟水平較低環境中的隊列。基于數據的特征,本研究通過構造基準組以控制時期效應對于儲蓄水平的影響,進而來研究不同隊列在各個年齡階段的儲蓄水平變化。
二、數據與模型
1.研究對象與數據
本文選取的研究對象是1926-1980年之間出生的群體。由于中國在1955-1980年間經歷了快速的人口增長,故在此期間出生的隊列群體在總人口及勞動力市場所占比重較大,其經濟行為與整體經濟環境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同時,對于不同隊列的群體來說,經歷收入快速增長的年齡階段不同,便于我們研究收入增長的沖擊是否給處于不同年齡階段群體的儲蓄行為帶來不同的影響。
為了研究不同隊列在不同時期的儲蓄行為特征,本文分別使用了1995年、1999年、2002年、2007年的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數據。其中1995、2002與2007年的數據包含城鎮和農村兩部分,1999年僅有城鎮數據,故本文只對城鎮數據進行分析。
CHIP 1995年的調查抽樣采取了按收入水平排序的等距隨機抽樣方法,最終包括6868個城市住戶(21533個家庭成員),城鎮調查抽得的省份包括:北京、山西、遼寧、江蘇、安徽、河南、湖北、廣東、四川、云南和甘肅。1999年城市住戶收入抽樣調查數據其樣本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的大樣本,抽取方法是隨機抽樣,同時兼顧地區的代表性、城市規模和產業分布等因素。當年城市住戶調查包含4500個有城市戶口的住戶和12869個個人。其中2/3為長期記賬戶,1/3為一次性樣本戶。2002年的數據中包括了6835個城市住戶。2007年的調查中包含了5000個城鎮家庭樣本。2002年與2007年調查的城鎮部分均由國家統計局執行。
另外,調查中的消費支出數據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收集的,所以本研究也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分析。考慮到測量誤差,我們將家庭人均收入最低的1%和最高的1%的家庭戶從樣本中剔除。
2.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為了研究出生于不同年代的人群在成長過程中由于經濟、社會環境差異帶來的異質性,在實證研究中通常會將樣本按出生年份分為不同的出生隊列(cohort),來研究隊列之間經濟行為的異質性,也稱為隊列效應(cohort effect)。
隊列概念也常被應用于準面板數據的分析中。由于同一出生隊列內的不同個體存在較強的同質性,在實證研究中可使用隊列內所有觀測樣本的平均值作為隊列的代表。大多數實證數據中缺乏對同一個體或家庭的連續追蹤數據,即真實的面板數據,故可以使用隊列觀測值的均值對面板數據中的變量進行追蹤分析。
在人口學的框架中,年齡—隊列—時期模型(Age-Cohort-Period,APC模型)是研究人口隊列的經典框架。該模型把社會學、人口學中研究影響目標變量的因素分為三類:隊列因素(個體出生年代)、年齡因素(生命周期)和時期因素。但由于三者之間存在完全線性關系,也即個體年齡(Age)=時期(Period) - 個體所屬隊列(Cohort),故無法使用最小二乘法同時對其中任意兩個變量直接進行回歸。
在APC建模方法的發展過程中,研究者提出了很多數學方法來試圖解決三者線性相關的問題,但目前為止各類方法都仍然只能消除三者表面的相關性[7]。根據數據特征的不同,在某些數據中研究者可以通過主觀判斷構造包含非線性結構的模型對三者的影響進行分解,但分解后所得到的參數結果無法被驗證。
其中一種被廣泛使用的APC建模方式是把增長歸到年齡效應和組群效應之中,將年代效應定義為周期性的波動或者商業周期效應, 即假定在所研究的時間段內不同年份的時期效應相加為零且與時間趨勢正交[2],也即:


(1)
其中δt為年代效應的參數(t=1 , 2 , …, T);dt為虛擬變量,當年代為t時dt等于1, 反之dt=0。
在關于中國居民儲蓄率的研究中,周紹杰、張俊森和李宏彬采用了這種分解方法對中國城鎮住戶調查數據(Chinese Urban Household Survey, UHS)進行研究,假設時期效應加總為零,即時期效應滿足經濟周期的假設[8]。查蒙和普拉薩德的研究主要分析的是儲蓄水平的年齡效應,即居民儲蓄的生命周期規律,故其模型中假設不同隊列之間的隊列效應相加為零且與出生年份正交[1]。由于假設不同,這兩種APC模型對同一數據的分解結果也不相同。由于周紹杰等所研究的1988-2003年間中國經濟經歷了高速發展,并不符合經濟周期的假定,這種假設下的效應分解將把大部分由時期效應帶來的影響歸入年齡與隊列效應當中。而查蒙和普拉薩德的研究通過假設隊列效應相加為零來研究年齡效應,忽略了隊列之間異質性可能存在的趨勢性。
為了研究不同隊列之間的儲蓄傾向異質性,本文參考生命周期假說下的家庭儲蓄模型[9],將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savingratei=α0+α1* ln (incomei)+α2*cohorti+ ∑jα3j* familyij
+ α4j* demographicsij+∑jα5j* provinceij+εi
(2)
模型中,i表示家庭,savingrate表示對應家庭的儲蓄水平,ln(income)為該家庭收入的對數,cohort 為戶主出生隊列的虛擬變量。family為描述家庭特征的一組變量,demographics為描述戶主特征的一組變量,由于不同區域的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存在差異,模型中還加入了描述省份的虛擬變量,εi為殘差項。
因變量儲蓄率(savingratei)由以下公式計算得到:(家庭總可支配收入-家庭總消費性支出)/ 家庭總可支配收入。在1995、1999及2002年數據中,家庭可支配收入由個人總收入減去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支出后加總得到,2007年的調查中由家庭總收入減去家庭總社保支出及所得稅支出得到。數據中的家庭支出均為家庭的總消費性支出。1995、1999、2002及2007年數據中的全年總支出數據均以家庭為單位。其中1995年的家庭消費性總支出包括食物、煙酒、衣著、日用品、耐久消費品等支出,以及非商品性支出,勞務和服務、教材及參考書、學雜費、子女教育的其他支出,成人教育及培訓費,子女托兒費,贍養費,送禮或禮品支出,交通、水電、燃料、電話費支出,全家自我負擔部分的醫療費支出等共19項;1999、2002、2007年調查中的家庭消費支出包括食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和通訊、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居住和雜項等共8大項。
自變量方面:①隊列變量(cohort):按戶主的出生年份將家庭劃分為1935隊列(1931-1935年)、1940隊列(1936-1940年)、1945隊列(1941-1945年)、1950隊列(1946-1950年)、1955隊列(1951-1955年)、1960隊列(1956-1960年)、1965隊列(1961-1965年)、1970隊列(1966-1970年)、1975隊列(1971-1975年)、1980隊列(1976-1980年)。②家庭特征變量(family)。包括:家庭人口規模:由于不同規模的家庭有不同的消費模式,為控制該影響因素,我們在回歸模型中加入家庭規模的對數:ln (familysize)。兒童、老年人口負擔比:由于兒童未來的教育支出以及老年人的醫療及養老支出是家庭預防性儲蓄的主要決定因素,模型中還加入了少兒負擔比(0-14歲兒童占家庭總人口的比例)及老年負擔比(65歲及以上人口占家庭總人口的比例)來反映家庭預防性儲蓄的特征。家庭房產產權情況:由于處于居住需求的購房儲蓄也是家庭主要支出的一部分,家庭所居住的房屋產權屬性也會影響家庭的儲蓄決策。在1995、1999及2002年的問卷中,均包括家庭房屋產權性質的數據,而2007年中,與家庭房屋購置有關的信息僅有個人繳納的住房公積金,故在2007年的回歸模型中,以戶主是否繳納住房公積金為虛擬變量來反映家庭房屋購置的相關信息。③戶主特征變量(demographics)。包括:戶主教育背景:根據調查數據中的分類,將戶主的受教育水平劃分為碩士、本科、專科(大專及中專)、中學(高中及初中)、小學及沒有受過教育六類,以沒有受過教育的樣本作為對照組。戶主醫療保障類型:由于醫療支出也屬于預防性儲蓄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模型中還加入了一組反映戶主醫療保障類型的虛擬變量,在1995、1999、2002年的調查中分為四類:公費醫療、醫療保險、自付醫療費及其他,2007年的調查中還加入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四次調查的回歸中均以其他作為醫療保障虛擬變量的對照組。
由于年齡、隊列、時期存在共線性關系,使用OLS對三個變量同時進行分析一定會導致一個或多個變量被過度識別(over-identify)。在實證分析中,若可判斷所要研究的因變量僅受年齡、隊列、時期中兩種作用因素影響時,可通過排除掉多余的變量后進行估計得到較為準確的結果。梅森(Mason)和沃爾芬格(Wolfinger)在無法直接排除三種效應中某一類效應的情況下,認為分析隊列效應最為可行的方法是根據數據的特征找到一個與年齡、隊列、時期三者之一共同變化的變量,以反映三種作用因素其中之一的變化趨勢,以此變量作為基準測度,來估計隊列之間的差異性[10]。
在本研究中,我們希望研究的是各個隊列在生命過程中的不同階段(年齡)的儲蓄傾向是否具有異質性,即不同隊列之間的生命周期儲蓄模式是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此,我們將選取四次調查中處于退休年齡段的隊列的儲蓄行為作為隊列虛擬變量的基準組,通過此基準測度控制短期外部沖擊的影響(即年代效應),通過OLS回歸,比較在同一截面中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隊列相對于退休隊列的儲蓄傾向。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1.主要變量統計分析
由于支出數據以家庭為單位,本文使用戶主的出生年份來描述家庭所處的隊列。在1995年的數據中,戶主出生年份處于1929年以前及1970年之后的家庭樣本較少,故僅分析1930隊列至1970隊列(戶主于1926-1970年間出生)的樣本。出于同樣的原因,對于1999年的數據,我們選取1935隊列至1970隊列(戶主于1931-1970年間出生)的樣本進行分析;2002的數據中我們對1935隊列至1975隊列(戶主于1931-1975年間出生)的樣本進行分析;2007年的數據中我們分析1935隊列至1980隊列(戶主于1931-1980年間出生)的樣本進行分析。本研究中各主要變量的描述性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2.基準組儲蓄水平穩定性分析
在1995、1999、2002及2007年的數據中,我們分別選取調查時處于退休年齡的隊列作為隊列虛擬變量的基準組,分別為:1931-1935隊列(60-64歲)、1936-1940隊列(59-63歲)、1941-1945隊列(57-61歲)及1946-1950隊列(57-61)。在四次調查中,作為基準組的四個隊列在退休前后的儲蓄水平均較為穩定且相近。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從圖1可以看到,被選為基準測度的四個隊列在四次調查中的儲蓄率水平都保持在幾乎一致的水平上,體現了四個基準隊列的儲蓄行為有著高度的同質性;同時,被選作控制組的隊列都處于退休階段,即相同的生命周期階段。通過以具有同質化儲蓄行為且處于相同生命周期的隊列作為基準測度,我們希望比較其他隊列在不同時點下的儲蓄傾向相較于退休隊列的變化情況,進而比較隊列之間的儲蓄模式是否存在異質性。

圖1 1935-1950隊列的儲蓄水平變化情況
由圖2可以看出,儲蓄率增長的波動主要集中在1950年以后出生的隊列家庭。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一個可能影響退休隊列儲蓄行為的事件是1997年開始的養老金改革。此次改革采取“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的原則,僅適用于1997年以后退休的個人。故1935隊列及之前的隊列不受養老金改革的影響[11]。在圖2中,1935隊列其后的三個隊列的儲蓄水平變動一直體現出較高的同步性,說明養老金改革對于改革前已經退休和接近退休的隊列儲蓄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

圖2 家庭儲蓄率水平1995-2007年增長情況(按戶主出生年份)
3.我國居民儲蓄模式、影響因素與隊列效應

圖3 家庭儲蓄水平及個人可支配收入(按戶主/個人出生年份)

圖4 1995-2007年分隊列家庭儲蓄水平變化
(1)我國居民儲蓄模式。從圖3和圖4我們可以看出,1995年的調查數據,若除去1965以后的樣本,居民儲蓄仍然呈兩端低中間高的駝峰型分布。但同時可以看到,年輕家庭的儲蓄率已經顯著高于中年及退休家庭。在1999及2007年的調查數據中,年輕家庭也明顯呈現出高儲蓄傾向。與年輕家庭同時儲蓄率顯著上升的是50歲以后的家庭,而中年家庭的儲蓄率上升幅度較小,使得儲蓄水平的差距不斷加大。此時中國的居民儲蓄并不符合生命周期理論的假設,而是呈現中間低、兩端高的“U”型模式。
(2)居民儲蓄的影響因素。為了減少異方差對估計結果造成的影響,本研究使用了異方差穩健標準誤。其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估計方程結果

續表
注:括號內為對應的t值。*p<0.05,**p<0.01,***p<0.001。
由回歸方程的收入變量系數可以得到,在各個年份里,收入水平都是影響儲蓄率的最主要因素。在控制收入水平后,仍然存在隊列的儲蓄水平差異,所以單純從收入水平入手不能很好地解釋居民儲蓄率年齡分布中的“U”型結構。
由家庭特征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2002年以后,養育下一代的成本顯著提高了家庭預防性儲蓄的強度。這個變化很大可能是由1999-2002年間進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帶來的。教育改革使家庭的預期教育支出增加,故提高了相應的儲蓄水平。這與楊汝岱和陳斌開對家庭在教育方面的預防性儲蓄的研究結果相一致[12]。
在1995年的回歸模型中,戶主的教育程度對家庭儲蓄有顯著的影響,教育程度越高,儲蓄強度越低,表明此時高學歷被普遍認為能夠在未來帶來較高的收入,進而產生較高的終身收入預期,故高學歷的家庭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儲蓄水平較低。由回歸結果來看,1995-2007年間大學擴招前后,學歷與個人終身收入預期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
在醫療保障政策方面,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顯著地降低了家庭的儲蓄水平,與基于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及CHNS數據的研究一致[13-14]。
住房需求在許多文獻中被認為是家庭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原因之一,但1995與1999年的回歸結果顯示住房對于家庭儲蓄水平的影響并不明顯。而2002年的回歸結果表明,相比于房屋產權不清的家庭,其他所有家庭的儲蓄水平都顯著較低。其中房屋產權為單位公房的家庭儲蓄水平顯著低于其他家庭,而租賃房屋的家庭與自購房產、繼承房產、其他類別單位公房的家庭儲蓄水平接近。趙西亮、梁文泉和李實的研究發現,房產價格的上漲與家庭儲蓄的增加沒有直接的關系。在2002年之后,根據趙西亮等人進行的實證研究,對于有房產的家庭,房價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提高了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而對于租房家庭,房價上漲并沒有顯著提高家庭的儲蓄率[15]。
(3)儲蓄水平的隊列效應分析。表3和圖5顯示, 1950、1955、1960、1965隊列在進入41-50歲區間時的儲蓄傾向都顯著低于剛剛退休的隊列;而1970隊列在26-30歲區間內表現出的儲蓄傾向顯著地高于退休隊列,1975隊列也表現出類似特征,與查蒙和普拉薩德的研究結果相符[1];除此之外,1975隊列在進入31-35歲區間后儲蓄傾向顯著低于退休隊列,1970、1965隊列也表現出類似特征。由于調查跨度僅12年,在有限的數據中,各個隊列在不同年齡間所表現出來的儲蓄傾向大體相同。在不同的隊列間都呈現出類似的“U”型生命周期規律。與傳統的消費習慣理論不同的是,年輕隊列的儲蓄水平并不完全低于較早出生的隊列,而與收入水平及所處的生命周期有關。

表3 隊列虛擬變量回歸系數
注:*p<0.05,**p<0.01,***p<0.001。

圖5 隊列虛擬變量回歸系數隨年齡變化情況(以退休隊列為基準組)
中國居民的“U”型儲蓄年齡分布主要可從兩個角度進行分析:年輕與退休家庭的儲蓄率上升速度顯著高于中年家庭;在儲蓄水平隨收入水平同步提高的情況下,中年家庭的儲蓄傾向降低。
中國儲蓄率的“U”型分布與幾乎所有經典的儲蓄理論的預測相悖,包括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布倫伯格(Brumberg)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論和弗里德曼的終生收入假說。消費習慣(habit formation)理論是解釋儲蓄率上升的一種可能:即中國的節儉傳統可能是使得儲蓄率持續提高的原因[16]。但周紹杰在研究中發現年輕人的邊際儲蓄傾向顯著高于老年人,這與本研究中發現的特征相一致[17]。由于老年人被認為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較大,消費習慣理論無法解釋年輕人的高儲蓄傾向。查蒙和普拉薩德使用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家庭調查數據對幾種整體儲蓄率上升的假說進行了測試,研究認為居民儲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住房、教育和醫療成本上升進而預防性儲蓄需求上升[1]。劉凱、查蒙和普拉薩德認為退休隊列的儲蓄率上升與養老金改革后的養老金替代率下降有關,但從數據中可以看到,養老金改革后隊列間的收入分布并沒有產生巨大的差異,處于退休隊列的個體收入并沒有顯著低于中年家庭。因此,養老金改革難以很好地解釋收入水平相似的中年與退休家庭之間儲蓄差距逐漸拉大的現象[3]。
本文認為,除了上述幾個原因之外,還應從中國的特殊人口結構、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勞動力市場變化及收入增長的角度入手對城鎮居民“U”型生命周期儲蓄分布的形成進行分析。
首先來看人口結構因素。不同隊列間在進入41-50歲區間后儲蓄水平顯著低于退休隊列及年輕隊列可能是由持續的隊列相對規模效應(relative cohort size effect)帶來的。伊斯特林(Easterlin)提出的隊列規模理論認為,個體終生的經濟福利與其所在隊列的相對規模呈負相關。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出生率越高,對應出生的隊列相對規模越大,其社會和經濟福利受到的負向影響越大。這種負向的隊列規模效應通過家庭、學校及勞動力市場中的“擠壓”(crowding mechanism)機制影響個體最終的社會及經濟福利。在勞動力市場中,由于年輕勞動力無法完全替代熟練勞動力(prime-age workers),即工作經驗對于勞動力的工資有著顯著的影響,當年輕隊列的隊列規模高于其所要替代的隊列時,其工資水平會受到擠壓而整體下降[18]。

圖6 1926-1980年出生隊列在20-24歲時的隊列規模 數據來源:聯合國人口數據(2012年)。
如圖6所示,從1946年開始中國的人口隊列規模呈不斷上升趨勢,期間1959-1961年發生了三年自然災害,1962-1970年隨之出現補償性生育的人口高峰,1976-1980年間出生的人口開始顯著下降,1980年9月,中國開始實施嚴格計劃生育政策,隊列規模開始減小。可以看到,1951年開始,隊列規模就有了明顯的上升,但中國居民的儲蓄水平年齡分布在1990年初仍然呈現駝峰型的分布[4]。若隊列規模效應成立,20世紀90年代初已經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隊列(1965年以前出生的隊列)應該同樣表現出高儲蓄率。但由于隊列規模效應是通過勞動力的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即隊列人口規模增大,供給增大,工資下降,隊列預期終身收入下降。在1995年國企改革之前中國城鎮地區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水平并非由供需決定,而由國家部門統一規定。國企改革使得城鎮勞動力市場的市場機制開始發揮作用。國企改革之前,中國城鎮居民的工資水平并不由勞動力市場的供需機制決定,居民的工資收入對于居民來說幾乎是有完全信息的。許多研究都顯示80年代底到90年代中中國城鎮居民的儲蓄年齡分布呈駝峰型[1]。
1990-2000年間,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完成了國企改革。改革之前,所有的城鎮勞動力幾乎都在國有企業工作,個體沒有失業風險,畢業后的工作單位為國家安排無法自行更改。工資水平由國家進行規定,不同企業間的工資差異較小,工資水平較低但有很好的社會福利保障措施,退休后的個人與退休前領取相同的工資。根據埃德·華池(Chi)基于中國國家統計局1989-2009年城鎮居民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個體所處隊列的人口規模對其起始工資水平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種負向影響到開始工作五年后才開始逐漸消失[11]。這種由隊列相對規模帶來的工資擠壓效應或許可以部分解釋數據中的幾個隊列在年輕時的高儲蓄傾向:由于工資擠壓,家庭對未來的總收入預期下降,為保證期望的生活水平,相應的,其消費下降,儲蓄上升。工資擠壓效應隨著工作經驗年限增加逐漸減小,這可能是由教育水平對工作經驗有著部分的替代作用促成的。同時,由于后續出生隊列的規模仍處于較高水平,隊列在勞動人口中的比例也逐漸下降(如圖7)。結合工資擠壓效應的消失與隊列人口占比下降兩方面因素,當隊列進入35-50歲階段,成為勞動力市場中的成熟勞動力后,對未來的預期收入提高,其消費水平提高,儲蓄水平逐漸降低。

圖7 各個隊列在勞動力人口中的人口比重(20-60歲) 數據來源:聯合國人口數據(2012年)。
隨著經濟發展,總體生活水平提高,每一個隊列對于最低生活水平的期望(material aspirations)也逐步提高[18]。這種作用機制可能可以解釋為什么在經濟發展背景下接近退休的隊列的儲蓄水平會重新提高:由于收入上升,居民消費水平上升,在預期退休后價格水平將持續上升的情況下,居民為了在退休后能維持同樣的消費水平而提高儲蓄水平。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1995、1999、2002、2007年中國居民收入調查(CHIP)數據中的城鎮數據考察了不同隊列間的儲蓄傾向隨年齡增長的變化情況。以各次調查中處于退休年齡段的隊列的儲蓄行為作為隊列虛擬變量的基準測度,通過OLS回歸,比較在同一截面中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隊列相對于退休隊列的儲蓄傾向。結果表明,不同隊列在調查的年份中均體現出“U”型的儲蓄水平變化:在年輕時儲蓄水平較高,隨著年齡增加儲蓄水平下降,到接近退休年齡儲蓄水平重新上升,這個特征對數據中的大部分隊列都成立。
對于中國居民儲蓄為什么會呈現“U”型生命周期分布,學術界還沒有共同的結論。本文認為,居民生命周期儲蓄水平的“U”型變化的可能性之一,是個人收入預期受隊列相對規模效應與個人消費水平不斷提高共同作用的結果。由于隊列規模不斷增加,年輕隊列在勞動力市場的初始工資水平受到負向影響,個人收入預期較低,進而不得不提高儲蓄以保證未來消費水平;隨著工作年限增加,隊列相對規模效應逐漸消失,同時隊列在勞動力人口中占比下降,隊列收入預期提高,相應的其儲蓄水平降低,消費水平提高;由于預期未來消費及物價水平仍會提高,為保持退休后的消費水平,接近退休的個體儲蓄水平又重新提高。簡而言之,在其他變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個體儲蓄水平受其對于未來收入水平的預期和物價水平(支出)的預期影響,而個人對于未來收入的預期,受隊列相對規模影響:對于未來收入水平預期越悲觀,儲蓄率越高。
由結論部分我們知道,提高消費水平主要有兩個途徑:①提升個體對于未來收入水平的預期;②形成對物價水平的穩定預期。
對于年輕人來說,提升未來收入水平(及預期)的主要途徑有:一是鼓勵個體進行有效的人力資本投資(例如:有市場需求的職業技能訓練),提高就業率及工資水平;二是減少勞動力市場的摩擦,增加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效率和集聚程度。
對于收入來源較為單一的老年人而言:養老金的水平如果與物價水平掛鉤并形成穩定預期,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消費;同時,還應鼓勵商業養老金、養老保險市場發展。
綜上所述,提升消費水平的最重要途徑是提高個人對于未來收入水平的預期,本質是提高個人對于人力資本的投資和改善經濟運行,尤其是就業市場運行的效率。
[1] CHAMON M, PRASAD E S.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8,2(1): 93-130.
[2] DEATON A, PAXSON C. Growth,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national saving in Taiwan[J]. General Information, 1998,26(2):141-173.
[3] LIU K, CHAMON M, PRASAD E. Income uncertainty and household savings in China[J]. General Information, 2013,105(5):164-177.
[4] YANG D T, ZHANG J, ZHOU Shaojie. Why are saving rates so high in China?[R].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2011.
[5] MODIGLIANI F, BRUMBERG R.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 Rutgers,1954.
[6] CARROLL C, SUMMERS L H. Consumption growth parallels income growth: some new evidence[R].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1989.
[7] FIENBERG S E. Cohort analysis’ unholy quest: a discussion[J]. Demography, 2013, 50(6):1981-1988.
[8] 周紹杰, 張俊森,李宏彬. 中國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費和儲蓄行為:一個基于組群的實證研究[J]. 中國經濟學, 2009(3):1197-1220.
[9] 范敘春,朱保華. 生命周期假說在中國成立嗎——兼論儲蓄率的生命周期分布及其動態演變[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 2013(3):16-28.
[10] MASON W M, WOLFINGER N H. Cohort analysis[R]. California Center for Population Research UCLA,2001.
[11] CHI Wei. FREEMAN R, LI H. Adjusting to really big changes: the labor market in China, 1989-2009[R]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2012.
[12] 楊汝岱,陳斌開. 高等教育改革、預防性儲蓄與居民消費行為[J]. 經濟研究, 2009(8):113-124.
[13] 周曉艷, 汪德華,李鈞鵬.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對中國農村居民儲蓄行為影響的實證分析[J]. 經濟科學, 2011(2):63-76.
[14] 寧滿秀, 潘丹,李曉嵐.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對農戶預防性儲蓄的擠出效應研究——基于CHNS數據的經驗分析[J].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3):32-37.
[15] 趙西亮, 梁文泉,李實. 房價上漲能夠解釋中國城鎮居民高儲蓄率嗎?——基于CHIP微觀數據的實證分析[J].經濟學(季刊), 2014(1):81-102.
[16] CARROLL C D, WEIL D N. Saving and growth: a reinterpretation[R].NBER working paper, No. 4476,1994.
[17] ZHOU Shaojie. Essay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household saving behavior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7:57-75.
[18] EASTERLIN R A. What will 1984 be lik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ecent twists in age structure[J]. Demography, 1978,15(4):397-432.
[責任編輯 方 志]
China’s Urban Households Savings Queue Effect Analysis
DU Benfeng1, LIU Wenxin2
(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is paper, by using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Survey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 data, queue for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effect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urban familie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queue on savings are showing a similar u-shaped age distribution, the middle-aged (40 to 50 years old) family savings rate is low, while the young families (20-40 years old) and the retirement household savings rate is higher, the phenomenon is different wit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in other countr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U ag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urban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s mainly caused by the rapid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The queue size effect of population growth make the young people face the greater competitive pressure cause higher savings rate, while the sustained growth and the expectation of consumption growth make nearing retirement level of household savings rise again.
urban households; savings rate;queue effect; life cycle
2016-04-05;
2016-07-15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1373272);中國人民大學品牌研究項目(10XNI02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12YJAZH012)。
杜本峰,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劉文心,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本科生。
C92-05
A
1000-4149(2016)06-0021-14
10.3969/j.issn.1000-4149.2016.0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