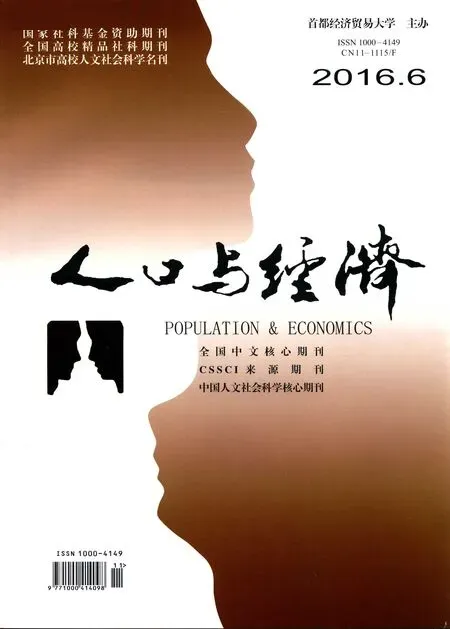基于人口遷移的中國城市體系演化預測研究
勞 昕,沈體雁
(1. 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北京100084; 2.北京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北京100871)
?
人口學綜合
基于人口遷移的中國城市體系演化預測研究
勞 昕1,沈體雁2
(1. 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北京100084; 2.北京大學 政府管理學院,北京100871)
從中國城市化的本質——人口遷移網絡出發,考慮所有城市空間單元以及城市間人口遷移聯系在內,開展人口遷移和城市體系的綜合性研究,探討中國城市體系演化機理,將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拓展到多區域,引入地理空間異質性,構建空間參考明確、全域均衡、空間單元之間存在明確人口遷移機理的城市體系模型。通過實證檢驗,該模型的模擬結果較為接近實際情況,模型擬合精度較高,可以用于城市體系演化預測。根據目前中國實際國情和國家政策導向,本文在三種大的城市化情景下根據中國各城市間人口遷移來預測中國未來城市體系的演化,即把整個城市體系視作一個通過人口遷移相互聯系的網絡整體來預測城市人口變化情況,從而為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的流動人口管理、公共服務改進和城市等級體系規劃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現實依據。
人口遷移網絡;城市體系演化;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模擬與預測
一、 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為中國社會變遷的重要特征,大規模跨地區的人口遷移既源于改革開放初期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優先發展戰略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又源于人口遷移政策和戶籍政策的逐步放松。截至2014年末,全國流動人口總量達到2.53億,超過總人口的1/6*數據來源: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伴隨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發展,人口遷移直接導致各等級城市數量及城市規模變化,進而影響城市等級規模結構和空間格局變化。城市體系作為一國或一地區各種規模、類型城市空間分布結構的有機整體,是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空間依托。城市體系的城市間不僅僅由城市等級體系及城市規模分布等已有研究所揭示的那樣,僅存在競爭及等級關系,更重要的是存在合作與相互關聯的網絡互補關系。從人口遷移的視角來看,城市體系中的所有城市通過相互間的人口遷移聯結成一個網絡,通過這種空間聯系將地域上分散的城市整合成一體。本研究通過對區域經濟學、城市地理學領域密切相關的重要研究問題——人口遷移和城市體系的二者關聯加以探索,輔以人口學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相關理論,全面深入展示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及共同演化機理。
目前相關方面研究存在的問題及本研究為彌補這些缺陷所作的貢獻如下:①現有城市體系模型(經典城市體系模型和新經濟地理學城市體系模型)均以一維空間為主,一般只有兩區域或者少數區域,且為均質空間,難以落實到真實地理環境上進行實證檢驗[1-6];本研究通過引入地理空間構造和地理空間異質性,將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從一維線性空間拓展到二維平面空間,從兩區域拓展到多區域,用于模擬和預測中國真實城市體系的演化,以推進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實證研究發展。②目前中國人口預測多為基于單個城市的局部人口增長模型,缺乏將整個城市體系視作一體的人口空間格局預測演繹研究[7],且人口遷移研究空間尺度較為宏觀[8-15];本研究構建了考慮所有城市單元以及城市間人口遷移聯系的全域網絡模型,即把整個城市體系視作一個通過人口遷移相互聯系的網絡整體來預測各城市人口變化情況,并將中國人口遷移的重要影響因素引入模型,以深化新經濟地理學模型的人口遷移機制,并將中國人口遷移研究的空間尺度從省級單元拓展到城市層面。③目前城市體系演化和人口遷移都已形成較為完整的獨立理論體系,而將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分析并未形成系統的研究框架[16];本研究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理論中的城市體系演化模型[3],構建人口遷移和城市體系的綜合性研究框架,因為該模型中的城市規模分布變化是由城市間人口遷移決定的。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梳理城市體系相關理論模型,采用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構建理論模型,以解釋城市間人口遷移是如何影響各城市人口規模變化的,并在此模型基礎上引入城市等級體系構建;然后用理論模型來模擬中國城市體系實際演化過程,模型擬合精度經過檢驗后,在不同的城市化情景下預測未來城市體系演變,為合理引導城市間人口遷移和優化城市化空間格局提供決策參考。
二、 模擬流程說明
從本文的研究目的出發,構建理論模型,需要解決以下問題:一是需要分析人口遷移對城市體系演化的影響;二是將城市體系視為一個整體,通過城市間的人口遷移連接成一個緊密聯系的城市網絡,各城市人口的變化是相互影響的;三是需要將現有城市體系模型拓展到多區域,且初始時各區域為非均質的,使得城市體系模擬結果可以落實到真實地理空間上。
經過比較選擇,作者發現新經濟地理學的城市體系演化模型[6,17-18]能夠滿足以上條件:一是模型中各地區人口規模變化是由地區間人口遷移導致的;二是多區域情況下模型中的各地區是通過人口遷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三是在已有研究中,斯戴爾德(Stelder)[18]和葛瑩等[19]引入地理空間構造和空間異質性對該模型進行改進,分別用于歐洲和中國浙江省城市體系演化模擬,模擬結果大體符合現實。因此本研究將借鑒該模型來模擬和預測中國城市體系演化。
根據人口遷移影響機制*根據相關人口遷移理論,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本文提出以下幾種影響人口遷移的重要因素:人口規模、經濟發展水平、公共服務水平、地理環境條件(包含居住條件和環境質量等)、社會網絡、空間距離和政策因素。(采用引力模型,計量分析結果見表1),在藤田昌久、克魯格曼和維納布爾斯(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的城市體系模型[6]中引入含有公共服務水平的效用函數以及兩兩地區間的空間距離矩陣,經濟發展水平用模型中的工資和收入表示,各地區的地理優勢度可用

表1 中國省際人口遷移影響因素計量分析結果
數據來源: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2000);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中國統計年鑒》(1999、2004、2009)。
注:1.括號中為對應的顯著性水平(p值),比值指的是遷入地和遷出地之間各因素的相對差距(即Xj/Xi),表格中只標出通過顯著性檢驗的變量回歸系數;2. 流動鏈指數等于遷出人口在各遷入地的構成比(i省流向j省的遷移人口/i省的總遷出人口)。
異質性的農民數量來表示,政策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則主要通過對公共服務水平的影響來實現,社會網絡聯系由于難以定量表示而沒有直接顯示在模型中。
模型基本構架如下:假設有N個城市/地區組成的城市體系,在該城市空間格局模型中,假設農業A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制造業M是壟斷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在達到短期均衡狀態時,生產者的利潤均為0,且供需平衡。具體到消費者,他們的生活費用就等于他們在經濟中所賺的勞動收入。所有地區的農民總數為LA,且每個地區的資源稟賦即農業勞動力份額是外生變量且既定的,記為φi。與此相對應,制造業的勞動力是隨時間變化的。用LM表示所有地區的工人總數,并且用λi來表示地區i在任何時點上的制造業勞動力份額。適當地選擇單位可使得LM=μ,LA=1-μ。

(1)
其中,M代表制成品消費量的綜合指數,A是農產品的消費量,S是公共產品的消費量,μ是制成品的支出份額,(1-μ)是農產品的支出份額。γ顯示消費者的效用關于地方公共品的彈性,即地方公共品供給每增加一單位,消費者福利水平提升γ倍。因此γ數值越大,顯示消費者對公共產品供給越敏感,體現在福利偏好上,即相對的更加偏好地方公共品。除以分母μμ(1-μ)1-μγγ(1+γ)-(1+γ)是為了簡化間接效用函數的形式。
將公共品視為模型的外生變量[20],設地區i公共產品供給量Qi是外生的,且為工人份額λi(城市規模)的增函數,由于在大多數情況下,城市層級越高(即規模越大),居民能享受到的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包括醫療、教育等)越多;但城市戶籍制度決定了勞動力是否能夠享受到公共產品,而城市層級越高,戶籍制度越嚴格,遷移人口獲得公共產品的難度越大[21],因此令λi的增長系數ε<1。則
(2)
在已知制造業勞動力分布,以及短期內勞動力在區域間不能流動的前提下,將以上公式代入藤田昌久、克魯格曼和維納布爾斯的城市體系模型[6],可推導出城市空間格局的短期均衡模型包括以下4個方程:
Yi=μλiwi+(1-μ)φi
(3)

(4)

(5)

(6)
其中,Yi是地區i的消費者收入,Gi是地區i的價格指數,Ui是地區i的間接效用函數,σ表示任意兩種制成品之間的替代彈性,piS是地區i的公共品價格。

假定工人會從效用水平低于平均效用水平的地區流向效用水平高于平均效用水平的地區,則將平均效用水平定義為:
(7)
同時假定人口遷移動態方程為:
(8)
其中ηi為遷移速度,即地區i人口的凈遷入量dλi與地區i的城市人口規模λi成正比,若地區i的效用高于所有地區平均效用,則地區i為凈遷入地,反之則為凈遷出地。
根據中國實際情況,將各城市人口分為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兩部分[22],城市實際規模應由城鎮人口來測度,不同規模城市的存在,產生城市的等級體系。各城市規模(城鎮人口)的變化由城鎮地區間的人口遷移和農村地區往城鎮地區的人口遷移共同決定:
Pu(i,t)=[uPu(i,t)+dλi+rPu(i,t)]*(1+bi)
(9)
其中
uPu(i,t)+dλi=λi,rPu(i,t)/Pu(i,t)=α
(10)
其中Pu(i,t)為i城市t時刻的城鎮人口,uPu(i,t)為原先和現在都在i城市城鎮地區的人口,rPu(i,t)為原先在農村地區、現在在i城市城鎮地區的人口,dλi為從其他城市的城鎮地區遷入i城市城鎮地區的人口,α為遷入i城市城鎮地區的農村人口與該城市城鎮人口的比例,bi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簡化研究將α設為全國統一的常數。

當圖1中兩個判斷條件均滿足時,可以得到在均衡狀態下,各區域勞動力λi的分布;只有當上述步驟對所有區域均滿足時,求解過程才可能停止。

圖1 城市體系模擬過程示意圖
三、 模擬結果分析
參考相關研究的經驗參數值,并經過反復調試后將模型中的參數值設定如下:μ=0.4,σ=5,τ=1.5,γ=5,ε=0.7,η=0.5;初始數據主要來源于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其中λi取各地級單元2000年城鎮人口數,wi取各地級單元2000年人均GDP來代替(該數據能更好地代表各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農民數量φi用地理優勢度賦值法*分別按各個省份所屬的地形分區、溫度帶分區和干濕帶分區對其進行賦值然后加總求和,各地級市的地理優勢度得分與其所在省份一致:地形分區中第一階梯賦值為1,第二階梯賦值為2,第三階梯賦值為3;溫度帶分區中高原氣候區、寒溫帶賦值為0,中溫帶賦值為1,暖溫帶賦值為2,亞熱帶賦值為3,熱帶賦值為4;干濕帶分區中干旱區賦值為0,半干旱區賦值為1,半濕潤區賦值為2,濕潤區賦值為3。來推算求得(各地區農民數量與其地理優勢度成正比,總和等于全國不遷移的農民數量),Dij取兩兩地級單元間的直線地理距離,各組初始值根據實際需要進行歸一化或者標準化處理。如式(9)和式(10)所示,Pu(i,t)=[λi+rPu(i,t)]*(1+bi),即根據模型模擬出各地級單元所占人口份額(此時的λi),再加上農村地區往城鎮地區的人口遷移部分rPu(i,t),并考慮人口自然增長率bi,從而計算出各地級單元2010年模擬城鎮人口數Pu(i,t)。為使模擬結果更接近真實情況,并結合數據可得性,各個地級單元的城鎮地區采用2009-2010年間各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農村地區(即農村地區往城鎮地區的遷移人口rPu(i,t))采用2009-2010年間全國統一的農村地區人口自然增長率,該兩項數據均來自于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由于本研究重點在分析由城鎮人口測度的城鎮體系,農村人口部分只需考慮往城鎮地區的轉移人口,且農村人口自然增長率缺乏地級市層面的詳細數據支撐,故用全國總體數值來簡化計算。經過反復修改模型和程序,多次試驗,最終得到的模擬結果表明,擬合精度較高,模型通過了檢驗。下面分別從模型本身的擬合精度、模擬所得的城市間人口遷移和城市等級體系結構這三個角度,與實際情況進行比較分析。
1. 模型擬合精度評價
模型擬合精度用模擬值與實際值的比值(即二者吻合率)來表示,平均值為99.58%,中位數為101.62%,最小值為38.74%,最大值為134.10%,標準差為14.00,擬合精度較高。且從圖2可看出,擬合精度圍繞100%的精度呈正態分布,絕大部分擬合值都接近于實際值(介乎75%-125%間)。

圖2 模擬值與實際值吻合率的分布直方圖 數據來源: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2000)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1》,圖3-6數據來源同圖2。

圖3 2010年各地級單元實際人口數與模擬人口數相關關系分析
從實際人口與模擬人口的比較(見圖3)也可以看出,二者呈顯著的正相關,相關性非常高,決定系數為0.9586,從另一側面證明了模擬結果非常接近現實。
2. 城市間人口遷移的模擬結果與實際情況比較
本文對各地級單元的模擬凈遷入人口與實際總遷入人口進行相關分析,得到Pearson相關系數為0.699,顯著性水平為0.01,表明二者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性。
由圖4可看出,模擬凈遷移人口空間分布與實際總遷入人口數的空間分布格局大體上類似:東部沿海地區遷入人口數較多,為凈遷入地;西部和中部大部分城市遷入人口較少,為凈遷出地;全國主要遷入地區都集中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區這幾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與實際情況有出入的主要為西部地區的部分城市,遷入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被高估了。西部遷入人口較多,可用自2005年起東部移民比重仍占絕大部分但已開始下降這一事實來解釋:隨著西部大開發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轉移到西部地區,新的就業和發展機會吸引了部分人口的遷入或遷回,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勞動力的外流。

圖4 各地級單元的模擬人口遷移空間分布與實際情況比較
3. 城市體系的模擬結果與實際情況比較
總的來說,用理論模型模擬2010年地級市層面的真實城市體系,通過分析發現模擬城市體系的以下幾方面特征與實際情況都基本一致。
(1)城市體系等級結構:從地級市層面來看,城市等級體系中,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數量最少*按照國務院2014年10月29日印發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將全國地級市劃分為五個級別: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城市為小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城市為中等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大城市數量最多,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數量相對較少;2000-2010年間,超大和特大城市數量增加且規模增加較大,大城市數量增長較快,而中小城市的數量有所減少,中小城市往大城市的晉級發展較為迅速。
(2)城市體系首位度特征:全國城市規模分布并不服從首位律,首位城市上海的集聚和輻射作用有限,整個城市體系呈雙中心或多中心分布,2000-2010年間首位度指數略有下降。
(3)城市體系位序—規模分布:全國城市體系大致符合位序—規模分布,且位序—規模等級結構比較穩定,位序—規模曲線十年間近似平行向前推移(見圖5),表明全國城市人口數整體不斷增大;十年間城市體系均衡程度逐漸加強,與首位度指數下降的趨勢正好一致;從理論上來說,就城市規模結構合理性來說,高位次城市還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

圖5 2000年和2010年中國城市位序—規模分布圖
(4)城市空間分布格局:城市數量和規模分布空間差異明顯,東部地區與其他三個區域相比,無論是城市數量、城市規模、大城市數量都占絕對優勢(如圖6所示)。
四、 預測結果分析
從模擬結果分析可看出,理論模型擬合精度較好,已通過實證研究的檢驗。因此,根據該理論模型,代入2010年各地級單元初始數據,采取同樣的模擬流程(見圖1),在不同的城市化發展情景下來預測中國未來(2020年)城市體系演化。按《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2020年要實現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的目標,令2020年城鎮化率為60%,與2010年全國城鎮人口比例(49.68%)相比增長了10.32%,即2010-2020年間共有14174萬農村人口往城鎮地區轉移,這與目前中國城鎮化發展趨勢基本一致(2015年全國城鎮人口比例為55.88%)。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公報,2015年全國總人口為137349萬人,按2010-2015年的自然增長率計算,2020年全國總人口為140810萬人。各地級市2010-2020年人口預測自然增長率仍按2009-2010年間的城鎮和農村地區自然增長率來計算*2005-2010年間,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64%,年均增長0.52%;2010-2015年間,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52%,年均增長0.5%;二者較為接近,可用該人口自然增長水平來預測2015-2020年間人口增長情況。此外,2009-2014年間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基本保持穩定(在0.48%和0.52%間波動),在無其他替代數據的情況下,可用2009-2010年間各地級市自然增長率進行外推來預測2020年人口。。

圖6 2010年地級單元模擬城鎮人口與實際城鎮人口空間格局比較
1. 自組織發展情景下的預測結果
這是城市體系演化預測的基準情景,即不設計任何城市化情景,按目前的發展趨勢預測2020年城市體系演化情況。
從表2可看出,2010-2020年間,城市體系演化仍然保持原來的(2000-2010年間的)發展趨勢:各級城市的規模,以等級未變的最多;其中特(超)大城市數量和規模比例都出現大幅度增長,數量增加了13個(即有13個大城市晉級成特大城市),規模比例增加了8.19%;大城市數量有一定增加,所占規模比例卻下降了;中小城市數量有所減少,規模比例也有所下降,但發展較為迅速,其中有35個中等城市晉升成大城市,9個小城市晉升成中等城市。未來中國新的城市面貌具體會呈現出何種具體形態是無法準確預測的,但如果國際經驗具有一定啟發意義的話,那么中國沿海大城市的人口增速將快于中國城市的平均水平,而中小城市的人口比例有可能會下降[23]。從地級市層面來看,中國總的城市體系演化趨勢還是以100萬人以上規模的大城市為主導的。

表2 自組織發展情形下預測得到的2020年城市等級結構
數據來源: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1》,表3-4數據來源同表2。
總的來說,根據預測結果來看,如果保持目前的發展趨勢不變,2010-2020年間,地級層面城市規模等級結構和城市空間格局都相對保持穩定,大部分城市規模有所增加但等級保持不變,只有少數城市躍升了一個等級,以大城市的發展最為迅速。人口規模較小的地級單元人口減少的幅度較大,這些發展較落后的小城市由于地處西部內陸,過于偏遠,或者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因而吸引不到人口,隨著時間推移有可能會漸漸消失。
2. 不同城市化發展模式下的預測結果
關于中國城市化發展模式的爭論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定論:小城鎮論者強調根據中國的基本國情,應以小城鎮為主推進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提出要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大城市論者依據理論分析,或強調大城市優先發展的階段性規律,或強調城市規模的集聚經濟效應;中等城市論者則試圖兼顧兩者的優點;還有學者從城市體系理論出發,提出“大中小城市相結合”的觀點,主張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以不同規模等級的城市為主導發展,將形成不同結構的城市體系。
本文對特(超)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設置不同的遷移速度,得到大城市主導(大城市凈遷入率最高)、中小城市主導(中小城市凈遷入率最高)、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各級別城市凈遷入率一致)情形下的三種不同預測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城市化發展模式下預測得到的2020年城市等級結構
注: 根據各級別城市的凈遷入率數據,經過反復調試,在取值允許的范圍內,大城市主導情形下參數設置為η1=0.5,η2=3,η3=0.5;中小城市主導情形下參數設置為η1=0.5,η2=0.5,η3=3。表中第Ⅰ類城市為特大和超大城市,第Ⅱ類城市為大城市,第Ⅲ類城市為中等城市,第Ⅳ類城市為小城市。
從表3可看出,不管依據何種城市化發展模式,預測得到的中國地級層面城市等級結構都較為類似,并沒有產生特別大的變動。與自組織發展情景相比,其他三種情形的特(超)大城市所占規模比例略微有所下降,但較之2010年還是升高的,反映了自組織發展趨勢的不可逆轉。此外,大城市往特大城市遞補的速度遠低于中小城市往大城市晉升的速度。
在這三種不同的城市化情景中,大城市主導情景與自組織發展情景的各級別城市規模比例較為接近(其特大城市規模比例低于后者,大城市規模比例高于后者)。這反映出在這三種情景中,大城市為主導是最接近于城市體系演化自然規律的,經濟集聚效應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其他兩種情景則主要受到政策的干預。將中小城市主導情景與其他情景相比,可以明顯看出該種情景下中小城市往上晉升的速度較快(有42個中等城市升級為大城市),導致大城市的數目較多(224個),且所占規模比例較大(61.24%)。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也是相對而言的,在該情形下各級別城市發展的速度(如中等城市升級為大城市的數量,以及大城市升級為特大城市的數量)介乎大城市主導情景和中小城市主導情景之間。
3. 不同戶籍改革力度下的預測結果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城區人口50萬-100萬的城市落戶限制,合理放開城區人口100萬-300萬的大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城區人口300萬-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即根據各城市人口規模和綜合承載能力的不同實際情況,實施差別化落戶政策。根據中國實際國情和國家政策導向,本研究設計了以下幾種城市化情景:全國城市的戶籍均放開、只放開中小城市戶籍、只限制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落戶。
對不同戶籍改革力度下的各級別地級市初始公共服務水平上分別乘以不同的落戶難易系數*在全國戶籍均放開的情形下,可將所有城市的落戶系數均設為1;只放開中小城市戶籍的情形下,令大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的落戶系數為0.5,中小城市的落戶系數為1;只限制特大和超大城市落戶的情形下,令中小城市、大城市的落戶系數都為1,特大、超大城市落戶系數為0.5。,使得戶籍制度與公共服務水平掛鉤。從2010年地級單元的實際數據出發,預測得到不同情景下2020年的城市等級結構,如表4所示。從中可看出:所有城市的戶籍全部放開時,特大和超大城市規模比例較高,即人口還是主要往級別最高的城市集聚,大城市則相對占比較低;只放開中小城市戶籍時,中小城市發展最為迅速,往大城市晉升的速度較快(有43個城市),使得大城市的數量和規模比例均較高;只限制特大超大城市戶籍時,其特(超)大城市規模比例和中小城市發展速度都介乎前兩種情景之間,大城市發展速度相對較快,使得大城市升級為特大城市的數量最多(14個)。

表4 不同戶籍松緊程度下預測得到的2020年城市等級結構
從表4來看,戶籍松緊程度差異對城市等級結構有一定影響,為具體區分三種不同戶籍松緊程度對城市體系演化的不同影響,本研究分析了這三種不同情形下各地級單元的人口增長情況。通過觀察可以發現:當戶籍制度全面放開時,所有城市的人口遷移均不受限制,與其他兩種情形相比,特大、超大城市在2010-2020年間的人口增長速度是最快的,這是由于中國人口遷移的自然規律是往最高級別的城市聚集;當只限制特大、超大城市落戶時,此時大城市的人口增長速度快于其他兩種情形下的相應值,這是由于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相比,存在城市規模效應,人口集聚能力相對較強;當只放開中小城市落戶時,與其他兩種情形相比,由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人口遷移都受到限制,此時中小城市的人口增長速度是最快的。
五、 總結與討論
本文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城市體系模型,從人口遷移的視角對模型進行改進,以解釋城市間人口遷移是如何影響城市等級體系演化的。根據該理論模型,用2000年全國地級單元的實際數據來模擬2010年地級單元城市規模變化。無論從各地級單元模擬人口數,城市間人口遷移模擬值,還是模擬所得的城市規模等級結構和城市空間格局等方面,模擬結果均較為接近實際情況,模型擬合精度較高。因此模型通過了實證檢驗,可以用于城市體系演化預測。
根據目前中國實際國情和國家政策導向,在理論模型中輸入2010年全國地級單元的實際數據,在三種大的城市化情景下預測2010-2020年間中國城市體系演化情況,結果如下。
(1)按自組織發展趨勢,2010-2020年間,地級層面城市規模等級結構和城市空間格局都相對保持穩定,大部分城市規模有所增加但等級保持不變;其中超大和特大城市的數量和規模增加都是最明顯的,地級市層面的城市體系演化以100萬人以上規模的大城市為主導;中小城市發展迅速,規模較小且吸引力不足的城市在未來有可能會消失掉。
(2)大城市為主導的情景下,特大城市規模比例最高,最為接近城市體系演化自然規律;中小城市發展迅速,往大城市遞補的速度較快,這一現象在以中小城市為主導的情景中最為突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情景下的預測結果則介乎其他兩種情景之間。
(3)不管戶籍制度如何變化,人口還是傾向于往級別高的城市集聚,而對這三種情形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戶籍全面放開情形與其他兩種情形相比,特大、超大城市人口增長最快;只限制特(超)大城市落戶時大城市人口增長最快;只放開中小城市落戶時中小城市人口增長最快。
(4)引入異質性地理空間和城市等級體系構建后,模型的模擬和預測結果與新經濟地理學“核心—邊緣”模型的結果基本一致:在不斷增強的集聚力和循環累積因果效應的影響下,具有先發優勢的地區(也就是原先人口規模較大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由于具備集聚經濟效應,會吸納越來越多的人口,核心地區逐漸得以強化,而城市周圍的鄉村地區和邊緣地區的小城市會出現人口銳減。
已有研究中對全國人口空間格局及城市規模等級體系的整體性預測較少,本研究預測結果與顧朝林[24]和鄧羽等[7]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在顧朝林預測的2020年中國城市體系中,2010-2020年間1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規模比例增幅是最大的;鄧羽等預測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為61%,其中北京、天津、江蘇、上海、浙江及廣東為凈遷入主導型人口快速變化區,河南、安徽、重慶、湖北為凈遷出主導型人口快速變化區,大部分西北和西南省份屬于人口平穩區(人口密度穩中有減),并且證明了通過基期人口數據和平均自然增長率進行人口外推具有可信性。此外,本研究預測所得的集中型城市化未來發展趨勢(以1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為主導)也與以下幾個研究報告的主要觀點相契合: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認為,是規模經濟規律促進了人口和經濟密度的日益集中,集中發展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25]。2008年麥肯錫研究報告《Preparing for China’s Urban Billion》指出集中式增長是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最優方案,以特大、超大城市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最為經濟,在規模效應的作用下將實現人均GDP最高、人均能耗最低、土地集約化利用、大眾交通更高效、污染控制更有力、促進知識外溢和創新發展等目標[26];順應這一城市體系演化自然規律,目前中國城市體系空間格局應該走集中型城市化發展道路,依托各大城市群,積極培育區域經濟增長極,形成以特大城市為增長極、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城市群結構。王小魯指出,更多地發展城市規模達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將會大大提高經濟效益,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中國未來新增城市人口仍將主要進入超過 100 萬人的大城市;大城市發展并不意味著只單純地擴大現有大城市規模,更主要的是要加快中小城市發展,以形成更多新的大城市[27]。
本文只選取了不同城市化發展模式和不同戶籍改革力度這兩種大的城市化情景來預測未來城市體系演化,根據當前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最新時代背景,還可以加強和細化情景分析與構造,在人口增長速度不同的情況下,對不同城鎮化水平(如老齡化日趨發展使得農村可轉移勞動力減少)、不同公共服務發展水平(如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推進帶來的各城市公共服務水平變化)、不同交通運輸條件(如高鐵大規模建設運營帶來的交通基礎設施條件改善)、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如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等情景下的未來城市體系演化展開更加深入的預測研究,采用多方案的預測參數,提升模型體系的預測與決策支持能力,并基于模擬結果加強政策建議研究。
[1] 克里斯塔勒. 德國南部中心地原理[M]. 常正文,王興中,等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19-157.
[2] HENDERSON J V.The types and size of cit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64(4): 640-656.
[3] KRUGMAN P. On the number and location of citie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3, 37(2): 293-298.
[4] BLACK D, HENDERSON V. 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2): 252-284.
[5] FUJITA M, KRUGMAN P, MORI T.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2): 209-251.
[6] FUJITA M, KRUGMAN P R, VENABLES A J.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119-131.
[7] 鄧羽, 劉盛和, 蔡建明, 等. 中國省際人口空間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與實證[J]. 地理學報, 2014(10): 1473-1486.
[8] FAN C C. Modeling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1985-2000[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5, 46(3): 165-184.
[9] JOHNSON K M, VOSS P R, HAMMER R B, et al.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in age-specific net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Demography, 2005, 42(4): 791-812.
[10] SHEN J. Changing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1985-2000[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2, 18(3): 384-402.
[11] 丁金宏, 劉振宇, 程丹明, 等. 中國人口遷移的區域差異與流場特征[J]. 地理學報, 2005(1): 106-114.
[12] 李薇. 我國人口省際遷移空間模式分析[J]. 人口研究, 2008(4): 86-96.
[13] 劉望保, 汪麗娜, 陳忠暖. 中國省際人口遷移流場及其空間差異[J]. 經濟地理, 2012(2): 8-13.
[14] 王桂新, 潘澤瀚, 陸燕秋. 中國省際人口遷移區域模式變化及其影響因素——基于2000和2010 年人口普查資料的分析[J]. 中國人口科學, 2012 (5): 2-13.
[15] 王國霞, 秦志琴, 程麗琳. 20 世紀末中國遷移人口空間分布格局[J]. 地理科學, 2012(3):273-281.
[16] MANSURY Y, GULYAS L. The emergence of Zipf’s Law in a system of cities: an agent-based simulation approach[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07, 31(7): 2438-2460.
[17] KRUGMAN P R.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89-108.
[18] STELDER D. Where do cities form?: a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model for Europe[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05, 45(4): 657-679.
[19] 葛瑩,朱國慧,吳野.地理環境下的克魯格曼式城市體系模擬分析[J].地理科學,2013(3):273-281.
[20] PFLüGER M, SüDEKUM J. Integration, agglomeration and welfare[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8, 63(2): 544-566.
[21] 梁琦, 陳強遠, 王如玉. 戶籍改革、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層級體系優化[J]. 中國社會科學, 2013 (12): 36-59.
[22] ROGERS A. Migration patterns and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1979, 9(4):275-310.
[23]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聯合課題組. 中國:推進高效、包容、可持續的城鎮化[J].管理世界,2014(4):5-41.
[24] 顧朝林. 2020年國家城市體系展望[J]. 未來與發展,2009(6):2-7.
[25] WORLD BANK.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R].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26] WOETZEL J, MENDONCA L, DEVAN J, et al. Preparing for China’s urban billion [R].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port, 2009.
[27] 王小魯. 中國城市化路徑與城市規模的經濟學分析[J]. 經濟研究, 2010(10): 20-32.
[責任編輯 方 志]
An Exploration into China’s Urban System Evolution Forecast Based on Intercity Migration
LAO Xin1, SHEN Tiyan2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2.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ssence of China’s urbanization—migration network,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study combining internal migration and urban system,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China’s urban system evolution, and expand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to multiple regions by introducing into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us constructing a urban system model based on intercity migration with explicit spatial reference and migration mechanism. The simulated values of this model are close to the actual situations with a high fitting accuracy, indicating that the model is feasible to predict the urban system evolution after passing empirical tests. According to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and policy direction, this model is used to predi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system based on intercity migration under 3 different scenarios, which regards the whole urban system as a network connected by intercity migration, thus providing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reasonable guidance of intercity migration, public service improvement and urban system planning.
migration network; urban system evolution;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2016-03-24;
2016-07-25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基于人口遷移網絡的城市人口預測及城市化格局優化研究”(16BJL124)。
勞昕,經濟學博士,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沈體雁,理學博士,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C922
A
1000-4149(2016)06-0035-13
10.3969/j.issn.1000-4149.2016.0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