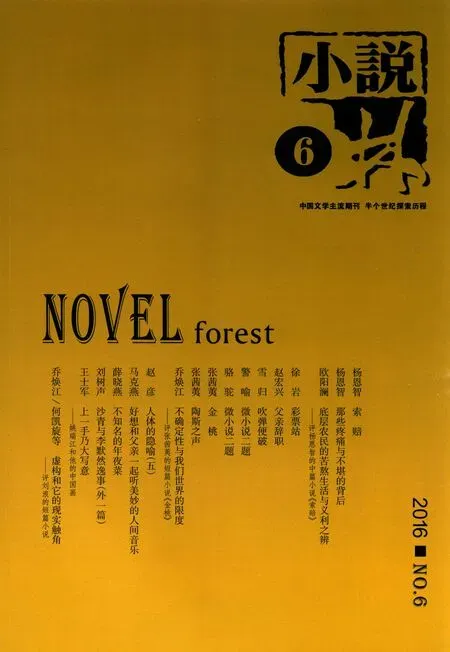微小說二題
◎警喻
微小說二題
◎警喻
子孫大事
秋天的雨下起來就沒完沒了。
工地上活計干不了,待在工棚子里的民工閑得牙干口臭,不是甩幾把撲克就是喝酒,再就是串聯胡大肚子唱段子。
其實,胡大肚子唱二人轉不用串聯,只要一杯酒下肚,必唱。
胡大肚子干別的稀松平常,唱二人轉卻板板正正。雖不是科班出身,但也在鄉里文藝宣傳隊干過幾年。胡大肚子其實肚子不大,只因為他把和他唱一副架的師妹搞成了大肚子,才有了這么個綽號。
那時候,亂搞男女關系可不是小事,胡大肚子和師妹雙雙被開除了文藝宣傳隊。師妹的母親找到胡大肚子讓他把姑娘娶了,才知道胡大肚子都有老婆孩了。母親覺著沒臉見人,便領著師妹悄無聲息地搬走了,從此音信全無。
那時候不像現在,沒有手機,搖把子電話也只有大隊才有。胡大肚子也曾到師妹的屯子打聽過,可沒人知道她搬到了哪里。
胡大肚子坐在板鋪上,一手端著一盔子豆腐湯,一手端著一茶缸子散白,喝口湯,喝口酒,喝喝咧咧地唱起來:
張三姐我正在昏迷之處啊,忽聽得有人管我叫娘。
睜開了二目昏花的眼,
看見了有一個小孩跪在身旁……
胡大肚子唱著唱著就落下淚來,工友們知道他又想起了小師妹,想起了他那沒見過面的孩子。
齊瓦匠湊過去拍了拍胡大肚子的肩頭問,那孩子今年有二十多歲了吧?
胡大肚子居然像孩子似的哇地一下哭出聲來。
齊瓦匠說,咋還整出聲來了,我也沒說啥呀?
李木匠白了他一眼,你還沒說啥?這都趕上拿瓦刀捅他心窩子了!
趙老蔫說,也是,兒女連心啊!
胡大肚子尿尿嘰嘰地說,也不知那孩子來沒來世上。
李木匠說,世上沒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撲奔來了,她不會把孩子打掉的。
胡大肚子抓住李木匠的胳膊,你說我那孩子在哪?這些年他咋沒來找我?他過得咋樣啊?
正在擺弄手機的三小子說,胡叔,這還不簡單,把你師妹的名字告訴我,我刷個朋友圈,讓朋友圈轉朋友圈,朋友圈再轉朋友圈,興許能找著。
胡大肚子急忙說,別,千萬別。師妹沒讓孩子找我,肯定有她的道理,不能再傷她了。再說,我現在家里的小孫子都十多歲了,他要知道他的爺爺當年有這風流事兒,在同學面前咋抬頭?
李木匠說,是啊,兒孫是大事兒。
齊瓦匠說,要不是為孫子,我才不出來打工呢,還不是為了掙倆錢兒,供孫子上個好學校,將來有點出息!
三小子撂下手機說,等我兒子長大了,我想讓他當城管,想打誰打誰!
齊瓦匠說,你可拉倒吧,小心讓人家把他的皮扒了!等我兒子長大了就讓他當醫生,天天收紅包,我天天在家數錢。
三小子嘁了聲,說大夫現在也不收紅包了,是信封。
齊瓦匠說,信封咋的,裝錢多!
李木匠說,我想讓我姑娘當老師,在課堂上不講重點,放學后補課,掙孩子錢容易。
趙老蔫喝了口酒,說,你們說得不貼鋪襯,我最大愿望,就是讓我兒子當村長,現在村長多肥呀!
李木匠說,是啊,我們村上有三百多畝機動地,所有承包費都揣他腰包里了。
趙老蔫罵道,媽的,就連直補款都打在他的折子上。
三小子嘆了口氣,好端端的土地,他說占就占,想在哪蓋房就在哪蓋。
胡大肚子憤憤不平,狗日的,想睡誰老婆就睡誰老婆……
工棚里一下子靜下來,誰都不再說話,各自倒在板鋪上,眼望棚頂,淅淅瀝瀝的落雨敲打著棚板,砸在心上……
高缸子
高缸子是老屯的一個哥們兒。
高缸子不叫高缸子,叫高剛。之所以叫高缸子,是因為他喝酒有節制,一般場合的酒他不喝。即便喝也從不多喝,一頓一缸子。后來,人們就叫他高缸子。
說這話,是兩年前的事兒。
那時的高缸子在老屯也算是個人物,是個可以和村長平起平坐的人物。村長娶了張家大女兒,高缸子就把張家二女兒迎進了家門,兩個人成了連襟;村長蓋房子,他也蓋;村長買車,他也買;村長去洗桑拿,他也洗。
每次我回老屯,村長都陪我,高缸子也陪我。說實話,我在縣城一個不起眼兒的科局任職,每次回老屯,都被高看一眼,也許在他們眼中,我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官。
有一次我回老屯參加一個遠房親屬女兒的婚禮,酒到興處,高缸子問我,再掂對點啥菜?我說夠了,這么多菜吃不了。
高缸子說沒事,我在這坐著,讓廚房的整倆菜還不屁顛屁顛的?
話剛說到這兒,村長干咳了聲。
村長瞅瞅我,自嘲地說,他就這德行。
高缸子不依不饒,你說我啥德行?
村長就是村長,當著我的面不好跟他計較。舉起酒杯笑著對我說,來,喝!
高缸子立起身,往后廚揮揮手,不一會兒,便有個五短身材的廚子端上兩盤菜,一盤大腸頭,一盤拼肘花。
廚子放下菜點頭哈腰地對高缸子說,慢慢喝,別著急,缺啥吱聲。
高缸子又揮揮手,便把那廚子又揮到了后廚。
后來出了一回事,高缸子整個人就變了。
高缸子出事的時候,是去年夏日的一個午后,我剛要上班,高缸子打電話給我,說他出事了,讓我去一趟!我問在哪?他說大西門,快來吧!我問咋的啦?他沒說就撂了電話,我的心跟著就懸了起來。
這廝打小就淘,隔三差五就弄出點事來,這下又闖下了啥禍?
剛到大西門,遠遠看見高缸子被帶上了警車。
警車里的高缸子肯定是看到了我,“貓抓”似的敲著車窗。
我奔跑了幾步,警車呼嘯著從我眼前絕塵而去。
正在不知所措,村長和一交警走過來,我問他怎么啦?
村長說,嘚瑟,酒駕。
旁邊的交警說,哎,是醉駕!
我一看交警是我同事的兒子,便湊過去問,大侄子能不能通融通融?
交警說,通融?叔,除非扒了我這身皮!
我急忙賠著笑,有那么嚴重嗎?
交警說,這小子,狂著呢!說他是地主,拿錢能買我們的命!還打了我們隊長一拳。
我感到事態的嚴重性。
果然,高缸子不但被罰了款還拘留十五天。我曾去拘留所兩次,一次是給他送了點吃的,一次是幫他交了罰款。這期間,我也找過交警隊長和拘留所長。還算給面子,高缸子總算提前三天被放了出來。
高缸子尿嘰嘰地對我說,罰款行,多少都行,咱有錢不在乎,關鍵是扣了我的駕照,等于砍了我的腿,往后我還咋走?
我問他,開車,咋喝那么多酒?
他說,別提了,那天我托我連襟兒找人辦事兒,我那狗卵子連襟兒不喝,把我推到前線上去了,人家為我辦事,我咋好意思不喝,就多貪了兩杯。也怪交警賊性,埋伏在酒店旁邊,我上車剛起步,就把我按住了。
為了去晦氣,我領他洗了個澡,又去酒店喝了點酒,算是給他壓壓驚。那天,高缸子只喝了半缸酒,說啥也不喝了,著忙回家,說想老婆了。
從那兒以后,我再也沒見到高缸子。
據說,那天,高缸子回到家,看到了他不該看到的,讓他永遠也抬不起頭的事情。
據說,高缸子用鎬把差點沒把村長的腿打斷了。
后來,他和老婆也離了婚。
據說,現在的高缸子逢酒必喝,逢喝必多。
我一直很自責,假如高缸子不是提前三天被放出來,事情恐怕就不會如此糟糕。
警喻,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會員,東北小小說沙龍副主席。曾在《北方文學》《山東文學》《章回小說》《小說林》《海燕》《延安文學》《百花園》《歲月》《短篇小說》《文學報》《遼河》《微型小說月報》《中華傳奇》等報刊發表中短篇、小小說近三百篇。有數十篇作品被《小說選刊》《小小說選刊》《微型小說選刊》及各類年選本選載,有數十篇作品獲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