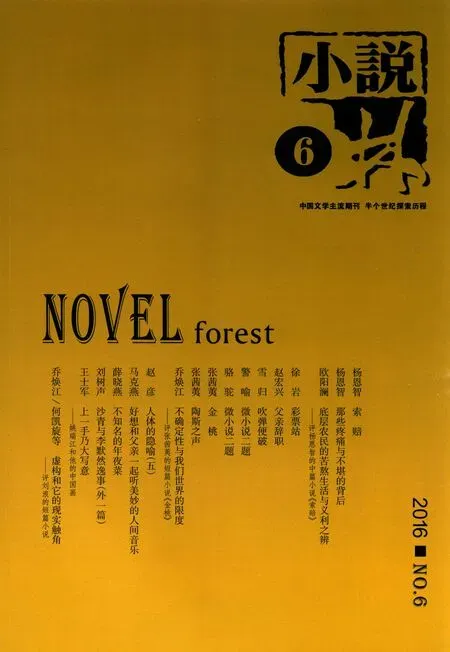好想和父親一起聽美妙的人間音樂
◎馬克燕
好想和父親一起聽美妙的人間音樂
◎馬克燕
有一種情感,總希望珍藏于心,在歲月流淌中獨自回味。因為,我始終無法確定文字表達的情感是否會因能力所及而失之本身的自然、純粹與源遠,進而被固化在文字所限的空間。然而,這么多年,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卻很難在每年的那一天回到家鄉去祭拜父親。歲月流逝,不安與缺憾也隨之一起生長,也許文字表達是唯一可以彌補那份缺憾的方式。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九年了,我以為我會經常夢見他,可是,父親卻極少出現在我的夢中。倒是母親常常夢到他,且一說到父親,就要掉淚,每每這時,我總是把話題岔開,帶著母親迅速逃離漸要彌散開來的悲傷。
父親生性樂觀、隨和、熱情、豁達。
在我兒時的世界里,父親是一抹暖色,他能讓我無憂無慮的天性得以釋放,也能讓承載生活負重的小舟平穩前行。小時候,我很懼怕母親,常常因為各種“不長記性”的錯誤受到母親嚴厲的責罰。而父親則很少動怒,對于我的錯誤,他總是用“喇喇忽忽”(馬馬虎虎)“以后注意”之類的話概括了之,為此,母親總是生氣地對父親說“你就慣著她吧”。有了父親的“慣著”,我的童年生活很多時候可以過得“肆無忌憚”“忘乎所以”,除了時不時被母親逮住機會一頓重罰之外,剩下的都是瘋玩的快樂。好像我身上快樂的基因更多的是來自父親的遺傳。父親對我這種“記吃不記打”的憨憨性格有幾分無奈,但更多的似乎是樂享和喜愛,因為他時常會笑著評價這個不長心眼的女兒“傻呵呵”的。雖說“傻”字聽著不太順耳,但是父親臉上流露出的疼愛還是讓我覺得十分受用,于是我便會以“傻呵呵”的狀態繼續著我的快樂并將這份快樂傳遞給父親。有母親嚴厲性格的映襯,父親的“親”和“好”在孩童時代便格外鮮明。
如果說,父親對我的愛是天然的血緣關系所致,那么,父親之于母親的愛則是感恩情懷下的尊重與豁達。父親大學畢業,母親則是解放后夜校掃的盲,兩人之間的文化差距很大。但是,父親從沒有輕視過母親,他總夸母親能干,夸母親做的飯好吃,無人能敵。奶奶過世早,母親嫁給父親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承擔起了一大家子的生活重任。長嫂如母,父親的三個弟弟幾乎都是靠母親拉扯大,父親深知母親付出的不易。我出生得晚,沒有經歷過他們早期的婚姻歲月,在我成長的過程中,覺得父親總是非常謙讓母親,母親情緒不好時,父親總是笑著化解,很少和她發生沖突。“你媽脾氣不好,你就少惹她生氣”,每當我被母親訓斥懲罰而去父親那訴苦時,父親總是這樣對我說。
父親沒有傳說中的所謂東北男人的懶惰,除了重體力活,父親還幫助母親分擔了大量家務。母親單位離家遠,每天早出晚歸,于是,從周一到周六的早飯、午飯都是父親來掌勺。那時,我覺得父親很能干,和面發面搟皮包餃子,樣樣會。父親直接用菜刀削土豆皮,技術嫻熟,不僅如此,父親還會熟練地用菜刀均勻、快速地掰開不規則的土豆塊,據說,這樣做出來的土豆好吃。小時候,我常常在廚房看父親干活,覺得十分有趣。但是,印象中,父親從未做出過一道讓我們全家人認為好吃的菜。父親做的發面玉米餅子常常發酸難以下咽(不知為什么總是堿放得不夠);父親炒的土豆白菜除了干咸啥味都沒有(我和哥哥抗議時他就說味精放得少)。很長一段時間,我和哥哥就是靠難吃的早餐成長的。周末母親忙于家務時,父親少不了也要幫忙,比如擦地,往往擦到一半,就能聽到母親抱怨:“王婆畫眉,東一下西一下的。”此時看過去,父親擦地的動作確實潦草粗獷,質量不高。比如買菜,似乎總是拎回來一些品相較差、不太入眼的次品,為此少不了遭受母親的一頓責備。但是父親并不會因為大家的“不滿”而推卸責任,父親把這份責任一部分承擔到母親退休,一部分承擔到病倒。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父親病重時卻向母親道出了心中的一分內疚。那次,在醫院里他們聊到了往事。當年下班因擠不上公交車,身材弱小的母親時常要抱著襁褓中的我步行十多里路才能到家,想到母親的這份辛苦,父親感慨萬千,同時深深懊悔當時為什么沒想到去接母親一下,他說,自己太大意了,想得太少了,太不周到了。那份來自內心深處的自責深深撞擊著我,在父親生命的最后時刻,他似乎一直在掃描自己的一生,他希望無愧于家人、無愧于朋友,無愧于一生。
父親的寬厚隨和也是深得母親娘家人贊許的,不管娘家人誰來,他都熱情相待。我的老姨(東北話的小姨)身有殘疾,家住農村,是母親最大的牽掛,除了在生活上盡可能接濟他們,父親總是經常寫信代母親問候他們,而“某某縣某某公社某某大隊第幾生產小隊”則是我兒時最熟悉的信封了。作為妹夫、姐夫、姨夫、姑父,父親給母親娘家人的印象就是“性格好!人好!”父親去世后,母親多次和我提起,姥姥在世時,父親工資一發下來,就會及時給姥姥匯去,從未耽擱過。父親對母親的這種好應該也是母親此生最感念的。
父親的隨和、寬厚不僅體現在家中,也體現在與外人的交往中。“人好”、“正直”是學校師生對他最多的評價。從小到大,父親都在以自身的言行告誡我們要品行端正、為人正派。同時,父親也告訴我們,為人做事要把握分寸,有禮有節,既要堅持原則,也不能太死性,一條道走到黑。做任何事情、看待任何問題都不要走極端,世間萬事萬物充滿辯證法,要學會辯證地看待問題。他特別推崇傳統文化的中庸之道。特別是退休以后,每每回家探親,他都希望就此多些交流。“不要以為中庸是沒有原則,沒有立場,是人性的圓滑,是和稀泥,做老好人,中庸是一種非常值得研究和學習的態度和方法”。他說,“不偏謂之中,不易謂之庸”,“這里面有很深的學問和內涵”,他希望我們晚輩能夠從中吸取更多文化精髓、思維方式、處事方法,豐富和滋養生命。父親說,他特別感謝他的爺爺從小告誡了他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他的人格形成與他爺爺灌輸給他許多傳統文化有著很大的關系,這些讓他受益終身。
父親一生堅守本分、謹慎自律、淡泊名利、知足常樂。
用母親的話說,父親什么好事都趕不上,吃苦受累的事卻一樣都不落。漲工資也好、分房子也罷,總是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吃虧不少。但是父親卻處之泰然,從普通教師到一名高校領導,從與人合住一套房子到兩居室再到三居室,生活一天天改善,父親覺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父親后來住的房子無論是環境還是樓層都很不理想,盡管后來還是有調房的機會,但是,父親嫌麻煩,也就放棄了。他說,他的房子陽光充足,且只有他和母親住,已經相當不錯了。父親退休后,被學校返聘擔任督導,只發不到一千元錢,當時我們都說沒必要去,錢太少了,還挺辛苦,可是父親樂呵呵地說,連工資帶返聘的錢加在一起三千多呢,足夠花了。父親七十歲以后,總對我們說,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經很知足了。
父親一生從事教育,熱愛教育,從大學畢業分配到高校,就不曾離開過校園,直至離開這個世界。
父親喜歡早睡早起,即使是退休后,也是早晨四五點鐘起來看書寫材料,母親常常數落他,退休比人家正式上班的都忙。
學校是社會的一面鏡子,父親退休后,高校官本位、行政化、官僚主義、機關作風似乎越來越盛行。回家探親,父親對我不無憂慮地說,學校的教學質量在下降,現任校長根本不抓教學,整天關在辦公室里,不僅如此,這位校長上任后還把所在的樓層打上了隔斷,同層的教職員工要是找這位校長還要從三層下到一層繞到另外一個門才能上去見他。如此工作作風、行事風格,父親很難理解,盡管看到問題越積越多,教職員工意見越來越大,但卻無計可施。
父親患病時,高校合并風盛行,父親所在的高校也與另外一所學校合并,校長也重新任命。合并后的學校會怎樣,新來的校長是否能讓局面改觀,教職員工們都充滿期待。借此機會,病重的父親給剛剛上任的新校長寫了一封長長的建議書,他希望他盡職了一生的這所高校能夠重新煥發生機,能夠在教改的道路上有所突破,能夠為國家培養更多的棟梁之才。
為了能給學校教學改進提供更有實際參考價值的建議,病重的父親不知從哪獲得的信息,讓在北京工作的我幫助他買一套剛剛出版的《名師頌》,為此,我還專門跑到高教出版社買回了這部上下兩卷厚厚的圖書。此時的父親已經沒有能力自己閱讀,讓我選擇一些篇目讀給他聽。盡管我不希望他再為學校的事情操心,盡管他已經沒有能力再為學校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也深深感受到任何與教育相關的話題都會讓他暫時減輕一些痛苦,能讓他在病痛之中獲得一絲慰藉。教育工作承載著父親一生的追求和夢想,是他一生的割舍不掉的情結。
父親病重時,體重快速下降,我無法相信這就是平時說起話來中氣十足、走起路來大步流星的父親。
記得小學時,父親曾興致勃勃地教我朗讀高爾基的《海燕》。
“在蒼茫的大海上,狂風卷集著烏云。在烏云和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在高傲地飛翔……”
父親聲情并茂,充滿激情,那一刻,我覺得父親好高大,好偉岸。而可惡的疾病卻讓我再也看不到父親健壯的身影。
父親說他不怕死,但是他害怕拖累家人。住院期間,哥哥每天都要跑前跑后精心照料,被病痛折磨的父親總說:放棄治療吧,這樣我解脫了,你們也解放了。他不愿意兒女為他付出太多的時間和精力。
病重期間,父親以強大的毅力與疼痛進行抗爭。都說,病人的脾氣很容易暴躁,但是,父親卻強力克制著自己。記得有一次,他和護士大聲嚷了一句,過后,他很歉疚地對護士說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父親感恩于每一個照料他的人,包括家人,也包括醫務工作者。
父親特別喜歡聽中國的古典名曲,特別是《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高山流水》《雨打芭蕉》《步步高》等。年少時,很難理解父親為什么如此沉醉于這些曲目,如今,當這些樂曲響起時,竟能在心中蕩起陣陣漣漪,此時,好希望和父親一起靜靜地欣賞著這些美妙的人間音樂。
逝去的不一定失去,遠離的也許并未走遠。歲月越是流逝,越是能神奇地感受到血脈基因在身體靈魂內的流動,越是能清晰地看清自己來自何處。
馬克燕,女。1985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現就職于北京電視臺研究發展部。主要從事媒介環境、媒介信息、媒體發展研究分析工作。近年來,負責完成了多個國家廣電總局及市廣電局層面的課題研究工作,在《中國廣播影視》《中國廣播電視學刊》等重點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十余篇研究文章,也曾發表過小說、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