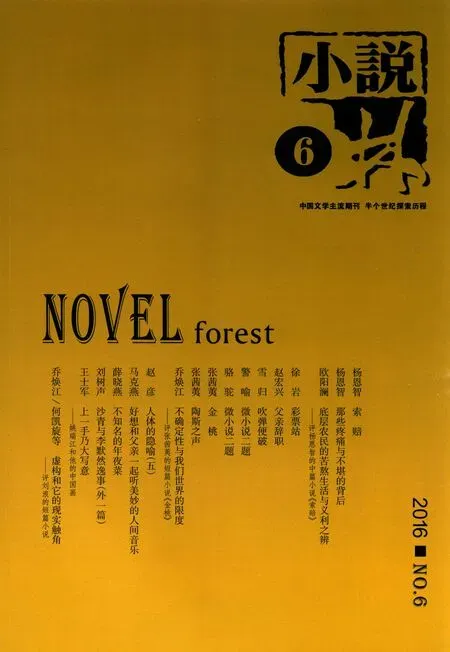不確定性與我們世界的限度
——評(píng)張茜荑的短篇小說(shuō)︽金桃︾
◎喬煥江
(評(píng)論)
不確定性與我們世界的限度
——評(píng)張茜荑的短篇小說(shuō)︽金桃︾
◎喬煥江
現(xiàn)實(shí)是否經(jīng)得起信任?或者,哪一種現(xiàn)實(shí)可以信任?這對(duì)小說(shuō)來(lái)說(shuō),永遠(yuǎn)是一個(gè)不大不小的問(wèn)題。納博科夫干脆就選擇了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不信任:“人們離現(xiàn)實(shí)永遠(yuǎn)都不夠近,因?yàn)楝F(xiàn)實(shí)是認(rèn)識(shí)步驟、水平的無(wú)限延續(xù),是抽屜的假底板,永不可得。人們對(duì)一個(gè)事物可以知道得越來(lái)越多,但永遠(yuǎn)無(wú)法知道這個(gè)事物的一切。”于是,他的小說(shuō)寫作不得不寄望于語(yǔ)言構(gòu)造的重重鏡像,寄望于結(jié)構(gòu)迷宮的回環(huán)往復(fù)。現(xiàn)實(shí),或者說(shuō)結(jié)果,在他的筆下一次次被延宕,剩下的似乎只有他一個(gè)人捧著一縷“微暗的火”,在繁復(fù)無(wú)休的互文空間里翻檢著意義的碎片。
張茜荑的《金桃》,同樣是一個(gè)關(guān)于不確定性的小說(shuō)。然而與后現(xiàn)代寫作中過(guò)度迷戀語(yǔ)言拆解的那種小說(shuō)相比,《金桃》顯然并不意在通過(guò)語(yǔ)言的不可靠展示意義的空無(wú),毋寧說(shuō),它不過(guò)是在提示我們所熟知的每一個(gè)世界的限度,每一種生存意義的限度,以及所生存的每一個(gè)時(shí)空的過(guò)程性,而他選擇的方式,則是講述一個(gè)具有開(kāi)放性的故事。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gè)能夠被讀者輕松把握的東方式故事,總體上并非破碎的,反倒是具有很好的可讀性。
金桃從未知中來(lái),又消失于未知,像是一個(gè)問(wèn)號(hào),出現(xiàn)在我們世界的開(kāi)端和結(jié)尾。“我們的世界”,在小說(shuō)里顯然是“我們”幾個(gè)廣告公司合伙人的世界。這個(gè)世界人們并不陌生,甚至早已習(xí)以為常。“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lái),舍我其誰(shuí),唯我獨(dú)尊。”“我們”的世界自然是從“決定下海”的那一刻開(kāi)始。然而,對(duì)于這個(gè)以富為榮的世界來(lái)說(shuō),“我們”從何而來(lái)似乎早已沒(méi)有什么意義,所謂抱負(fù)和雄心,也無(wú)非給自我典當(dāng)穿上冠冕堂皇的外衣。當(dāng)“我們”正在為實(shí)現(xiàn)這個(gè)世界的原則而絞盡腦汁的時(shí)候,金桃出現(xiàn)了。她顯然缺少這個(gè)世界的身份,她之所以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緣于一個(gè)不凡身世遠(yuǎn)早于其祖父母降生的般般的引薦——“她的身份證行李都被偷了”。實(shí)際上,“我們”這個(gè)世界看似鐵板一塊,卻遠(yuǎn)不是嚴(yán)絲合縫,或者說(shuō),這個(gè)世界需要的從來(lái)就不是真正的理由,它只需要自己所設(shè)定需要的。金桃由此進(jìn)入故事,“沒(méi)有敲門,也許敲門了,但是我們沒(méi)有聽(tīng)到”,金桃到底年齡幾何……但這些誰(shuí)又真正在意?——當(dāng)“我們正聲嘶力竭得面紅耳赤”,怕是沒(méi)人還會(huì)去想世界從何而來(lái),向哪里去了吧。
但這個(gè)世界畢竟多了個(gè)金桃,“我們”的世界開(kāi)始出現(xiàn)微妙而奇異的變化。金桃讓“我們”開(kāi)始意識(shí)到“工作屬于生活的一部分”,她讓“我們”在“安靜中,居然聽(tīng)到從通風(fēng)窗傳來(lái)幾聲?shū)B(niǎo)鳴”。然而,這些細(xì)節(jié)與“我們”幾位先富起來(lái)的“宏大目標(biāo)”相比,顯然又是微不足道的。“我們”似乎更善于把金桃編織進(jìn)這一個(gè)世界的邏輯,鄭凡奇的話道出這個(gè)世界的真相——“沒(méi)有邏輯的逼真細(xì)節(jié),誘導(dǎo)人們對(duì)宏大虛假的相信”。洗衣機(jī)廣告的成功,并沒(méi)有讓“我們”駐足反思,反而使“我們”更加得意忘形。金桃于“我們”,似乎還只是靈感的來(lái)源,是“我們”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現(xiàn)賦予了金桃額外的價(jià)值。慶功宴上,邱益益有關(guān)形意功法言論的玄機(jī)重重,其實(shí)早已在傳說(shuō)中消耗殆盡,主角雖然是金桃,但“我們”的張狂實(shí)在是蓋過(guò)了金桃的不以為然。為國(guó)際化妝品公司策劃首發(fā)式,當(dāng)“我們”千方百計(jì)要投外國(guó)人所好,金桃倒是有意反其道而行之,她令人瞠目結(jié)舌的現(xiàn)場(chǎng)擺設(shè),讓“我們”再也無(wú)法把她當(dāng)成可有可無(wú)的人物——“金桃的出現(xiàn)和所作所為,絕非偶然”。不過(guò),金桃到底在什么意義上是“我們”的“貴人”呢?按照這個(gè)世界的邏輯,當(dāng)然,金桃?guī)汀拔覀儭睌埖搅丝蛻簦拔覀儭睂?shí)現(xiàn)了先富的夢(mèng)想,是“貴人”無(wú)可置疑。然而,金桃的不取一物不辭而別,這讓“我們”和這個(gè)世界的意義自足出現(xiàn)了危機(jī)。“我們”既無(wú)法以這個(gè)世界的邏輯把金桃收編,所謂“在這里好好干,然后在北京買房成家,將來(lái)你就是北京人了”,原來(lái)不過(guò)是我們自以為是的一廂情愿。金桃悄無(wú)聲息地離“我們”而去,讓“本來(lái)可以春風(fēng)得意如日中天的我們,卻完全高興不起來(lái)”。她的出現(xiàn)也許只是讓“我們”的夢(mèng)想早熟,讓“我們”以最快的速度明白這被欲望驅(qū)動(dòng)的所謂“夢(mèng)想”,不過(guò)是意義的虛設(shè),她傳遞給“我們”的是在這個(gè)世界之外的更多的未知,她告訴“我們”,“舍我其誰(shuí)不是我們,唯我是尊也不是我們”。
“我們”三人由此干凈利落地從下海到“上岸”,生命的限度既已出現(xiàn),作為一個(gè)過(guò)程,倒真是應(yīng)該逞意而行了。喜歡到處流浪四海為家的“我”,則懷著對(duì)未知的好奇,要去金桃的老家探個(gè)究竟。
從北京切換到漢中,小說(shuō)對(duì)場(chǎng)景的敘述反差極大。在占去半個(gè)故事的后一場(chǎng)景中,敘事節(jié)奏變得非常緩慢,大量細(xì)節(jié)的堆積,使得時(shí)間仿佛停滯下來(lái),不到一天的時(shí)間,對(duì)“我”而言似乎像另外過(guò)了一生。在漢中,有關(guān)金桃的神秘傳聞,疊加在已成傳說(shuō)的飲馬池上,平添了故事本身的詭異氣息。在人們關(guān)于這個(gè)詭異故事的講述中,金桃被演繹成一個(gè)死而不亡的幽靈,而應(yīng)對(duì)這個(gè)幽靈的辦法,就是把金桃的忌日變成儀式性的“活水節(jié)”。人們談?wù)摻鹛液退挠撵`,談?wù)擄嬹R池詭異的聲音,甚至給這一事件附加上道德的意義——作為檢驗(yàn)誠(chéng)實(shí)善良的標(biāo)準(zhǔn)。然而,正如儀式化既是對(duì)未知事實(shí)的畏懼,更是對(duì)未知的逃避和掩蓋,道德化也無(wú)非企圖自證清白的圈套。在中年男子的講述中,死于戰(zhàn)爭(zhēng)疲勞的金桃,原來(lái)也并非漢中本地人,就像她悄無(wú)聲息地出現(xiàn)在北京“我們”的世界門前,她不過(guò)在另一個(gè)歷史時(shí)刻偶然出現(xiàn)在飲馬池,偶然存在于那個(gè)特定的時(shí)空。小說(shuō)別有深味地提到了“陶斯之聲”,與其說(shuō)將有關(guān)金桃的詭異事件引向超自然的解釋,不如說(shuō)試圖還原金桃所喻示的未知世界或世界的未知。這當(dāng)然不是在講述一個(gè)穿越故事,在當(dāng)下層出不窮的穿越小說(shuō)中,我們最終能發(fā)現(xiàn)的,無(wú)非是現(xiàn)實(shí)世界之邏輯的翻版,并沒(méi)有什么別樣世界的打開(kāi)和別樣可能的隱約呈現(xiàn),但在這里,未知回到了未知,“我們”世界的限度再一次被揭示出來(lái)。不僅如此,為了讓金桃停留在未知的世界中,“我”甚至沒(méi)有逗留到活水節(jié),沒(méi)有以敘述人的親歷為讀者們驗(yàn)證這一未知的有無(wú)。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金桃都見(jiàn)過(guò)了,活水節(jié)還有什么意思呢?”但在小說(shuō)之外,讀者的窺視欲卻就此也被中斷,只留下一個(gè)不確定的時(shí)空,兀自漂浮在小說(shuō)自造的時(shí)空,像一個(gè)難以填充的空洞,讓人不得解脫。
喬煥江,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從事文藝?yán)碚摗?dāng)代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