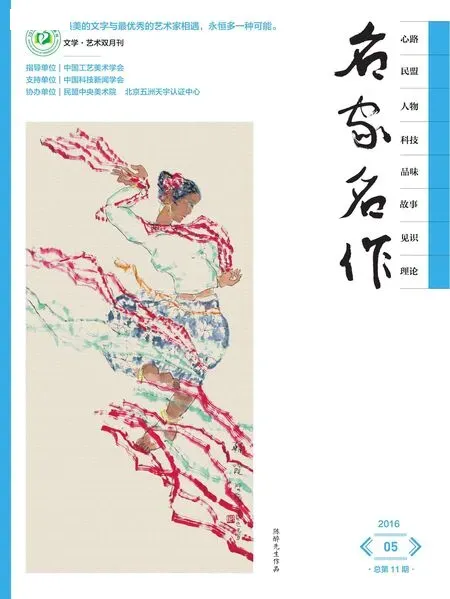從經典繪畫的立體三維化到數字媒體藝術的內空間屬性
葉淑華
從經典繪畫的立體三維化到數字媒體藝術的內空間屬性
葉淑華
2015年4月在上海新天地有一場極其特別的梵高作品展——不朽的梵高。這場展覽里沒有出現梵高的油畫實體,而是將油畫作品數碼化成為動態的視頻,利用技術通過聲、畫結合增加代入感。畫展的感染力很強,觸動了許多觀眾的心靈,而不須要太多知識儲備的要求。
與傳統架上繪畫相比,數字影像的優勢在于其儲存、傳播、觀察、修改方法的方便簡易。同時這種從圖像到編碼再到圖像的轉譯方法也為空間距離信息的傳輸提供了新的空間和方法,讓數字影像中的視覺平面信息和距離信息可以一同被記錄并最終播放出來。基于對視覺平面系統以及距離信息系統的進一步了解,我們需要探討數字影像通過自身的哪些屬性來完成對影像內部空間的記錄與再現,最終達到還原真實視覺空間的目的。
在這些“會動”的大型畫作中,它破壞了傳統的看畫方式,引起了人們最大的興趣,使觀眾沉浸在經典畫作帶來的一幕幕場景空間中。也有很多人,對畫展中圖畫的空間立體效果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是什么讓這些靜態的經典畫作“動”了起來,并且具有空間呢?
首先,這些數字化的名家名作是動態(具有連續多幀組成的時間軸)的,相對于靜態的數字影像作品(攝影、數字插畫、計算機圖形等),兩者都同時蘊含平面二維性與空間三維性,只是表現出的空間屬性的強弱、狀態不同。
例如,很多人認為攝影、錄像以及以手繪插畫都不具有空間屬性,它們在生成采集的時候已經被記錄成二維的像素點了。攝影以及錄像作品建立對真實世界進行光學記錄的基礎之上,它們記錄的是真實空間當中的一個瞬間可視畫面(或者連續瞬間可視畫面),內部深深烙印著這個畫面生成時的三維空間信息。例如,它們的鏡頭、景色、透視比例等,而這些空間信息在當代的計算機測繪以及計算機繪圖手段的幫助下,是可以被測算并再現的。展覽就是使用這些信息,對畫作重新進行了空間信息的強化和繪制。
影像的空間屬性如何體現在影像作品當中?要分析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從人類的辨別空間的機制入手。這套機制當中包含兩套不同的系統。
人的視域(Horizont)——視力所及的觀測范圍在六十度左右,在這個范圍內眼睛采集光學信息轉化為生物電,獲得時域范圍內的視覺平面,真實記錄了物體在視覺平面上的位置以及大小。這種記錄是不含距離信息的,類似于觀星圖或者觀察星空,無法得知星星和觀者之間的距離關系,我們稱它為第一套系統。
同一時間,因為人的左右眼睛所處空間位置的略微差別,導致雙眼所獲得的圖像略有不同。視覺平面信息通過眼睛接收傳達到大腦,大腦在接收到眼睛所獲得的信息后,會把這種差異化的圖像整合成為一個完整的畫面,里面包含了眼睛觀察所獲得的“夾角”信息——視差(Parallx),人的大腦利用它轉譯出物體距離人遠近的信息,也就是第二套系統。至此,人類神奇的生物構造完成了一次信息的轉譯以及空間定位,以人的視覺平面為坐標,加上距離信息,形成一個以觀察者為原點的空間坐標體系。
請假定觀眾是靜止的,屏幕上的畫面也是靜態的。由于靠近觀者的視覺夾角大、視覺空間跨度大,距離觀者遙遠的事物視覺夾角小、視覺空間跨度小,因此屏幕上存在基礎的空間信息,通過前后遮擋以及近大遠小的形式表現出來。通過對光學的運用以及數值研究,人類逐漸摸索出這種基礎空間信息的規律并把它發展成為方法以及學科——線性透視。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布魯內蔡斯基發明的線性透視系統沿用至今,歷經眾多的改良和發展,仍然是架上繪畫中最為重要的表現畫面空間信息的方法。
第一套視覺系統——視覺平面的信息在屏幕上被真實再現了,但是屏幕上呈現信息仍不完整。由于虛擬屏幕上呈現出影像是在一個平面上呈現的,從屏幕上獲得影像對于觀者的距離被壓縮在了屏幕上,因此缺失了“視差”這一項重要信息。
假定觀眾現在可以在屏幕前運動,但是屏幕上面的內容不改變。通過視差信息的獲得以及視點運動比對,觀者立刻會做出判斷:這是平面的,畫面由透視造成的空間信息都是“假的”。
為什么要通過視點運動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視差是通過“夾角”來進行計算的,這套系統在單一的靜態畫面中,由于缺乏比對,感知的能力很弱,幾乎不能構成有效的判斷。因此前面在進行分析時,將虛擬屏幕上的視差信息判斷為“缺失”而非“錯誤”的信息。這種視差信息的缺失在某種特定情況下,能夠被周圍環境填
補和引導,完整真實空間信息傳達或者成為視錯覺。位于韓國濟州島的幻覺藝術博物館,里面存放的許多作品能夠利用畫面、燈光、觀眾和角度合理掩蓋真實的“視差”信息,從而獲得十分有趣的錯覺互動藝術品。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藝術錯覺只能在一定的角度范圍內生效,而且觀眾一旦以運動的方式進行觀察,不論以何種角度,都能很輕易地看出真實的空間關系。
基于人的視覺運作系統具有以下特點:視點為坐標系統原點,包含視覺平面信息以及距離信息。一個視覺平面信息只對單一視點有效,屬于一一對應的靜態信息,特點是直觀有效。距離信息則需要通過視點運動才能被準確傳達,而且有這種信息的準確程度不容易被覺察,特點是動態和允許誤差性。
1997年上映的電影《鐵達尼號》由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進行執導,在2012年利用影像的各部分嵌入計算機圖形空間技術,完成了電影3D版的制作并上映。3D版本的上映讓許多影迷能夠獲得身臨其境的觀看感受,但也有不少人詬病這并非真正的三維空間,而是“假3D”。《鐵達尼號》制作團隊重新制作出影片對應的空間信息的確是存在主觀設計因素在其中,由于拍攝當時使用的影像記錄工具并沒有完整地記錄空間信息,因此導演以及制作團隊在原有數據的基礎上通過制造視差景深、深度重繪以及三維模型接入的手段重新繪制出空間信息以一種主觀力求貼近真實的創作。即使是這樣,數字媒體的空間屬性在影片中存在可塑造性,已經獲得充分的肯定與實踐。
在繪畫作品中有這樣的定義,“作品內部不同物體之間的距離以及觀眾與作品中物體之間的距離形成繪畫作品的空間”。這里所說的繪畫空間,是一種虛幻空間,即視覺空間。引申到數字影像當中,即為單幀或多幀影像“內部”視覺所包含的空間屬性。
在展覽中,梵高的作品《星空》(Starry Night,1889年),原來是一幅傳統的架上繪畫作品。在數字影像技術的介入下,可以為其補充加入內空間屬性,在原畫的基礎上塑造出具有三維空間感的動畫。
空間屬性按照存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數字媒體的內部空間屬性以及外部空間屬性。記錄在作品內部,不因播放介質改變而改變的空間屬性,稱之為內空間屬性,由畫面構成、深度信息、衰減、材質等內容組成。數字影像在不同播放介質和實體上,所獲得的不同的空間效果屬性,稱之為外空間屬性,通常包括光源、成像材質、實體形態、視點運動、地理環境等內容。
空間屬性中,最為重要的是深度,它是其他空間屬性的根本來源。例如,畫面大小構成、深度和衰減等。
深度信息的采集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源頭采集,一種是空間采集。所謂的源頭采集,就是現場測量記錄由劇組將現場的空間關系利用光學測距的方式記錄下來而空間采集則是通過特定方式將整個對象的空間記錄下來,或者在軟件三維空間當中生成虛擬實體,設定觀者位置,最終獲得與觀者相關的深度信息。
深度信息以距離長度為單位,但同時又是微妙而富有彈性(允許誤差以及強化重點)。每個空間都可以量化出無限個的點,意味著從視角原點出發,可以獲取無限多的深度信息。
通過源頭采集方式獲得空間信息若以數字進行記錄顯然是不合理的,這可能造成需要記錄的信息量變得極不穩定或趨向無限大。我們需要一種細膩準確、方便直觀利于傳輸的轉譯方式,很顯然我們找到了答案——貼圖深度貼圖以黑白兩色的二維點陣記錄畫面當中的空間信息,淺色距離近,深色距離遠,黑白分別表示無限遠以及貼近視角原點。這也是現行數字影像工業中,將二維圖像轉為三維圖像的最常用方式。
在3D版的電影制作中,經常可以看到兩臺攝影機被架設在幾乎相同的位置,拍攝同一個鏡頭的情況,這是獲得空間信息的最直接的記錄方法,借助模擬“視差的機制,同時把信息采集與圖像生成、傳輸以及最終播放連接在一起。這種方法非常有效,因此相關的三維成像技術在過去十年間飛速發展并開始被廣泛應用在影視行業當中。
但從本質來說,源頭采集建立在二維畫面構成采集的基礎上,與視角的關系一一對應,即一個畫面構成對應一張深度貼圖。這造成景深信息與畫面構成同樣的局限性,在畫面重新被轉譯出來之后,觀眾不可以看到其他的角度的內容。因此在轉譯階段這兩種方式都只成功了一半。傳達出富有深度信息的數字影像,只有一個視覺角度。真實的視覺環境是觀眾視點可以運動和改變的這也是主流數字影像被詬病為假三維的原因所在。
空間采集可以利用電腦生成深度信息,而且更加全面——它可以從空間維度的任意一個視點出發,獲得準確的深度信息。單純從信息采集的定義上出發,目前現行可用的方式有兩種:利用三維軟件生成空間信息或利用光衍射進行全息影像記錄。而在三維軟件制作的數字影像中,由于要采集深度信息的對象和視角都是在軟件當中虛擬出來的,因此要模擬并生成任意的深度信息都是可能的,只要配合恰當的播放介質,選擇合適的轉譯編碼形式,便能夠被轉譯和播放出來。相信在不遠的將來特別是在VR技術越來越普及的今天,相信很快將被攻克,經典藝術從畫架走入屏幕,再從屏幕真正走入立體空間中的世代,不遠矣!
(作者單位:廣州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