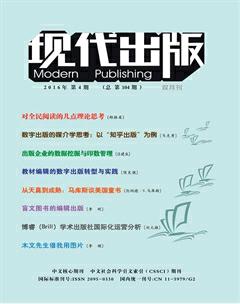三聯編輯談圖文書
圖文書出版近年來在業界頗為興盛,這也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簡稱三聯書店)當前的主要業務板塊之一。三聯書店版圖文書大多傳承了三聯書店特有的濃厚“書卷氣”和文化品位,由此打造出了許多品牌產品,與之相關的編輯出版經驗有一定代表性。
“小蔡本”散發大效應
現在通常所謂圖文書,廣義而言主要指圖文相互搭配編排出版的圖書,與純粹的繪本和文字書相區別。中國自古有“左圖右史”的傳統,古典繡像本小說戲曲、連環畫可謂早期的圖文書籍。及至晚清民國,隨著攝影、印刷技術的興起,圖文混排藝術日益受到青睞,不但《點石齋畫報》《良友》等畫報畫刊先后興起,諸多出版機構同樣紛紛涉足圖文書編輯出版活動,如三聯書店前身之一的生活書店曾出版了黃炎培的游記作品《之東》,內文附有多幅江浙名勝古跡圖版。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受改革開放影響,加之出版社擴張經營需要,三聯書店逐漸在圖文書出版方面發力。據三聯書店原總編李昕回憶,三聯書店應是大陸第一家嘗試做彩色圖文書的出版社。20世紀90年代,時任三聯書店總經理董秀玉女士發現國內的人文書中圖文書的品種很少,印量也不高。于是,她提出做圖文書,且以系列叢書的形式出現,以便形成集約優勢,產生較大的影響。“鄉土中國”是三聯書店第一套彩色圖文書系列,該系列第一本便是《楠溪江中游古村落》。這套圖文并茂、裝幀精致、彩色印刷的人文讀物,給出版界帶來了一個新的理念,給讀書界呈現了一種出版與閱讀的新形式。
三聯書店在圖文書協調文化品位與大眾需求方面,主要選擇最富有文化性、一流的大眾讀物來出版,并且多以套書形式規模化出版。1989至1991年間,三聯書店共出版“蔡志忠中國古籍漫畫系列”19種22冊,隨即又推出“蔡志忠古典幽默漫畫系列”19種,此舉便是基于上述考量。盡管當時文化界對三聯書店出版蔡志忠的圖文書存在一些非議,但事實證明,其作品一炮走紅,蔡志忠這位原來在大陸不太知名的作者,逐漸受到許多讀者認可和喜愛,此舉也被三聯人戲稱為“賣蔡”。
之后,三聯書店趁熱打鐵,接連出版了“幾米系列”、《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中國古建筑二十講》《繪畫的故事》《建筑的故事》《哲學的故事》等系列圖文書,進而在全國圖文書出版領域開風氣之先。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認為三聯書店在圖文書市場開拓方面先行一步,較為敏銳,“三聯的其他圖文書,比如馬國亮的《良友憶舊:一家畫報與一個時代》(2002)、周一良的《鉆石婚雜憶》(2002)和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建飛與楊念群筆述的《雪域求法記》(2003),也都很能見精神。除了三聯書店外,如今許多出版機構在圖文書出版方面表現不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平如美棠》,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上海字記:百年漢字設計檔案》,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愛不釋手》都堪稱精品。
老照片里的新選題
圖文書中,老照片類別向來受追捧。與三聯書店類似,早在1996年年底,山東畫報出版社的《老照片》圖文叢書通過講述照片背后的故事記錄歷史,別開生面,一度創下每輯發行30余萬冊的銷售業績,引發了風靡全國的“老照片文化熱”。老照片圖文書至今時有佳作,如山西人民出版社《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光明日報出版社《中國老旗袍:老照片老廣告見證旗袍的演變》,各有特色。在蘇珊·桑塔格看來,書籍向來是整理、保存照片的最有影響力的方式,即便不能確保它們不朽,也能延長其壽命,從而使它們更容易擴大傳播面抓取讀者,因為照片容易損毀或丟失,“書籍中的照片,是影像的影像”。
依筆者的編輯出版實踐經驗,一本書越有鮮活的史料,越能夠激發讀者的好奇心;越是貼近讀者的生活,越能夠吸引讀者的興趣。并且,老照片圖文書與三聯書店的文化品位追求契合度較高,相對其他插畫、插圖類圖文書更便于找到適合出版的選題。三聯書店《妝匣遺珍:明清至民國時期女性傳統銀飾》等圖書即是其中代表。由筆者責編的《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2014)、《東方照相記:近代以來西方重要攝影家在中國》(2015)出版后,也得到中央電視臺紀錄片頻道、《中華讀書報》《文匯報》等數十家媒體的關注或作為好書推薦。
老照片因大多為歷史題材,除了具有史料價值外,還容易激發讀者的懷舊情結,它們如果與恰當的文字結合,具有明顯的記憶重建功能。“閱讀老照片絕不是讀者當下無‘先見地進入客觀的歷史,而是讀者當下的‘閱讀視界與老照片的‘歷史視界之間的一種‘視界融合。在這種融合中,歷史被重新建構起來,而個體與歷史的關系也在其中被建構起來。”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釋,為何人物傳記、歷史題材作品,搭配一些罕見的照片后,往往成為賣點之一,且更容易受到媒體和讀者關注。如三聯書店版《張充和詩書畫選》把傳主不同時期創作的詩、書、畫分類,結集,便非常雅致。民國題材類圖片也具有懷舊元素,名家名作便于提升圖書的品相,上海書店曾將豐子愷為魯迅名著《阿Q正傳》畫的插圖結合起來,并配上周作人過去寫的一些相關點評文字,出版了一本新的圖文書,視覺上較為精美。而《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一書中的圖片全選自百年前國外報刊刊發的照片或圖像,有些還是刊于封面或封底的整版圖片,為了完整呈現,帶有當年報頭的圖片都整版放在了書上,甚至有海戰場景的圖跨版呈現,這樣使得圖片視覺沖擊力更強,同時附上報頭等信息,增強了圖片的史料性。
圖文避免“兩張皮”
一本真正有深度的書不能只有珍貴的圖片,還需要有精彩的文字與獨特的思想觀點。尤其對具有學術色彩的書而言,如何將高深的文化話題“翻譯”成讀者可以接受的語言,這是需要編輯和作者共同完成的事情。三聯書店的圖文書在編輯時,非常注重將學術知識大眾化。如《百年衣裳:20世紀中國服裝流變》從題材上看,類似于學術研究課題,但文字可讀性強。在論及21世紀的服裝潮流,作者以活潑的筆調寫道:“中國時裝界在又一次的新舊世紀交替的門檻上悄然發起了‘中裝熱潮,立領、盤扣、斜門襟掀起了未來中國時尚的蓋頭,這回輪到外國人嘖嘖稱贊:‘Cool(酷)!”
在圖文書的文字編輯加工上,圖說是圖片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兩者分屬不同的敘事手段,具有不同的功效,但又得融為一體,否則便成“兩張皮”。“圖片說明依附圖片而存在,既要與圖片保持敘說對象的同一性、敘說效果的統一性,又要調動文字特有的表達方式和手段形成話語策略、言說指向的差異性,從而形成文圖之間有離有合的對應關系,達到圖文意義互生互動的復合效果。”此外,圖說起到交待圖片的來源與授權情況的作用。筆者曾操作多本圖文書,且圖片大多涉及版權保護問題,需要得到圖片所有者的授權才能使用。最初,筆者在編加源自國外版權所有者的圖片說明時,對同一系列圖片中出現的同一授權人(或授權機構)的名稱,只在首次出現時保留,之后都作了刪除處理。圖書作者看校樣時特別指出,外國人相當重視版權,每一幅圖片都得注明授權處,絕不能刪去。
佛靠金裝,書要“精”裝
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系在圖文書中體現明顯。一部好題材、好內容的書稿,如果在形式上下足功夫,更能提升書的品質,有著錦上添花的效果。三聯書店在書的設計與印制環節上抓得很嚴,對編輯、美編及印制人員的要求較高,“書卷氣”便是其核心表征。
以《東方照相記:近代以來西方重要攝影家在中國》為例,筆者在審稿階段時,心里就琢磨著每章節圖的擺放問題。按照作者的想法與要求,每幅圖隨文插,散于書中各處。可筆者通讀完全稿后,深感若將圖分散放,反而削減了圖片的沖擊力。于是,在編輯加工過程中,筆者時常去書店翻看相關的圖文書,將看到的一些感受與美編交流,請美編從專業的角度來研究什么樣的設計才更為理想。后來,我們商量將書稿中大部分圖集中放在每章文前,少量圖片隨文插。這樣的做法有三個好處:一是集中插在文前,形成的沖擊力較大,較為吸引人;二是在后期印制環節中,彩色印張與黑白印張可分開印,能夠節約一定的成本;三是這也很好地表達了作者的意圖。
對書稿的紙張選擇,三聯書店一向較為講究。《東方照相記:近代以來西方重要攝影家在中國》全書有彩色照片也有黑白圖片,有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也有二十多年前的新照片,如何將這些新舊、色彩不一的圖片很好地呈現出來,紙樣的選擇與印制時的機上調色很關鍵,不同的紙張來印制所起的效果會大相徑庭。筆者與美編及印制為此書稿先后挑選了五種紙,從70克晨鳴米膠到90克的藝術紙,打出多個紙樣來比較,最后較滿意于80克藝術紙的打樣。但經過成本核算,發現費用甚高,出于保障圖片質量的考慮,最終仍然使用了80克藝術紙。于是我們想到書稿中多為黑白圖片,彩色圖片并不多,又大多為集中插,何不用“4+1”的印圖方式呢?如此一來,在不損害圖片呈現效果的前提下,減少了彩色印張數,印制成本也得到控制。
數字時代的圖文書
隨著數字技術的普及和微信等新興媒介的崛起,帶有鮮明技術驅動特質的出版業,正歷經從“鉛與火”到“光與電”的變革,并且已然形成了印刷媒介、電子媒介、數字媒介鼎足而立的態勢。與此同時,讀者的閱讀習慣日趨多元:一一方面,讀者獲取信息的能力極大提升,他們通過智能手機、移動閱讀器等媒介,足以獲取海量內容;另一方面,閱讀尤其是數字閱讀的泛娛樂化傾向凸顯,重形式觀感輕內容思想的淺閱讀、碎片化閱讀十分流行。
就讀者接受角度而言,相對于純文字的圖書或純圖片的繪本(畫冊等),圖文結合得體、印制精美的書籍具有其獨特優勢,其生動、直觀的視覺形象,往往更容易令人產生審美愉悅,也便于抽象的思想、論述具象化呈現,有助于讀者理解。數字時代,探索紙質圖文書融合出版的路徑,或可發揮其傳統長處,并與新興技術和應用嫁接,從而適應時代發展需求。基于成本控制和目標市場考量,圖文書在推出優質印刷版的基礎上,可以借助數字技術,建構主題圖片庫、數字體驗館、信息數據庫或進行IP運營,以此拓展產品鏈,為讀者提供多樣的增值服務,并通過“兩微一端”等平臺傳播,增強互動、擴大影響。筆者責編的《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體觀察》(2014)出版時正值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可謂當年主題出版物,雖然紙版圖書上市后被《新京報》等30多家媒體報道,不少讀者向出版社打電話要求訂購,或在網上留言表示贊許等,店里還應讀者要求出版了精裝大開本珍藏版1000冊,但即便這樣一本較有特點的歷史圖文書,其平裝版當年也只銷了1.5萬冊。現在反思,在原圖片的發掘以及數字化產品的配套研發上,尚有改進空問。當代圖文書出版的轉型,仍待諸多有識之士不斷探索、創新。
(唐明星,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2015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