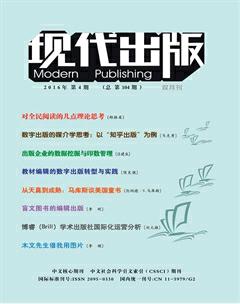《科學》雜志怎么應對數據造假
美國的《科學》(Science)是全世界最權威的期刊之一,從1880年創辦以來,已走過130多年的歷史,主要發表最好的原始研究論文、科學綜述和前沿研究與科學政策等的分析報告。最近幾年,隨著網絡技術的進步和科技發展的加速,人類科學的發展邁進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同時伴隨著科學倫理與科研生態急劇惡化的嚴峻局面,大量的數據造假論文呈現愈演愈烈之勢,因造假丑聞而鋃鐺入獄也非絕無僅有。2015年度科學丑聞之一的韓東杓(Dong Pyou Han)承認其艾滋病疫苗實驗為“追求完美”而偽造數據,結果被法院判處57個月的監禁,這是20年來少有的因科研不端而被美國法院重判的科學家。毋庸置疑,打響保衛科學精神的“數據戰爭”,《科學》雜志別無選擇,也責無旁貸。
數據造假始于何時很難考證,但集中爆發的時間卻可追溯,標志性事件距今也不過10年時間。2002年,《科學》雜志集中撤銷了8篇德國物理學家合恩(Jan Hendrik SchSn)論文,原因是文中很多數據由作者捏造杜撰。時隔兩年,《科學》雜志發表韓國生物學家黃禹錫(Hwang Woo suk)的關于人體干細胞克隆胚胎的研究論文,被韓國首爾國立大學調查,結論是蓄意數據造假,被雜志撤稿,這一事件成為《科學》雜志乃至人類科技史上的標志性負面事件。
后來,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技術的智能化,加之科學研究的商業化和功利化的滲透,科學研究的數據造假越來越猖獗。尤其是《科學》與《自然》這樣的頂級期刊,更是造假的“重災區”和世人矚目的焦點陣地,造假丑聞頻頻曝光,2012年第335期《科學》雜志發表的論文,關于癌癥治療藥物對老年癡呆癥有治療作用的結論,受到多位重量級科學家的質疑,需要進行藥物的臨床驗證,以此驗證數據的真實性。2010年第467期《自然》雜志發表的論文,關于蛋白的治療作用也被科學家質疑。科學數據造假,原因不外乎三個方面,一是科學評價對科研生產的誤導,二是科學家對科學神圣性的動搖,三是法治對科學造假懲戒軟弱。針對這一危及科學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科學》雜志審時度勢組建了數據編輯委員會,《自然》雜志也及時實施類似的舉措。
自然科學領域的數據造假已經不是新聞,社會科學的數據造假也有“罪證”。就在2015年5月,美國社科界的造假丑聞浮出水面,《科學》雜志半年前發表的一篇論文被質疑數據造假,署名第二作者的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政治科學家唐納德·格倫(Donald Green)已經提出撤稿。2014年12月12日出版的《科學》雜志發表一篇標題為When contact changes minds:An experiment on transmission of support for gay equality的論文,其調查的數據認定,如果同性戀平等權游說者與選民進行短至20分鐘的當面談話,無論其原來立場如何,都有可能讓其產生支持同性婚姻的立場。論文同時認為,這種立場會持續一年之久的時間,而且,這一立場還直接影響到其家庭成員。論文甫一發表,即受到國際社會政治科學領域的廣泛關注并引發質疑,因為加州大學和耶魯大學的學者發現他們無法驗證這篇論文的結果,一致認為不可能“按論文中所提到的方式獲得數據”。最終,論文的第一作者、加州大學的博士生邁克爾·拉科(Michael LaCour)不得不承認數據造假,唐納德教授已在2015年5月19日正式向《科學》雜志申請撤回論文。
愈演愈烈的數據造假丑聞促使《科學》雜志采取應對措施,在原有審稿規則的基礎上,加入專業統計學家對論文數據審查這一環節。主編瑪西婭·麥克納特(Marcia McNutt)指出,數據審核的做法不是《科學》的首創,國際上許多科技期刊已經實行數據審核的審稿環節,雖然原因相當復雜,除了明顯的故意造假之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期刊編輯發現,越來越多的論文提供的數據無法“可重復性驗證”,測試性試驗也證明無法從論文提供的數據中得出相同或一致的結論。在科學飛速發展和科研生態惡化的今天,《科學》雜志以實際行動呼吁全球期刊界必須攜手努力,推進數據審核的標準與制度建設,維護科學的求真精神和尊嚴,
實際上,在德國物理學家合恩的論文被撤稿之后,《科學》雜志就決定改變學術界實行多年的審稿慣例,采取對可疑性的成果論文“先試驗、再發表”的做法,但限于試驗手段和實效性的要求,這一措施實際上沒有嚴格付諸實施。雜志編委會還采取過其他手段強化審稿責任,提出建議把收到的論文稿件分為“無爭議性稿件”和“爭議性稿件”,以使存在爭議的文章數據能夠更嚴格地接受審查和重復性驗證。事實證明,結果并不理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學》雜志需要更有效的舉措。
2014年7月,面對已經到來的“數據戰爭”,應戰并制勝是《科學》唯一的選擇,雜志終于正式向全球宣布,開始對投稿論文進行數據審查,具體的做法是在原有審稿規則的基礎上,加入專業統計學家對論文數據審核這一新環節。主編瑪西婭·麥克納特對每一位編輯提出如此嚴格甚至有些苛刻的要求:“《科學》雜志每一篇論文的結論必須為讀者認可,而不被質疑。”數據審核是—項耗時、復雜、難度極大的任務,一些新的科學發現甚至超出現有的認識與科技水平,要想發現其中的問題或進行重復試驗,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對科學保持謹慎的精神卻是必要的。2016年2月11日,美國科學家LIGO執行主任戴維·賴茨宣布探測到引力波,立即引爆全球科學界,愛因斯坦一個世紀前的結論得到驗證,他與期刊之間的一段審稿故事也隨即傳為佳話。1936年6月1日,國際權威刊物《物理學評論》(Physical Review)收到愛因斯坦和他的助手合作的一篇稿件,題目是《引力波存在嗎?》(DoGravitational Wave Exist?),返回的審稿意見足足10頁,認為“稿件有嚴重問題,必須大修”,這個“嚴重問題”就是結論錯誤。審稿專家沒有因為作者是愛因斯坦而盲從,對論文的推導數據和結論保持謹慎和質疑,發現論文的結論竟然是錯誤的,因此要求論文“必須大修”,從而避免了愛因斯坦本人以及科學發展史上發生重大錯誤的可能。
正是基于對科學數據的重視與負責,《科學》雜志決定聘請美國統計協會的7位科學家組成數據編輯委員會,專門負責論文的數據審查工作。一般稿件的審核有三種方式,一是雜志編輯的審核,二是雜志固定審稿專家的審核,三是雜志特聘審稿專家的審核。雜志主編瑪西婭·麥克納特表示,成立數據編輯委員會的目的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大量的科學研究需要用數據說話,數據的科學使用關系到科學發展的未來;二是《科學》不僅僅做科學傳播工作,更愿意通過可重復試驗和驗證科學數據推進科學進步。數據編委會成員之一、哈佛公共健康學院的生物統計學家喬凡尼·帕瑪嘉尼教授與編委會一致認為,《科學》雜志的數據編委會是數據科學的先行者,數據編輯必將是期刊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對期刊行業的發展將產生深遠影響,《科學》雜志因此將更加強化科學意識,期刊行業也將因此改進科學方法,這是科學的進化和人類的福音。
成立數據編委會的探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數據審核的想法由來已久。早在布魯斯·艾伯茨(Bruce Albert)擔任《科學》雜志主編的時候,他曾提出過一個設想:“成立一個類似于‘出版社千家計劃(Publishers Faculty Of 1000-F1000)的數據平臺,所有的科學研究論文與試驗數據在線公開,很像現在流行的公示一樣。論文在線發表不進行審稿,期刊編輯只審核論文的試驗方法,隨后公開上網接受全球任何人的評議,對有造假嫌疑的論文數據進行專門審查,以確保所發表的論文無可置疑,數據可進行重復性試驗,維護科學的尊嚴和純潔。”
《科學》雜志的新舉措引起了國際知名學者的關注與推崇,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物理學家約翰·艾尼迪斯教授認為,數據編委會是科學的福音和未來的方向。事實上,國際上大多數期刊因為忽略數據審查,造成數據失真甚至結論謬誤,嚴重危及論文的質量和科學態度。毫不夸張地說,在某些領域,數據審查比專業審查更為重要,尤其是醫藥、生化等領域。澳大利亞知名細胞生物學家戴維·沃認為:“全球期刊上科技論文的數據錯誤觸目驚心,對審稿專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們具備數據分析的能力。因此,對期刊而言,必須挑選有數據素養的專家擔任審稿,招聘的編輯要求具備數據推理與審查能力。”
“科學共同體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進行可重復性試驗,以保證科學研究的公正性與數據的真實性。任何點滴努力,看似微不足道,實則善莫大焉。”英美神經科學領域的領軍式人物查德·多爾梅齊(Ricardo Dolmetsch)如此看待科學研究中數據的重要性。多位國際學者斷言:科研數據公開已是大勢所趨,除了特殊情況之外,所有的科學數據都要及時公開,通過共享機制以推進科研進步。美國的國家科學數據公開平臺Zika Open已經呼之欲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公開予以支持,希望所有相關數據在24小時內在網上公開。
2014年1月13日下午,我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科學》雜志主編瑪西婭·麥克納特時表示,尊重科學、尊重知識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當今時代,科學技術不僅關乎經濟社會發展,而且事關民生改善。希望《科學》雜志繼續支持中國科技事業進步,促進基礎科學研究,向國際社會積極傳播中國科學界的聲音,擴大中外科研成果交流互鑒。
新的時代,數據戰爭已經打響,期刊改革號角聲聲不息,國際頂級期刊的行動大幕開啟。2013年4月,《科學》雜志正式公布第一批數據標準清單,供投稿者和研究者與自己的研究數據進行對照,以追蹤數據偏差的根源和進行可重復性驗證。同時,《自然》也決定將聘任統計學家“擔任審稿顧問、編輯業務指導和稿件爭議仲裁”。《科學》與《自然》作為國際頂級期刊,在引領科學發展和發揚科學精神的道路上不謀而合,勇于探索,奮力開拓,做科學精神的衛士,燃科學的創新之光,值得我國期刊出版領域深入思考和虛心借鑒。
(郜書鍇,河南理工大學建筑與藝術設計學院教授)